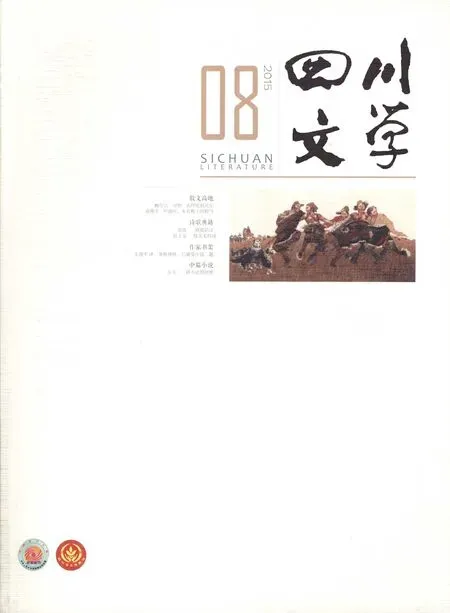晚餐后
格 致
晚餐后
格致
晚餐后,扶疏正喝茶,从窗子看出去,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这时,门铃又响了。门铃在这个时候响起来,吓了扶疏一跳。因为家庭成员在一个小时前已经到齐了。这个时候门铃响,她不知道是谁来了。
一小时前,扶疏的儿子放学回来。他放学的时间是固定的,总是5点半放学,6点左右到家。门铃在这个时候响起来,一点都不吓人。六点门铃响的时候,扶疏正在准备晚饭,进行到饭煮好,正切菜的阶段。因为切菜刀钝,她在这一环节用掉了太多时间。要是切青菜刀可以钝,切青菜有块铁片就行.现在是切酸菜,切酸菜刀必须快。两个月前这把刀快过一阵子。孩子的爷爷从乡下来了,满院子人他一个不认识。他不爱下楼,他就在7楼上磨刀。把菜刀磨快了后,他又找到了两把水果刀。磨完水果刀再想磨刀就没有了,扶疏家就这3把利器。原来是4把,那第四把是蒙古刀,柄上、鞘上刻着花纹,是件艺术品。刻着花纹的艺术品被她前夫带走了。走时还恶狠狠地说,指不定哪天,就用这把刀结果了她。扶疏也不知道害怕。她了解那把刀,上面花纹不少,却是刃还没开,不是个杀人的好工具。再说,杀个女人还用刀吗?他越这样说,她就越觉得性命无忧。越觉得不光那刀没开刃,他也没开刃,比刀钝。扶疏努力把肉片切薄,薄到透过肉片能看见下面盘子上的蓝色花纹。
这样切了五、六片。孩子能吃一片,自己能吃两片。三片肉做白肉酸菜太少了。那棵从乡下姐姐家拿来的酸菜卧在盆子里,正散发着生机勃勃的酸味。这棵酸菜在一个陶缸里,压在一个大石头下已经好几个月了。它的身上积压了一个季节的心酸。一会还要把它切成细丝,纤维里的压抑都会以气体的形式从断口里倾泄出来。这样来历的一棵酸菜三片肉怎么能镇压得住呢?扶疏切了15片肉。15片肉和这棵酸菜刚好势均力敌。
切完五花肉,刀的钝就又加了一层。下面的酸菜已经没办法切得细了。而酸菜切不细是不好吃的。扶疏从小吃她妈妈切的酸菜。妈妈能把酸菜切细,并不是她父亲是个多爱磨刀的人。相反,他父亲是从来不知道磨菜刀的,他整天开会,整个人在形而上里。他不肯磨菜刀,一磨菜刀他就掉入形而下。扶疏常听见母亲把刀往米缸的边沿上挡。这种摩擦只解决一次切菜问题,于是母亲就天天这么磨刀。那声音刷刷的,一直响在她的童年。今天,扶疏遇到了和母亲相同的问题。母亲磨刀的声音响起来,她开始在厨房里寻找米缸的边口。她找到了米却没找到缸。她的米装在一个软软的口袋里,因此她没有缸,也就没有缸的边沿。也就没办法像母亲那样磨刀。她转过身就找到了洗碗池的边。把刀与洗碗池的边摩擦,发出的声音与母亲的声音出入很大。没有母亲磨刀的声音爽朗。洗碗池太薄,发出的声音也薄,还短促。陶缸的边有一个拳头厚,母亲磨刀就有回声—陶器的回声—厚度里的回声。那声音前一声还在绵延,还没走出多远,后一个的高音部分就追上来了。所以母亲磨菜刀的声音是个复式结构,是至少两个声部的合唱。扶疏磨刀的声音脆薄,一出来就断了,在第二个声音出来之前,有一段无声的空白。这样的声音就不好听,像米粥没煮稠。
比不磨还是快了一些,酸菜切得肯定不如母亲,但
也勉强及格了。
等水开了,先放酸菜丝。等水再开上来,再放肉片。然后放盐、料酒、八角、桂皮、花椒、姜片、葱段,她是按照母亲的程序作业的。肉片变白后,她想起忘放粉条了。这时放很粗的粉条已经来不及,就放了一小捆龙口粉丝。扶疏不爱吃粉丝,粉丝太细,禁不住滚水的煮。她爱吃粉条,煮了又煮,柔软、透亮。粉条是开水里的鱼,只有开水才能让它复活。它在沸水里游动,闪着光。不知道难受。
盛到碗里之前,她又放了几种绿色的菜:香菜、油麦、藤蒿。这些是她自己决定放的。母亲没这样放过。母亲那时的冬天也没有青菜啊!若是有,母亲是会放的。最后,扶疏扔进一块重庆火锅底料大红袍。这块东西一融化,汤锅立刻就像喝醉人的脸,不仅红而且油亮亮的。
这时门铃就响了,5点半,儿子血嫣然放学回来了。血嫣然是他的网名。在松花江中学,他叫黄虎;在扶疏视野里他叫小龙。他刚十几岁,就已经有至少这三个名字了。总之,在不同的空间,他有不同的名字。现在,他回家来了,他不叫黄虎,也不叫血嫣然,他叫小龙。
血嫣然一进门就大叫,老妈,你又做酸菜啦!我最不爱吃酸菜啦!你还做!说多少次了你还不知道改。这屋子里全是酸菜味。你还让人活不活啦?
扶疏一边把做好的酸菜往碗里盛,一边决定得教育这个孩子。对酸菜这么抵触是不对的。
扶疏说,这可不是普通的酸菜,这是你大姨家的酸菜。不吃大姨家的酸菜,就是对你大姨有意见。没有大姨那些年你就得去幼儿园,幼儿园有多可怕,你是知道的。是大姨把你从火坑里救出来,并且一直把你抱大。如果你想感激大姨,那么就吃大姨家的酸菜吧。
血嫣然不是那种特别犟的孩子。他总是先说不,然后坚持不住自己的立场。他比较容易被语言左右。这点特别像他爹。
血嫣然开始试着吃那碗酸菜。
扶疏的那段没什么道理的话开始起作用。说来这是扶疏惯用的招法。一遇到他对某种食物抵触,她就随口编故事。这个故事要把这种蔬菜与血嫣然编进去。听着听着,血嫣然就进入情节,开始吃菜了。开始报答他大姨的恩情了。但这次,血嫣然与这碗里的酸菜的关系不是虚构的。那酸菜真是他大姨家的。
在事实的基础上,扶疏得寸进尺,提出让血嫣然把一整碗都吃掉,要求他把那酸溜溜的汤也喝了。
汤他怎么也不肯喝。对大姨的感激再多他也喝不完,但他超额完成了吃肉任务。他顺利地吃了碗里的三片肉,还吃了扶疏碗里的两片,算超额完成了任务。
血嫣然还说:“妈你好久都没做猪肉了。”
扶疏说:“是吗?那妈明天给你做红烧肉。”
“别再做酸菜了。我不爱吃。”
“好,就吃这一次。”
这样也可以了,他们的晚餐圆满地结束了,连明天的菜谱都定了下来。
血嫣然回房间写作业或用手机上网听歌;扶疏坐沙发上打量她的起居室。屋角放着几个青瓷花瓶,刚买回来的。一个外地瓷器店到期,所有的瓷器摆门口打折。扶疏去了三次,一次抱回一个。都很大,尤其是花瓶的肚子。这些花瓶没什么收藏价值,但是插花还是比那花店的所谓艺术花瓶好许多。明天去买绢花。她喜欢秋叶牡丹。要整束花不见绿叶子。绢花若模仿自然之花,那是费力不讨好。模仿只能靠近,或无限靠近。不要往真靠近,要不怕假。要一看就是假花,然后比真花好看,比真花惊人。在真花之上。
这时,门铃又响了。
在从沙发往门口走的几秒钟里,扶疏想这人是谁?天已经黑了,所有家庭成员都已到齐,不缺谁了。亲戚们一般不天黑来。走到门口时,扶疏已经把按门铃的人界定了下来:知道自己住所,又认为自己可以天黑了后不打招呼就造访的,这个人只能姓童。
扶疏摘下听筒,谁呀?
门外的童济说,我。
扶疏竖起右手食指,按“开门”键,同时左脚已经迈出去,她的脚是向着与门相反的方向—落地窗。她没穿拖鞋,跑起来就像猫,无声、迅捷。窗子向左右拉开,北方十一月傍晚的凉风就灌了进来。
这个房间面积应该有40平,2分钟内很难置换完酸菜五花肉味。她决定帮助一下窗子,卫生间里找到一瓶花露水。站在屋子中央,旋转,同时按下喷雾开关。
这些动作完成,用了有30秒。这时,楼梯间的脚步声已经能听见了。从声音判断,童济应该走到5楼了。还有30秒,另一个空间的环境也需治理。刷牙是来不及了,茶几上的圣女果,一口吃掉2个。2个被大致咬碎的圣女果经过食管刚落入到胃里,童济就站到了打开的房门前。他一只手托着个葫芦似的蜜柚。扶疏已站在了门口,像是等候多时。她连拖鞋都穿好了,嘴里不再咀嚼,嘴角适度向上,微笑着。她弯下腰,把一双灰色拖鞋工工整整地放到他的脚边。
柚子坐在茶几上,一片塑料叶子像柚子举着的一面小旗子;童济坐在柚子后面的沙发上;扶疏面对童济坐在地板上。童济开始抽烟。扶疏着手剖开那个包了层海绵似的福建平和蜜柚。
烟雾开始弥漫。扶疏把拿到的果肉放入口中,期待这些清甜的果肉继圣女果后进一步破坏口腔里的酸菜肉味。
一根烟抽完,童济熄灭那个烟蒂的同时,环视房间,终于说:“你冷不冷?”
扶疏起身,向窗子走,开着窗子呢。关窗子的声音很好听—啦啦啦啦。童济把头扭向扶疏:“都几月了,你还开窗子?”
扶疏往回走,坐在地板上,童济和柚子的对面:“三九天我也开一会窗子。室内空气得定时置换,就像床单得定时洗。空气也能用脏呢。”
“空气也能用脏。”童济重复了一遍,“这话说得有趣。”
扶疏说:“能听出来有趣的人,也是有趣的。”
扶疏的神经从紧绷处往外松了一扣。他的注意力已经在说话上了。窗子开了至少5分钟,还有花露水,然后是一支香烟的气味、柚子的气味。这些气味一层层压上来,原来的酸菜猪肉味被压在了最底层,越来越模糊。扶疏放心了,平静下来。她一平静就向童济提了个问题:
“你从来没在晚上来过?”
他们见面总是事先约好。后来,略熟了后,基本就是在扶疏家里。扶疏也不爱到外面吃饭,她计较环境及环境对情绪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家里有沙发,可以坐着,可以说话;家里有厨房、餐桌,可以制作餐饮,可以吃饱;家里有卧室,卧室里有床,有床就可以躺着,睡觉或者不睡。总之,家里功能齐全,自给自足。对外面的需要仅仅是一些阳光。有时连阳光也构成打扰。
第一次来扶疏家,是两个月前。那时还是比较好的秋天。扶疏说,那午饭就在家里吃吧。童济说好。
放下电话,扶疏就进了厨房。打开冰箱,里面只有几只乌鸡蛋,还有一条黄瓜。看看已经10点了,就到离家最近的百联超市买菜。她买到筐里的菜是:两条苦瓜,一片冬瓜,一簇西兰花。到生鲜肉区,她犹豫了,菜是可以随便买点,但肉不行。想起前夫不爱吃牛肉,那么童济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呢?最好问问。童济从一个嘈杂的背景里大声说,那就羊肉吧。扶疏买了一块羊排,又买了一块牛腱子。回到厨房,扶疏用买回的这些原料,制作了4样菜:1、酱牛肉。2、冬瓜羊排汤。3、苦瓜素炒。4、西兰花凉拌。童济表现得很好,几乎把所有的羊肉都吃了。没忘表扬扶疏做的菜看着吃着都很好。
扶疏说,你是如此地爱吃羊肉啊!
童济说,嗯,牛肉也行。
扶疏说,我原想买猪肉炸丸子来着。
童济说,我不爱吃丸子。油炸的就更吃不了。
扶疏说,我怎么感觉你是不吃猪肉,而不是不吃丸子?
童济说,你感觉得很准确。
扶疏惊讶:真的?
童济就给扶疏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小时候上学要经过一个菜市场。市场上有一长溜卖猪肉的床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气味,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闻那个气味。每天早上我走到市场头上,我就先站好,深吸两口可靠的空气,然后我开始跑。那个市场有50多米。我要跑过去,不能中途换气。上学、放学,我每天要这样跑两次。
其实,我也不爱吃猪肉,听完童济的故事,扶疏说。
那就别吃了,童济似漫不经心地说。
就是这样开始的,扶疏开始戒掉了猪肉。
童济走了后,扶疏把所有的餐具用开水煮。她不信任那个消毒柜。因为她看不出那个消毒碗柜是如何消毒的,而翻开的水花令人信服。那水是100度,什么样的细菌能在开水里不死呢?她不光是为了煮死细菌病毒,主要是煮掉那些经年的猪肉味。
第二周的时候,扶疏又去超市买菜。童济不在,她就不买鲜肉,尽可能素食。但男孩血嫣然得吃肉。没有肉他就要生气。扶疏就给孩子买了哈红肠。等晚上切的时候,她猛然意识到:这肠是猪肉的!已经切到了一半,刀停在那里。童济的脸出现在眼前,他说,你坚持不住了吧。扶疏晃了一下头,把童济的头晃没了后,坚持把那肠切完了。然后立刻把刀和菜板用洗碗液反复洗。
吃饭时,扶疏一口没吃那肠,也不敢看。她找到了两个自己可以被原谅的理由:1、自己不是有意的,并且没吃。2、孩子可以不加入到这个大人的感情附加条件里。
一周后,童济和扶疏又在一起吃饭。扶疏说了红肠事件。童济笑了,他说,我哪有理由要求你什么。这样我已经很感动了。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 ,我也可以忌。扶疏说,我不吃狗肉。童济说,那以后我也不吃了。说完,把头向扶疏移过来,在扶疏的嘴唇上亲了一下。
一种突然的困倦像一片薄云遮住了扶疏。接着出现了轻度的意识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扶疏还是吃力地思考:童济这是第一次吻自己的嘴唇。来往有快两个月了,做了有4次爱,每次童济都是小心地绕过扶疏的嘴唇,他吻她的额头,吻她的眼皮,吻她的头发,还吻过她的脚。他几乎把她给吻遍了,但扶疏记得,他没吻过自己的嘴唇。这件事一直是扶疏心里的一个疑问,一个结。扶疏认为,童济不能完全地接纳自己。甚至可以说,他不爱自己。扶疏认为,两个人如果能热烈地接吻,那么这两个人是相爱的,是完全接纳的。哪怕他们没在一起做爱。如果两个人做爱而不接吻,那么这两个人就可疑了。这不是扶疏在哪里看到的理论,这是她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总结归纳出来的。她反抗丈夫大同。但大同以婚姻为依据,每每强迫扶疏。他充分利用自己在体力上的明显优势,打过几次架之后,扶疏放弃了反抗。但是,她用两只手,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大同试图把她的手移开,但她坚决地封死了这个入口。大同也不太坚持,他似乎不重视这里。以这种姿势,他们又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提完了问题,扶疏也点上了一支烟。她的嗅觉不好,已经不知道房间里现在到底是什么气味,或以什么气味为主。但她知道男性的嗅觉都很敏锐。有的还超常地敏锐。她担心的是自己的口腔气味。吸烟,吃柚子,吃圣女果,自己的口腔里现在气味也跟这房间一样,很复杂,很混乱。
“忽然想来看看你。”童济说。“你这是第一次,在忽然的支持下来看我。”扶疏说。“这段单位忙,下个月要承办一个系统内的全国会议,等这会开完了,就好了。”童济熄掉手里的烟。
扶疏把一块蜜柚递给他,然后起身去了卫生间。只要家里有男性在,扶疏在卫生间方便时就要比平时废水。她要按两次冲水按键。大同跟她说过,他一听到女人的声音就有反应。由此,扶疏推导出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的。那么,她就不愿意让男人听见。她认为,由这件事而起的反应一点也不美好。她一进卫生间就先把水箱按下去。在巨大的水声里,自己的声音被很好地淹没了。完了,再按一次。扶疏在第二次水的轰响里,迅速刷牙。刷牙的尾声还是被童济听到了。这也是她不愿意的。她不愿意暴露心思。尤其现在刷牙,欲盖弥彰。可是,她太需要刷牙了。扶疏涂了点唇膏从卫生间出来,童济已经站了起来,他说,我先走了,找时间再来。你休息吧。
扶疏没说话,平静地看着他。
童济向门口走,扶疏跟在后面。她没说挽留的话。整个屋子都是她背叛他的气味,再说什么自己都觉得假。只能过些天,等这些气体完全消散了后,看看还能不能弥补。
临出门,童济缓慢地转过身,面对着后面的扶疏,伸出右手,环住扶疏的腰,同时低头在扶疏的额头上印上自己的唇印,小声说,你好好睡觉,我先走了。
一直到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消失,扶疏没说话。在门口站了有一会儿,直到意识到这样站着什么意义也没有,就关了门,回沙发上,在童济刚坐过的地方坐下了。沙发已经被童济坐热了,他在这坐了有一小时。
扶疏坐在童济留下的余温里,一点点把这些温热吸收给自己。
与扶疏身体的接触,童济总是从她的额头开始,小
心绕过她的唇,向下。最初的几次,扶疏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扶疏的一半留在原地寻找答案,另一半跟着他向前进。虽然在前进,但童济是可疑的。她发现,他也是一半在这里,另一半,在别处。扶疏是不愿意与一个半边人做爱的。这让她感到挫败。就在她决定放弃他的时候,那个困扰她的疑问突然在他们共同的餐桌上,呈现清晰的答案。
障碍原来仅仅是一种食品。扶疏认为这太简单了。她和他之间的障碍不用太费劲就可清除。她清除这个障碍一个月后,童济第一次吻了她的嘴唇。此后,他们是以两个完整的人在共处。
今天,几个月的努力归零了。扶疏从里到外散发着背叛的气味,童济不提问,但他迅速后退,一直退到起点,退到扶疏的额头。
就在下午,扶疏去超市买菜。这次去买菜的背景是这样的:童济已经两周没来扶疏这里了。不但如此,而且没有打过一个电话,像是失踪了。扶疏也不打电话,她不愿意追问。如果愿意等那就别怨,如果觉得委屈,那就不等。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买菜,意外就发生了。扶疏走进超市的时候,脑子还是混沌的,没有清晰的方向。只是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冰箱需要补充。她先买蔬菜:黄瓜、苦瓜、菜花……然后买水果:苹果、柑橘、龙眼……然后,她来到生鲜区。牛肉的颜色很好。红,大片的。扶疏看见在童济的左颈部,有一条暗红色。如果这条红色在身体的其他位置,如胳膊或腿上,那么就一点都不可疑,它的位置是在颈部,扶疏看在眼里,记在了心上。当时她没问。问也没什么意思。关键是扶疏马上知道了这条位于颈部的暗红色是怎么来的。她想在他的颈部的右侧也来这么一下,让他对称。最后她没那么做,觉得没意思。没有任何情绪。半个月了,扶疏以为自己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当她看见红色的牛肉的时候,她知道自己没忘。如果在这半个月内,童济不是这种失踪状态,扶疏是可以强制自己忘掉那条颈部的红色印痕的,扶疏在超市里就不会突然改变方向。扶疏推着购物车,缓缓走过牛肉柜台。她和童济的联系随着他的失踪断了。扶疏在超市的轨迹缺少童济的羁绊,她走到了猪肉柜台。扶疏犹豫了。已经多少个月了?至少是4个月她因为一个男人戒掉了从小就吃的食品。她和这种食品是没有仇的。现在,她认为再拒绝这种肉已经没有理由了。还有,那棵姐姐给她的酸菜,那酸味从童年飘来。一同飘来的还有猪肉的气味。母亲从来都是用猪肉和酸菜一块做汤的。她也应该用猪肉一块做汤。如果童济在她的生活里,她可以修改这个汤的成分,她已经修改了好几个月,现在,突然,她发现这种修改已经没有依据,找不到了理由。如果,继续下去,那么就是怀念。扶疏不想怀念,她想坚决地翻过去。她命令自己行动。她的行动是需要一块五花肉的支持的。
扶疏坐在童济坐过的沙发上发呆。童济的余温已经飘散,猪肉酸菜的气温也已经模糊。现在,她像坐在真空里,什么气味也没有了。
用一种食品报复童济后的感觉不怎么好,她感觉不到那种平衡。童济的那边还是重,自己在童济的压力下,在离开地面。
扶疏认识到童济这一页她没能翻过去。那几片五花肉太单薄了,虽然都尽力了。不但没能帮到她,甚至帮了倒忙。她发觉自己吃了五花肉之后,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原来的那页上,没有前进。不同的是,现在这页四处布满了错字。她回不去过不去,卡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如果是错字就好了,擦掉错字是多么容易。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面前的那盘圣女果,她一个接一个地吃。不停地吃。一盘子很快吃完了。
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
童济说他一直在楼下的小街上走。扶疏说你怎么还没走到家?
童济说不知为什么还没走到家。
扶疏说我也需要下楼在小街里走一走,吃完晚饭我每天都要走一走的。今天怎么忘走了?
童济说那你现在下楼补上吧。其实我还没吃饭呢。我看见这里有一家回族餐馆。
扶疏穿上大衣,回头看了一眼镜子:有点胖,明天得减肥了。
一出大门,凉风像水一样向她吹过来,顷刻把她包围了。扶疏深吸一口气,又缓慢地吐了出来。感到从里到外都被洗过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