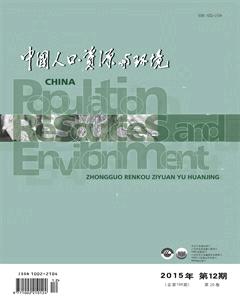基于风险与机会视角的贫困再定义
王文略 毛谦谦 余劲


摘要 对贫困概念和成因的合理界定和理解是制定反贫政策的重要基础,对贫困的定义是根据不同阶段和时期的贫困特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动态过程。我国是世界上贫困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新的反贫阶段中,原有的贫困概念界定和贫困成因已无法对新时期贫困的特征进行全面解释,需要进一步对贫困的概念和成因进行丰富和完善,以制定合理有效的反贫政策和方法。本文主要利用文献归纳法,对国内外不同时期对贫困概念界定和贫困成因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对贫困的解释由单纯考虑收入因素发展到综合考虑能力、权力、社会排斥、脆弱性等,造成贫困的原因主要有制度不利论、资本缺乏论及环境约束论,虽然在贫困的概念及成因中脆弱性的提出涉及了风险的要素,但大部分学者将脆弱性视为贫困群体缺乏权利的一种表现,没有突出风险在贫困内涵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没有涉及机会把握对反贫困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在新时期贫困的形成过程中,应将风险和机会纳入到贫困的内涵中,将贫困概念进行扩展和完善,即贫困应为缺乏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及没有把握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风险冲击与机会缺失是导致贫困的本质因素。机会缺失其实质是个体风险偏好的不同,近年来实验经济学引入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开拓了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视野,由此本文设计了基于风险与机会的贫困分析框架,为反贫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框架。并提出对风险的有效管理是农户脱贫的重要手段,有效的风险管理可将导致贫困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同时也是最为节约成本的反贫方法。
关键词 贫困;风险;机会;再定义
中图分类号 F3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2-0147-07
减贫是世界最重要的人权事业之一。我国是世界上贫困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981年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43.1%,到2010年,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下降至13%,为全球的减贫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突出贡献[1]。虽然我国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新时期的贫困问题具有诸如相对贫困人口增多,贫困代际传递,贫困区域集中连片,深度贫困人口众多,无法精确瞄准等新的问题和特征,为进一步减贫带来了巨大挑战。长期以来,不同学者试图总结贫困的概念及贫困的成因,由单纯考虑收入因素发展到综合考虑能力、权利、社会排斥、脆弱性、话语权等,使贫困的概念不断丰富和完善,普遍认为制度、资本、环境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但纵观贫困概念的发展历程,都是对贫困现象的概括和反映,对贫困的成因也仅从贫困的现象解释,对贫困的本质及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仍未形成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1 贫困概念的再定义
对贫困的定义最早是从收入和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角度考虑,Rowntree在1901年对贫困的定义为“总收入水平不足以获得仅仅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生活必需品”[2]。随着对贫困的广泛理解,阿玛蒂亚·森提出能力贫困,扩展了贫困的概念和研究领域。在能力缺乏论的基础上,众多学者认为社会排斥、话语权等权力的缺失同样是贫困的表现,由此形成了权利贫困理论。世界银行在1990年将贫困定义为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2000年扩大了贫困的概念,认为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
我国学者依据中国贫困问题的特点对贫困的概念不断深化和完善。叶普万将贫困总结为缺乏说、社会排斥说、能力说和权利说[3],郭熙保将贫困归结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力贫困,在以上贫困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上,相关机构和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贫困概念,如 “人文贫困”[4]、 “知识贫困“[5],但其内涵均包含在上述几种基本的贫困概念中。李实将我国城镇贫困分为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6],类似的还有学者提出了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将时间维度纳入到贫困的度量中,从动态或风险的视角来研究贫困[7]。虽然对贫困内涵的总结不尽相同,但均反映了对贫困理解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8]。
世界银行2000年在对贫困的定义中涉及到脆弱性,其中包括了风险的要素。樊明丽等认为贫困的脆弱性是前瞻性的度量,是测度家庭暴露于未来风险、冲击而给家庭成员发展能力带来约束的一种事前估计。其他学者对脆弱性做了概念解释及测量[10-13],但大部分学者将脆弱性视为贫困群体缺乏权利的一种表现,没有突出风险在贫困内涵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没有涉及机会把握对反贫困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应明确将风险与机会纳入到贫困的概念中,使贫困的定义更加完善。贫困的本质应是缺乏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及没有把握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
风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静态风险,如人们面临的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疾病、自然灾害、社会的动荡与冲突、家庭成员疾病、死亡和作物、家畜的病害等所有能够为贫困群体带来冲击和影响的因素。二是动态风险,指原有富裕的群体在遭遇风险后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机会不仅仅简单指由外部介入提供给贫困群体的诸如政策、教育、就业及补贴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指贫困人口能够主动进行改变,把握能够改善目前生活状态的行为。如贫困农户较早采用新技术、外出打工、提高自身能力等,虽然这些行为不能完全保证使其脱离贫困,但大量事实证明,只要贫困人口能够主动把握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在逐步改善的。
2 风险冲击和机会缺失是致贫的本质因素
依据不同的贫困理论,学者们开始寻找产生贫困的原因,虽然对贫困形成的原因莫衷一是,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制度、资本和环境。
2.1 制度不利论
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认为,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彻底解决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Townsend阐述了制度与贫困的关系,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分配不公和相对剥夺。Piketty用翔实数据和生动事例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使贫困人口增多,阐释了制度是造成贫困的原因[14]。
从国内研究看,我国户口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制度都被认为是造成不同时期贫困的成因[15]。叶普万认为贫困是由于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所造成的使个人或家庭不能获得维持正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一种生存状态[3]。匡远配认为制度创新不足和有效制度滞后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16]。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经济增长对减贫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17],但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了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发挥[18-22]。近年来有关制度对贫困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政策对贫困的作用[23]、社会保障制度[24-25]方面。
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长期以来都在不断优化其各种制度安排以改变贫困状况,但至今通过制度的改变和创新并未能完全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却加剧了贫富差距扩大、相对贫困人口增多。如陈飞的研究表明,虽然收入增长使得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26]。
2.2 资本缺乏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的壮大,开拓了贫困研究新的理论视野。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从资本角度分析,普遍认为资本投入不足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比较典型的理论有 “贫困恶性循环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等。
舒尔茨提出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缺乏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因素;Naschold提出了“家庭资产贫困陷阱”理论,认为拥有稳定资产、大面积土地并且受到良好教育的家庭贫困的机率会小很多[27]。Christiaensen依据人力资本论,认为农户通过生产的兼业化、获得更多的生计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贫困[28]。
国内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缺乏[29],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30],家庭资产,特别是土地的拥有情况等资本缺乏[31]导致了农村贫困。胡鞍钢于本世纪初提出了知识贫困,认为知识贫困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5]。另外,很多学者认为农村贫困家庭具有明显的代际传递现象[32-33];程明望等认为健康与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显著因素,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作用[34];王春超等从收入和教育角度考察了我国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35];薛美霞、钟甫宁探讨了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贫困状态的关系[36]。这些观点形成了资本缺乏论。但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不同资本对减缓贫困作用不显著甚至为负。如教育质量对贫困的影响不显著,教育数量恶化了贫困状态[37];农村金融规模有利于减缓贫困,但农村金融效率对缓解贫困有负向影响[38],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资本缺乏论的思想。
根据资本缺乏论,向贫困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本会减缓贫困,但从实践和相关研究来看,我国长期以来向贫困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教育等资本,但所起的减贫效果并不理想,并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我国政府扶贫投入逐年增加,引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决策的扭曲、资金的低效使用甚至挥霍等[39]。另外,资本主导型的扶贫效率不高,如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倾向,寻租现象比较严重,同时难以调动起穷人的积极性。
2.3 环境约束论
从环境角度,Mkondiwa通过实证研究论述了马拉维农村地区缺水和贫困的关系,对贫困产生的自然环境决定论进一步印证[40]。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将地理信息技术和遥感技术的应用及空间计量方法应用到贫困的研究中,将环境对贫困的影响扩展到空间层次。如Daimon[41],Bird[42]基于印度、津巴布韦、越南等国家的贫困类型研究表明,地理位置偏远、农业生态环境恶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及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区域越容易陷入空间贫困陷阱[43];Okwi et al通过对肯尼亚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地理条件关系的探寻,发现海拔、坡度、土地利用类型等因子能够显著解释贫困空间格局[44]。
曲玮等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仍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45]。但毛学峰认为,在资源禀赋充足的地区同样有大量贫困人口[46],万广华对中国沿海与内地贫困差异比较研究认为,内地的高贫困主要归因于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而不是资源禀赋的欠缺[19],可见自然资源和环境并非贫困的决定性因素。
国内外对贫困形成原因的论点基本一致,均认为制度、资本、环境是导致贫困的三个基本因素,但也有研究说明单一的环境、资本或制度并非贫困的决定性因素。由此看出,贫困是由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在现有贫困成因理论中,只从现象层面解释了贫困产生的原因,而忽视了风险和机会因素,风险的冲击和机会的缺失是导致贫困的本质因素。
2.4 风险冲击与机会缺失
随着对贫困涵义的不断扩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外部冲击会加剧贫困[47],由此将脆弱性纳入贫困分析,而脆弱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风险。Ligon和Schechter将脆弱性分为贫困和风险两个因素,并进一步把风险分为两个次级因素:总体风险和特殊风险[48]。
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都面临着自然灾害,脆弱群体在遭受这种风险后很容易导致贫困[49]。如Dercon等对埃塞俄比亚的研究表明,当收获减产时,农户不仅会减少消费,而且会减少化肥的使用量,产出效率降低,陷入贫困陷阱[50]。陈传波的研究也表明,脆弱群体面临着资产风险、收入风险、消费风险的交织和循环,多种因素都可能使脆弱群体遭遇经济困难[51]。
对机会的把握,其实质是对风险偏好的不同,如高风险偏好群体会率先接受新事物、采用新技术,从而比其他人较早脱离贫困,而低风险偏好群体总是抱着观望态度,不愿冒险而仍旧采用他们认为保险但实际上落后的技术或行为。Phung Duc等对越南三省农户的研究表明,高风险倾向的农户较低风险倾向农户更容易进行劳动力多样化和土地种植多样化[52]。Azam对非洲农户的研究发现,相对富裕的农户具有更强的冒险精神,并获得更高的收益[53]。Rosenzweig和Binswanger的研究表明,富裕的农户从事更多的投资风险性生产活动,并且获取了更高的收入[54]。罗楚亮的研究发现,农户外出务工显著降低了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55];邹薇实证分析表明,贫穷的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较富裕农户低[56]。
表1中对贫困成因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历程进行了简单总结和比较。将风险与机会加入到贫困的成因中,可使贫困的成因理论更为完善和合理。
3 基于风险与机会的贫困分析框架
风险和机会往往相伴而来,二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风险是负担,同时也是机会,为了追求机会,人们必须面对风险,风险和机会的本质是个体风险偏好的不同。穷人由于意识到负面冲击会使他们陷入赤贫、破产或危机,可能就会坚持使用那些看来比较保险但实际上落后的生产技术和谋生手段[57],而不冒险把握或尝试能够使其生活变得更好的各种机会,从而长期陷入恶性贫困陷阱。由此,不同学者对个体风险偏好进行了研究,树立了基于风险与机会的贫困分析框架。
实验经济学引入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开拓了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视野,Von Neumann & Morgenstern、Kahneman & Tversky分别提出了期望效用函数和前景理论[58],成为个体风险偏好研究的理论基石,Holt & Laury设计的HoltLaury机制开创了个体风险偏好研究的新领域[59]。Elaine Liu利用HoltLaury实验机制考察中国农户应用新技术的风险偏好,发现具有冒险意识的农户采用新技术更早。Tanaka & Munro在乌干达运用HoltLaury机制,发现个人的风险态度和时间偏好也存在差异性[60]。
国内对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较少,较为典型的为周业安等以大学生为实验对象,计测实验对象的风险厌恶和不平等厌恶水平[61]。目前国内仍鲜有此类基于HoltLaury机制的针对贫困群体的风险实验研究,因此,以脆弱性贫困群体为实验对象,应用此类实验机制较大范围的研究我国贫困群体的风险偏好对反贫的影响,将是未来反贫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析思路和框架。
基于以上相关文献的总结和分析,提出一个基于风险与机会的贫困分析框架,如图1。贫困成因可归纳为风险与机会,由风险造成的贫困,进行风险管理,以事前防止富裕群体陷入贫困及原本贫困的群体更加贫困的可能性。针对机会,一方面应加强外部介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应用实验经济学方法了解贫困群体的风险与机会偏好,改变其风险态度,使其把握一切能够改变贫困的机会,最终脱离贫困。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贫困概念及成因的文献梳理,明确了将风险与机会纳入到贫困的涵义中,对贫困可定义为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及没有把握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风险冲击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因素,机会缺失是脆弱群体无法摆脱贫困的重要阻碍。
对风险的有效管理是农户脱贫的重要手段,风险管理是事前的预测和防范,有效的风险管理可将导致贫困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从源头防止贫困的出现,同时也是一种最为节约成本的反贫方法。风险与机会相伴而生,对获得更好生活机会的把握,其实质是风险偏好的不同。借助实验经济学,探讨不同脆弱群体风险偏好对脱贫的影响,将是未来农村反贫困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创新。
(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汪三贵. 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J]. 管理世界, 2008,(11):78-88. [Wang Sangui. Beating Poverty by Means of Development:A Summary and Evaluation of the Experiences of Chinas LargeScale Reduction of Poverty in the Past 30 Years [J]. Management World, 2008, (11):78-88.]
[2]吴理财. “贫困”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分析的贫困[J]. 经济评论, 2001,(4):3-9. [Wu Licai.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Poverty and Poverty Analysis[J]. Economic Review, 2001, (4):3-9.]
[3]叶普万. 贫困概念及其类型研究述评[J]. 经济学动态, 2006,(7):67-69. [Ye Puwan. A Review of Concept and Type of Poverty [J].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7):67-69.]
[4]叶普万. 贫困经济学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 世界经济, 2005,(9):70-79. [Ye Puwan. The Research on Poverty Economics: A Literature Review [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05, (9):70-79.]
[5]胡鞍钢, 李春波. 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3):70-81. [Hu Angang, Li Chunbo. New Poverty in the New Century: Knowledge Poverty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1,(3):70-81.]
[6]李实, Knight J. 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J]. 经济研究, 2002,(10):47-58. [Li Shi, John Knight. Three Poverties in Urban China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2, (10):47-58.]
[7]章元, 万广华, 史清华. 暂时性贫困与慢性贫困的度量、分解和决定因素分析[J]. 经济研究, 2013,(4):119-129. [Zhang Yuan, Wan Guanghua, Shi Qinghua. Chronic Poverty and Transient Poverty in Rural China: Decomposition and Their Determinants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3, (4):11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