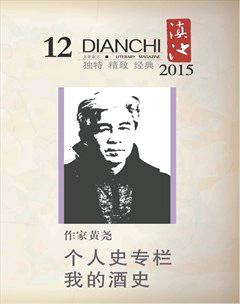风起
东巴夫
天擦黑,街上很热闹。屠大刚肩挎工具包,手提一捆尼龙绳,从前边的小巷斜插过来;没有红绿灯,他站在马路中央,一辆蓝色小汽车擦膝而过,他打了个趔趄,肩往左边一闪,差点儿栽倒;他再穿过一个小广场,过了马路就到了家门口。
屠大刚是一个门窗制作工,他技术好,活儿多,每天都很忙碌。这天大清早,他就接到顾客电话,他要去安装防盗门,早饭是在路边买了个馒头。他一个人一忙就是一整天,中饭没顾得上吃。待活一干完,他就匆忙往家里赶。他妻子叫余欢欢,他俩是赣州同乡,五年前经乡里的媒婆牵线结了婚,婚后她就在家,没出去工作。他们现在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叫倩倩,余欢欢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家照顾女儿。
快到家门口,屠大刚却放慢了脚步,说实话,他有点怕余欢欢。余欢欢三天两头跟他吵架,一天安生日子都不让他过。吵架时,他只是退让,听任余欢欢恶骂,他知道只有等余欢欢把满肚子的怒气喷射出来,她才会停歇,反驳或犟嘴只会让咒骂无限升级。他怕见余欢欢那张脸,他怕她那一抹轻蔑的眼神。但他一想到马上就能看见他那懂事又可爱的女儿,双脚又不觉加快了速度。他做什么怎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女儿,女儿是他的心头肉。
家门口有一个花坛,长着齐腰深的冬青,花坛边有一个三米多高的飞马铜雕,这条街叫打马街。屠大刚走到花坛边上,就看见女儿一个人蹲在铜雕下,玩她最喜欢的橡胶小黄鸭。
“倩倩——倩倩——”喊声刚落下,屠大刚已大步走到女儿跟前。女儿抬头看见屠大刚,脸上笑眯眯的,露出两排小米粒样儿的牙。“爸爸,你回来啦!”“爸爸不在家时,倩倩有没有想爸爸?”他放下工具包,把女儿抱在手上。“我想爸爸啦!我玩了一会儿小黄鸭,我想爸爸!”他笑起来,一脸的褶子沟里粘着黑灰。他用自己的额头顶了顶女儿的额头。
屠大刚放下女儿,一扭头,看见妻子余欢欢赤脚坐在家中央的竹木床上,妻子的头向两腿间弯下,拱起的膝盖遮住了她的脸,她脚边平放着一部新手机,他知道她又在抢微信红包。余欢欢是玩微信红包的专业玩家,这部新手机就是她用抢得红包的钱购买的。
屠大刚放下手里的尼龙绳,发出一声闷响。余欢欢抬头瞄了一眼,很快又垂下头。
“菜买了吗?”声音是从裆部传出来的,瓮声瓮气。
“嗯?你说啥?”屠大刚没听清。
“问你晚上要吃的菜买了没有?”余欢欢的头一抬一垂,丢了一句。
“没买,我刚回来……”
“没买你回来做什么?晚饭吃什么?你吃屎啊?!”余欢欢抬头说了这么一句,她的手指惯性似的在手机屏幕不停往上滑。
“你怎么这样说?我刚回来,手里也没闲着,什么吃屎,屎能吃吗?”屠大刚说着笑了起来,笑得很勉强。
“狗能吃屎,你怎么不能?难不成你还比狗
金贵?”余欢欢板着脸,两眼一横说。
女儿看看屠大刚,又看看余欢欢,嘴撅着,一副紧张又害怕的神情。三岁的娃儿多少懂点事,亲历了父母太多的争吵,只要父母脸色一变,说话的语气一变,她就知道一场争吵即将上演。
女儿拉了拉屠大刚的手,说:“爸爸,我们买菜去吧!”
“你的火气真大,你看,女儿都害怕了。”屠大刚拍拍衣角,腾起一团灰尘。
“滚出去拍!”
屠大刚在门外脱下外套,换了一双拖鞋。他走进左屋的一间内室,那是一个小单间,窗户口对着护城河,他们用来做厨房。他揭开电饭煲,是空的,他从柜下拉出一袋大米,舀了两碗,淘米,擦干锅底的水,放入煲盆中,通电,先煮着饭。
屠大刚牵着女儿的小手到菜市场买菜。晚饭是屠大刚做的,女儿不爱吃米饭,他在饭中蒸了一碗鸡蛋花。开饭了,余欢欢没在饭桌上找他的碴,她唯独这点好,不挑食,吃得顺嘴就行。
晚上八点,余欢欢给女儿洗澡。女儿坐在大澡盆中,玩她的小黄鸭。屠大刚坐在左侧方的一只小凳上,他手里捏着一根烟,却迟迟没有点燃。他看见妻子用毛巾轻轻擦洗女儿的后背,额角上的一绺头发散下来遮住了她的半张瓜子脸,她的嘴唇,红润,翘翘的,充满挑逗、诱惑,她尖尖的下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在灯光照射下,亮晶晶的,她的皮肤白嫩得能捏出水来。屠大刚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胳膊,又看了看自己裸露的胸膛。正如别人说的那样:他看起来比妻子老十岁。而实际是余欢欢跟他同年,还大他三个月。他想,他毕竟是男人,挣钱养家是应该的,辛苦点累点,也是理所当然的,看起来老些就老些吧,大男人,年轻也不能当饭吃。他看着妻子,心想,真是个小美人。“真好看!”他轻声说。
“你嘀咕什么?”余欢欢说。
屠大刚回过神来,吧唧一下嘴巴。他说:“老婆,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有什么话直说,别喊我老婆,我听着恶
心。”“怎么就恶心了?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嘛!”“喊我名字,别喊我‘老婆!”屠大刚方才流露出的混合着各种情愫的目
光,突然就黯淡下来,好多个话语涌到舌尖,一阵乱撞,找不到出口。屠大刚紧闭嘴巴,头往前倾,上身僵硬,像一块化石,搁在凝滞的空气中。
余欢欢把女儿从澡盆里提溜起来,用挂在脖上的干毛巾给女儿揩身子。见屠大刚一声不吭,像石墩似的杵在那儿,她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刚才要说什么?”屠大刚还没融化开。他没反应,依然保持那
个站姿。“哎!神经病!”“你说啥?”“你刚才要说什么事?”“噢,我原想跟你说,我想买块机械手
表。”“买手表做什么用?你兜里不是揣着手机
吗?”屠大刚摇摇头。“算了,不买了。”“那是你自己的事,你爱买不买,不用问
我。”“不买了。”余欢欢把女儿从澡盆抱出来。屠大刚慌忙把
准备好的睡衣递过去,余欢欢腾出一只手接住。屠大刚弯腰,想把洗澡水端出去泼掉,他的手无意中碰到余欢欢的小腿肚。
“啊——啊——”余欢欢尖叫,左脚啪啪啪跺地。“怎么啦?怎么啦!”屠大刚忙问。“你不要碰我,不能碰到我!”“我碰到你哪儿啦?”“你不要碰我!脏!脏!……”说着,余欢
欢急得哭起来。女儿被她光屁股放在一边的椅子上坐着。
屠大刚把端起的澡盆往地上一丢,许多粒水珠荡弹出来,一泼水浪出来打湿了他的鞋。
“我怎么脏了我,我是心里肮脏,还是身体肮脏?我不过是手指头不小心碰到了你,这是手指头又不是针,你至于搞得一惊一乍吗?”
“你要是再碰到我,我就把皮肤用刀割下来,你碰到哪我就割哪,我就是嫌你脏,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想。”
余欢欢泪渍未干,就露出一副凶恶决绝的面孔。
“这些都是你的心里话?究竟因为什么让你发这么大的火?我一直弄不清,你现在已经失控了,疯狂了,一点理智都没有了,你知道吗?”
“你只要同意签字,我们离了婚,这些就都不存在了。”
女儿小声抽泣起来,她最怕从父母口中说出“离婚”两个字,小手背不停地抹眼泪,晚饭前那会儿她就害怕,想哄着爸爸,让他不说话,让妈妈干说一会儿,等她气消;她不知道怎么劝说,去年他们吵架,她大哭,她大哭也不能阻止什么,反而会招来妈妈一个大耳光,她就不敢嚎哭,她真是害怕,很无助,小肩膀一颤一颤的,嘤嘤地哭。屠大刚看了女儿一眼没说话。
“你就死赖着,不签字,害死我了,我跟你说。”
余欢欢给女人穿衣服。屠大刚绞心绞肠地气,胳膊一阵阵发麻。
“你老把‘离婚两个字放在嘴边说,离了婚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不签字不同意离婚,是在给你时间,给你机会,让你好醒悟。我心疼你,心疼女儿,你感受不到吗?这几年我一直在奋斗,为了这个家,你是看得到的,你扪心自问,我有没有让你吃一丁点儿苦,再说我们过得也不比别人差,房子盖了,你说喜欢车,车也买了,你说不愿意出去打工,我依你,你在家玩,我养得起。我做的这些你都视而不见,反而三天两头吵着离婚,你是闲出毛病来了?”
“别说了,你到底还是不懂,什么都不懂,我们压根就不是一路人,你知道吗?不是一路人啊,怎么能一路走下去?从结婚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错了,这些都不是我要的。”
“你现在说跟我过不下去,离了婚你再找个人,那个人就跟你过得下去?你自己的性格你的怪脾气你自己不清楚?这世上,除了我屠大刚,谁还能容忍你?啊!你说说,你找出一个来让我看看。你把我的宽容当成迂腐无能!你仔细想想。”
余欢欢一时语塞,屠大刚的话击中了她的要害。她是那样的强势刚硬,不打一点儿弯,不服一点儿软。脾气很不好,怒火一旦爆发出来,谁都安抚不了,亲爹亲妈都拿她没法子。在她十二岁那年,因点小事,她觉得母亲在她与弟弟之间偏袒了弟弟,一气之下,她连夜跑出了家门,她往孤山上跑,往乱坟岗里钻。父母慌了,一时寻不到,就喊来村里的亲戚友邻,执手电筒打火把,村里村外山上山下寻了一夜,才把她给找出来,她就藏在坟岗边的一棵大树下,不哭不闹不作声,就悄悄坐在那儿,她也不知道害怕。跟屠大刚结婚后,余欢欢也跑过几次,可这是在城里,这么大,屠大刚上哪儿找?一个人成心想躲你,不必天涯海角,她就隐藏在你眼皮底下,你没办法找到她。屠大刚找了一回两回就不找了,找也找不到,就随她去。好心朋友提醒他说,一个小妇人半夜三更在街上游荡可不安全,出点啥事不好收场。屠大刚坐在椅子上,两眼一闭,像在幻想什么,然后突然睁开,盯着面前的墙壁说:“我有什么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照顾好女儿,女儿是我的,我管得住。”一般情况下,余欢欢夜里离家出走,第二天清晨,她自己就回来了。
他们的住房不大,还要堆一些货物,一楼有一半分为工作间,一半是生活区。他们搭了个阁楼,平时余欢欢和女儿在阁楼上睡,屠大刚在一楼睡。夜晚临睡前,屠大刚就把一米五宽两米长的工作台收拾一下,铺上棉絮,这就是他的床。
夜里九点半,他们在各自的床上睡下。屠大刚平卧在床上,头枕在两条叠加的胳膊上。他睡不着。屋里异常安静,那些白天惊叫的机器:切割机、钻孔机、点焊枪、喷钉枪,统统安静下来,变成一堆冰冷的铁;菜刀睡着了,锅和饭铲挂在墙上;筷子入笼,碗压着碗,都睡死了;用手拍拍被子,也没什么特别的声音,眨动眼皮,那是皮肤摩擦碰撞发出的声音,很细微的,像手心在水面平滑地走过,多么可爱的纤细之声。屠大刚想买一块机械手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在夜深时,他可以把头枕在手心里,侧身倾听手表秒针“铮铮铮”走动的声音,像一条连成线的水珠不停地滴打在破瓦上。那是时间的脚步声,他知道这似乎暗示着,每个人都应该珍惜眼前的一切,珍爱自己所拥有的。真奇妙,他就想听听,一个人的时候,在夜深,在无眠时。
可惜他没有得到这么一块机械手表。
“唉……”这时,屠大刚听到阁楼上的余欢欢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声。原来她也醒着。
屠大刚抬起脑袋,立直了耳朵,听阁楼上的动静。余欢欢翻了一下身,床板咯吱一声响,过了一会儿,床板又响了一声,余欢欢又翻身过来,接着她吧唧了一下嘴巴。屠大刚翻身下床,往茶杯里倒了一杯凉水,小心翼翼爬梯子上阁楼,上至楼口,他停下来,说:“想喝水么?我倒了一杯。”
余欢欢从里面伸出一只手,接住水杯,咕咚咚喝了大半杯,把水杯递出来,屠大刚连忙接住,快步顺溜地下了梯,把水杯放在饭桌上。
屠大刚没有回到自己的床上,他稍作停歇,也就是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接着,他手扶梯脊,悄悄往阁楼上爬,像做强盗似的,不敢弄出一点声响;他爬到阁楼口,单膝跪在边缘上,一探身,钻进了阁楼。他想碰碰婆娘。给娃儿洗澡那会儿,对屠大刚最后说的那些话,这余欢欢没有反驳,刚才给她递水,她也没拒绝,屠大刚以为余欢欢应该是消了一些气,心里也应该有一点儿触动。他想,他再趁热打铁,好好和余欢欢做一次爱,身体上再敲敲打打交融一番,这场争吵带来的僵局应该就暖化了。
可谁曾想,屠大刚的手才摸到被褥,他的脸啪地一声,重重挨了一脚,他两眼冒金光,脑袋
也碰到了床头的隔板上。“哎呦!你踹我干吗啊你?”“你偷偷摸摸上来做什么?”“你是我女人,你说我上来做什么?我想你
嘛!我想陪你睡觉!”“你滚开!听到没有?滚下去!”“又怎么了?你要闹到什么时候?”“谁跟你闹?你想女人,你身体需要,你去
找小姐啊!扒弄我做什么!”
扯了布帘,光线微弱,但还是能看清余欢欢那张冷绝僵硬的脸庞,她坐在那儿,被褥抹胸缠在身上,细嫩的脖颈泛着幽幽的光。
“你再不下去,我就用脚把你踹下去!”余欢欢冷冷地说。“这样闹有啥意思!”屠大刚说了一句,他
挪动屁股,从阁楼上溜了下去。屠大刚重新躺到自己的床上。“是没什么意思,老拖着有什么意思,想有
意思就同意离婚呗,你好,我也好……”从阁楼传来余欢欢一声冷笑。“真到那一天,我也认了,什么我都不要,我只要女儿。”屠大刚无奈地说。“你凭什么要女儿,女儿是我生的。”余欢欢用手一捶床板说。“没有我,你一个人就能生?女儿是我的命根子,别的东西我可以不要,包括财产全给你。 ”
“你别做梦了,我的东西你是得不到的,我宁愿亲手毁掉也不会留给你,你要女儿,我就掐死女儿,让你得不到。”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屠大刚从床上
弹起来,他知道余欢欢说得出做得到。“你想要什么,我就偏不让你得到……”“疯子,你就是个疯子……”屠大刚三下两下爬上阁楼,把余欢欢从被窝
里捞出来,抱到阁楼门口,像夹草把子似的,把余欢欢拦腰夹在腋下,带到一楼,两只手抓住余欢欢的屁股,把余欢欢扔到自己的床上。余欢欢拳打脚踢,像个耍脾气的熊孩子,她在屠大刚的床上打了个滚,一把坐起来,指着屠大刚的鼻子骂:“你这个畜生!”
“骂我畜生,你这个蠢女人,真不知好歹 ……”
屠大刚说着,猛一吸气,唰地一声跳上床,“啪啦!”一声把余欢欢扳倒,两只手像铁钳,一下子撕开余欢欢的上衣,余欢欢慌忙用手遮住奶子,他又十分迅速地扯开余欢欢的内裤,余欢欢不再遮挡什么,光身子大喊:“你疯了?”
屠大刚没说话,他很快褪掉身上的衣裤。两个人光溜溜互相对视着,屠大刚的喘息越来越重,他的身体就像一架出了故障的机器。余欢欢感觉浑身冷,瑟瑟发抖。屠大刚的心像一张撕烂的纸,他迫不及待,他没法控制自己,他浑身的血在往脑帽顶上冲。他伸出右手,抓住余欢欢的脚,往他跟前使劲一拖,余欢欢已经坐在他脚下,他熟练地爬上了她的身。
毕竟是两口子,都是熟悉的。余欢欢刚开始还挣扎,尖骂,用手掐屠大刚的胳膊,那儿鼓捣了几下,余欢欢就安静下来了,低低地呻吟,不时用牙咬屠大刚的肩膀,屠大刚浑身是劲儿,他越干越有劲。
可冷不丁地,余欢欢在兴奋中说了一句:“天啦!我要告你,告你强奸……啊!”
屠大刚像个鼓胀胀的气球,被人用针一扎,扑哧一声,泄了气。他一把倒在床上,两眼怒睁,顷刻,他眼里的气焰也萎下去了,代之以两行浊泪流出,打湿了他的耳朵。
余欢欢的欲火被撩起来,烧得正旺呢!她旋腰爬起来,一屁股坐到屠大刚的肚皮上,噼噼啪啪又折腾了半个钟头,这才翻身下马,歪身躺在床的另一头,忽儿,她低声抽噎起来。
天蒙蒙亮,屠大刚打开门,天空阴沉。晨风裹挟着落叶,呼啦啦向他袭来,街上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屋顶黑黑的,马路冷冷的,斑驳的墙壁还是那样陌生,他的心突然很痛,他觉得很难受。
天啦!这是一个杀人的深秋。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