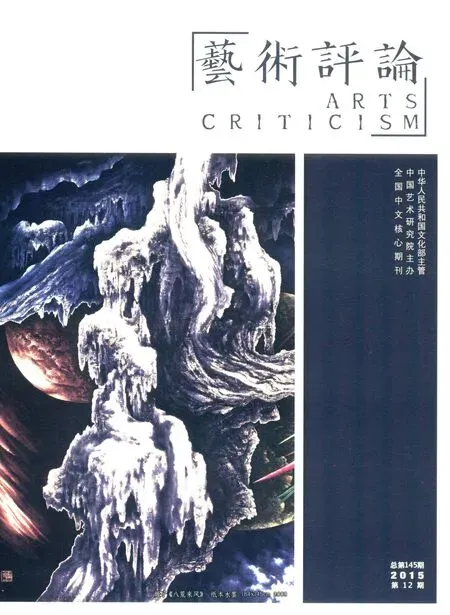《惊奇的山谷》与彼得·布鲁克戏剧
李 英
《惊奇的山谷》与彼得·布鲁克戏剧
李 英
2015年10月29日晚7∶30,彼得· 布鲁克和玛丽海伦娜·伊斯坦尼共同编、导的新作《惊奇的山谷》(The Valley of Astonishment)在北京9剧场进行了彩排演出。此剧于2014年4月29日在巴黎首演,随后开始世界巡演。作为今年中国乌镇戏剧节的闭幕大戏,在京演出之后还将奔赴津、沪,分别为第二届曹禺国际戏剧节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画上点睛之笔。
一
《惊奇的山谷》是继《情人的衣服》(2012)之后第二部在国内上演的布鲁克戏剧。在落座的瞬间,经典的布鲁克式简约舞台便扑面而来:一张带轮的方形木桌和四把椅子都是单一的原木色;一台电子琴和一个方形衣架;除了常规舞台照明灯,只有两盏萤火虫似的落地灯[1]。有观众在演出后问“萨米”的扮演者凯瑟琳 · 亨特:巴黎的演出是否也使用了如此简单的舞台道具?答案是肯定的。
极简主义(minimalism)是布鲁克建立理想观演关系的前提。把戏剧还原到最基本的观演关系,前提条件就是清除一切不必要的舞台元素,抛弃一切外在的戏剧关系,从而取得形式减省而内容深刻的舞台效果,也就是阿托德在《残酷戏剧》中的宣言:“没有布景,也不需要布景。”[2]布鲁克深受阿托德和格洛托夫斯基质朴戏剧理念的影响,1947年以来的舞台设计总体趋向是越来越精粹、越来越简练。他说:“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是一出戏所需要的一切。”[3]
极简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道具和一切戏剧工具减到最少,巴黎“北方剧院”(Theatre des Bouffes du Nord)的舞台设计堪称极简主义的典范,一切舞台置景都用未加修饰的原始材料。1990年,《李尔王》在光秃秃的舞台上演出,除了一个粗糙的木质王座和一个可以随时上下移动的长凳,舞台上几乎没有任何布景,场景也几乎没有更换过。在《摩诃婆罗多》中,红地毯表示舞台,简单的竹枝代表弓箭,两个货仓的货板首尾相连替代敞篷马车。而《惊奇的山谷》中的科学仪器等道具则都是假想的。此外,《惊奇的山谷》也像《哈姆雷特》等剧作一样,尽可能地减省了演员。三位主演和一位乐手共扮演了9个角色,例如:艾克多·弗洛雷斯·小松扮演画家,凯瑟琳·亨特扮演记忆超人萨米,马尔塞洛·马格尼扮演中风患者;在认知科学院的场景中,当一个人扮演患者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就穿上白大褂扮演医生。
现场的年轻观众对“扑克牌魔术”中演员的即兴表演以及与观众的互动非常感兴趣。实际上,与《摩诃婆罗多》《奥格哈斯特》《IK》和《飞鸟大会》等实验戏剧相比,《惊奇的山谷》带给观众的新奇的观演体验只是小巫见大巫。布鲁克在《空的空间》中提出,理想的戏剧应该是灵活、流动、变化、创新的即时性艺术,实验戏剧的目标就是建立以演员为主导、以观众为主体、以体验为基础的新型观演关系。演员是戏剧表演的中心,也是戏剧体验的核心,演员的表演激发出观众的情绪,让观众和演员在剧场之内共同进入一种非理性状态,这就对演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布鲁克在演员训练上提出“从零开始”的理论,在表演技术层面上要求演员一方面想方设法减少外在肌肉、想法、个性等与角色之间的差距,如“扑克牌魔术”这种即兴创作不是为了表现演员的自我,而是为了更真实地塑造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艾克多·弗洛雷斯·小松扮演的画家在乐手的自由弹奏中随性地舞动画笔,绚丽的色彩和充满想象力的表演令观众为之动容。
布鲁克的戏剧是抽象的,既不是填满舞台的实物,也不是演员本身或表演。剧
场是演员与观众相遇那一刻的内心反应。他将戏剧舞台处理成空的空间,让导演、演员和观众的心灵具有无限的包容力、想象力和时间感。
二
《惊奇的山谷》的创作灵感来自史诗《鸟的集会》。早在1975年,布鲁克就亲自将这个故事改编为实验戏剧《飞鸟大会》,并且在北风剧院试演部分片段,1980年分别在“妈妈剧院”和澳大利亚上演。布鲁克在2003年的采访中谈到,《飞鸟大会》是一个讽刺性的寓言:“一群鸟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寻找它们的国王。在寻找的过程中,一些鸟失去信心,后来死去了;那些幸存下来的发现它们自己就是国王——或者神的化身。”“在世界文学中,很少有这样的杰作真正能成为人类本质体验的见证者”,“它将完全超越我们的洞察力。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飞鸟大会》。它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4]
《飞鸟大会》借百鸟朝凤的历程描述了对人性的体验。盛年的布鲁克把人性阐释为未知或不可知,而在《惊奇的山谷》中,这位如今90岁高龄的艺术大师用三个小插曲对人性做出了明确的阐释:一无所有的人、凤凰涅和对母亲的记忆。人性不再由《哈姆雷特》《李尔王》和《摩诃婆罗多》中的英雄、国王和领袖来呈现,每个人都是一个奇迹,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平凡的百鸟在朝觐的历程中饱经艰辛与磨难,最终发现它们自己就是重生的凤凰,平凡的人们可以在词汇、图画、音符和颜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最终回到家园。
由于语言、文化和个人阅历的差异,多数中国观众难以体验到媒体对《惊奇的山谷》演出效果的盛赞:“《惊奇的山谷》是一次进入神秘的惊奇的人类大脑的万花筒般的旅程……我们开始了大脑迷宫的探险……生活的秘密在音乐、色彩、味道、想象、回忆中蔓延开来,我们往返于天堂和地狱之间。”但不可否认的是,布鲁克在《惊奇的山谷》中通过“通感”(synesthesia)这一认知现象阐释主体功能和主体位置,在人性主题的处理上比《飞鸟大会》更加深沉而稳健,在语言实验上比《奥格哈斯特》更加踏实而有效。
主人公萨米拥有非凡的记忆能力,她能复述出一系列看似毫无关联的词语和数字。认知科学的专家发现萨米采用了联想记忆法,在无意识中把词汇和数字转换为图画,然后把图画放在想象中的街道、院子和其他场景中。另一位主人公卡尔的大脑则在颜色和音符中转换:每当他看到颜色的时候,颜色会自动变成音符,形成交响乐。布鲁克的崇拜者对此剧中的语言、图画、颜色、音符和味觉等元素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很容易联想到《奥格哈斯特》的原生态音调,以及《摩诃婆罗多》中的大地灰、火焰红等颜色和画面。
《惊奇的山谷》的奇特之处在于,主人公的大脑在不同的感官体验中游走、转移——每个单词和数字都是一幅画,每个颜色都是一个音符,每个音符都有一种颜
色,每个颜色都有一种味道。词汇、数字、颜色和音符在主人公的大脑中形成一个滑动的能指链。在萨米和卡尔的精神之旅中,图画取代词汇和数字、音符取代颜色,一个能指取代另一个能指在连环中的位置,产生了创造性——萨米把词汇转换成图画,图画的意义就超越了词汇的意义;卡尔把颜色转换成音符,音符的意义就超越了颜色的意义。两个能指的结合构成隐喻,通感具有隐喻的功能,指出主体位置和主体功能。因此萨米说:“无论我的精神去过哪里,最终总会回到童年的家。”
萨米和卡尔拥有非凡的能力,是普通人眼中的“奇迹”(phenomenon),然而这种天赋同时也给他们带来痛苦。萨米在失去了记者的工作后不得不在马戏团里表演真人秀,但记忆表演使她更加脆弱,她说:“我把词汇变成图画,放在街道上,可是表演让街道上都放满了图画,我怎么才能忘记呢?”医生建议萨米在表演中只记忆数字,把数字放在一块想象中的黑板上,可是不久黑板也放满了。马戏团的经理让萨米把黑板上的数字写在纸上,然后把纸烧掉,这也无济于事。萨米痛苦地说:“我的记忆被塞满了。”可以说,《惊奇的山谷》为拉康的隐喻概念提供给了一个完美的脚注:“症状是一个隐喻。”[5]
萨米辞去了真人秀表演,把记忆中的词汇和数字写在一个笔记本上送给认知科学专家,并且希望未来能够把大脑捐献出来做研究,帮助发现精神的秘密。这也是萨米在结尾那句独白的意义:“就算世界不再存在,就算人类全部消失,也不能否定一条蚂蚁的断腿,也不该停止期待雨滴。”萨米把词汇变为图画,图画总能帮助萨米回到童年的家园。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我们去过哪里,我们总会回到家园,找到主体位置,获得主体功能。
观众很难在《惊奇的山谷》中发现仪式戏剧、跨文化表演和东方主义等标签。把宏观的人性命题阐释为主体位置和主体功能,在主题上已经超越了种族、民族和文化等概念。把语言实验具体化为对通感这一认知现象的阐释,使《惊奇的山谷》更有的放矢,也更接地气。创新戏剧语言是20世纪西方实验戏剧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主义……关注‘自由的文字’,达达主义则采取无意识的行动,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字游戏’活动。”[6]音乐家瓦格纳、哲学家尼采以及残酷戏剧、质朴戏剧、超现实主义和荒诞派戏剧,都对现代西方语言的表意功能提出种种质疑,认为语言扼杀了戏剧的活力。曾几何时,布鲁克的语言实验最积极也最极端。他彻底放弃现有语言系统及语言的表意功能,重新创造出由声音构成的语言。他说:“我们必须完全取消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语言。”[7]
《飞鸟大会》研究“鸟的声音、与发音清晰的语言相对的音节发音、纯语言、法语或英语之类的语言。”[8]《奥格哈斯特》则试图唤醒前逻辑状态。与戏剧同名的“奥格哈斯特语”既不是盎格鲁撒克逊语,也不是盖尔特语、古希腊语、古波斯语或原始印欧语。“演员们完全用新的发声方法来说话,造成一种声音和词语交响的效果,以突出音乐的国际性。or,gr和tr是硬音,sh
是软音——五个元音从一个滑到另一个,一起咬合成一个词语。”[9]它摆脱了现有的语言系统,用声音直接表达行为和情感。语言与戏剧分离。
布鲁克的语言实验震撼了“剧本中心论”,并且进一步推动“表演中心论”“导演中心论”向“观众中心论”转变,但实验戏剧的观演效果却差强人意。摆脱语言或语言的理性特征,轻则让观众兴趣索然,重则干脆赶走了观众,让戏剧走进了死胡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惊奇的山谷》无疑是成功的。布鲁克把语言实验具体化到通感这一认知现象,既捕捉到其非理性特征——不可知、不可解的潜意识存在,又带给观众温暖的希望——精神之旅的起点和终点总是童年的家园,在那里才能够忘记,才能得到解脱。
有批评认为布鲁克的戏剧缺少创新,只是把现代戏剧的若干方法笼统地搬上舞台。认同也好,否认也罢,布鲁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理论家或批评家,他是一个敏于思而勤于行的舞台导演。诚然,《空的空间》在理论创新性上无法和质朴戏剧、残酷戏剧、表现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相媲美,但布鲁克是现代西方实验戏剧的集大成者。在他的戏剧中,格洛托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阿托德等大师的影子总是若隐若现。观众能够在他的戏剧中发现整个现代西方戏剧所关注的最基本问题,如戏剧的本质、理想的戏剧形式以及现代戏剧的实验精神和创新意识。
《惊奇的山谷》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没有超越《摩诃婆罗多》等巅峰之作,但其表演却赢得了跨文化观众的欢迎和认可。如果说20世纪中期,荒诞派戏剧通过荒诞手法阐释存在主义哲学命题,取得形式和内容的统一,那么21世纪之初,布鲁克以通感为切入点阐释主体位置和主体功能,又一次把形式和内容有机结合起来。
《惊奇的山谷》短小而精致、简洁却深刻。
注释:
[1] “北京9剧场”的演出场景。
[2] 安托南·阿托德.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M].桂裕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87.
[3] 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M].邢历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3.
[4][7][8][9] 玛格丽特·克劳登.彼得·布鲁克访谈录(1970-2000)[M].河西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75;95;177;52.
[5] Lacan, Jacques.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2: 175.
[6] [法]布勒东.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丁世中译.//柳鸣九主编. 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01.
李 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雍文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