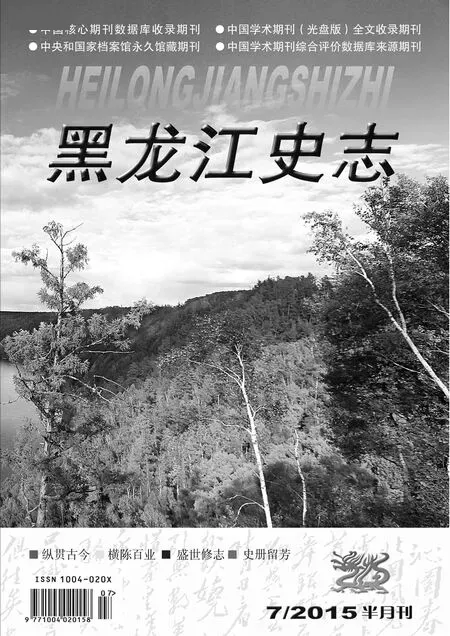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几个问题
段光达石恒林
(1.黑龙江大学;2.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为进一步推动哈尔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加强哈尔滨历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哈尔滨历史研究中,城史纪元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
要研究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首先要搞清城市与乡村的本质区别。只有把握了城市与乡村的本质区别,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城市的多样性和时代性;才能理解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时代条件下城市形成过程的非一致性及各城市的诸构成因素的不同顺序或主次位置的不同;才能避免在判定城市形成过程时做生硬的比附或规定。
城市与乡村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人类聚落形态。社会发展史表明,一个地区最初的城或都邑往往是其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的标识。尽管城通常都是在乡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自城市与乡村分离之后,两者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甚至是尖锐的对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城乡差别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别从未消失。正是这种差别,决定了城市历史与乡村历史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把城市的历史当成乡村历史的自然延续或延伸。当然,古今中外的城市大都是在乡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城市与乡村的这种联系并不能弥合二者之间的差别或使两者在性质上趋同,城市恰恰是因为在乡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之后,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才有别于乡村。这如同人类从猿进化而来,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人与猿之间的本质差别,将人的历史与猿的历史等同起来一样。城市的形成过程就是其自身摆脱乡村状态的转换过程,城史纪元就应该是准确反映其摆脱乡村状态或与乡村状态分离的“分水岭”,是乡村向城市转换过程完成的“临界点”或新的城市形态开始的“起始点”。
二
有学者认为哈尔滨的城史纪元应从金代算起。
确定城史纪元不仅需要进行共时态的横向比较,搞清城乡区别、而且还需要进行历时态的纵向考察,明确城市自身的发展轨迹。无论是以金代古城为起点向后延伸,还是以现在哈尔滨为起点逆向上溯,都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非连续性断裂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城市既然有其形成起点的发展过程,自然也有其衰落的过程和消失的终点。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长生不死,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这恐怕是没有疑义的事实。如果认为金代故都与现代的哈尔滨属一脉相承,城史纪元应开始在金代,那么如何解释这些古城在元、明、清三朝七百多年的萧条、停滞和消失。一部哈尔滨城市发展史总不能只写金代和清末开始的城市如何繁荣,而留下七百余年的空白去让人“回味思索”吧?事实上这些金代故城以其遗址早就为自身的历史划上了句号,现代的哈尔滨与这些古城不具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其次,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都还不能证明哈尔滨地区的金代故城与现代哈尔滨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哈尔滨行政所辖地区的历史归结为哈尔滨这座城市自身的历史,也就是说现代哈尔滨地区的城市发展史决不等同于哈尔滨这座城市自身的历史。很显然,哈尔滨行政辖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因多种原因而不断扩大或缩小(如呼兰县、双城等相继归属哈市),因而哈尔滨地区城市发展史的空间范围也在不断变化,而哈尔滨这座城市作为哈尔滨行政区划的中心则是稳定的,所以,哈尔滨地区的城市发展史可上溯至金代,但哈尔滨的城史纪元则不能从金代算起。
退一步讲,如果以哈尔滨地区的古城出现时间作为哈尔滨的城市发展史的上限,那么城史纪元也不会在金代,而应大大提前,哈尔滨东郊的黄山就有北魏勿吉古城,继为辽、金沿用。
三
1905年10月,滨江关道的设置是哈尔滨的城史纪元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城市的形成和行政建制(设治)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一定规模的城市是行政建制(设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作为依托是不可能设立行政建制的,由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转化为有行政建制的城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设治(设市)。行政设治通常要按照严格的行政法规程序完成,主要有三个基本内容:1.明确的行政管辖区域,2.拥有管理和司法权力的行政管理中心,3.包括行政级别和行政隶属关系的行政建制。
有清一代,东北地区作为满清的“龙兴之地”其行政设治与内地不同,对旗人实行的是按八旗军制设置、即以将军衙门、副都统衙门、协领衙署为地方各级行政建制为主的军政体制。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边疆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大量流民的迅速涌入,满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又陆续设置了一批府、州、厅、县等民政机构,从而在行政建制上形成了旗治与民政并存的双重行政管理体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清政府在东北地区还增设了一些处理新出现的特殊问题的民事行政机构,如隶属于黑龙江将军衙门的黑龙江清丈局、厘金总局、木税总局等。在哈尔滨地区1899年设治的吉林铁路交涉总局、1902年设治的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和1905年设治的滨江关道都是“专办吉江两省铁路交涉并督征关税”的特殊行政机构,而不是按行政建制设治的拥有明确管辖区域的地方政权,况且滨江关道首任道台杜学赢在1906年5月11日才到任视事。
就其本质而言,吉林铁路交涉总局、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和滨江关道衙门都是中国政府批准设治的行政机构,并无根本上的差异。如果说“这两个交涉局实质上是在俄人干涉与控制之下的行政机构”,那么1905年10月哈尔滨关道设治后,哈尔滨绝大部分市政管理权依旧被沙俄中东铁路管理局非法控制的事实难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吗?
毋庸讳言,1905年10月前的哈尔滨作为近代城市已经形成,只不过是一个中国政府尚未正式设治、被沙俄殖民统治者非法控制而饱受屈辱的城市罢了!所以,在确定哈尔滨诞生日——城史纪元的时候,必须把握其自身历史发展中各种极为特殊的因素,否则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
四
有学者认为1905年12月中日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哈尔滨开埠通商应为哈尔滨城史纪元。
但是,哈尔滨作为近代城市在1905年之前早已形成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以1903年为例,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管理局所在地已经成为全线通车的2498公里的中东铁路的枢纽;这一年哈尔滨的人口据有关统计,香坊(老哈尔滨)人口已经达到4688人,南岗(新市街)23040人,道里(埠头区)16848人,此时道外(傅家甸)据单士厘在《葵卯旅行记》中的记载:“居民约万户······”;主体人口所从事的是建筑、机械修造、木材加工等非农业产业以及商贸、金融、文教等非生产性职业;原来分散、无序的地域己经向集中、有秩序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工厂、码头、车站、银行、医院、教堂、学校、气象站、俱乐部、警察局、商行、店铺已经纷纷出现……如果说1905年哈尔滨这座近代城市才“诞生”,恐怕与历史事实出入太大。
因此,在探讨哈尔滨城史纪元的时候,我们还应在把握好城市与乡村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分清城市的形成过程和城市形成后的早期发展过程,前者是由乡村向城市转化的质变过程,后者是新的聚落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是量变的过程,而这两个过程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五
客观地说1898年中东铁路的修建,直接促使哈尔滨从松花江畔若干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的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结构的村落中,骤然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现代化大都市。
那么,哈尔滨的城史纪元应在何时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搞清哈尔滨作为城市是何时基本形成的。因为城史纪元作为城市历史的起算年代,也就是城市自身历史的起点或开端,自然应是城市形成的标志。城市作为一种新的聚落形式,首先是作为乡村聚落的对立物而存在的。近代以来,城市与乡村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各自主体人口的生活方式不同,即城市生活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乡村中的主体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并通过参加农业生产,直接获取农业生产物及用农业生产物换取其他生活资料来维系自身生活;而城市的主体居民则以从事工商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或以非生产性职业工作为主,以间接的方式——交换的方式来获取农业生产物和其他生活资料来维系生活。马克思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确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马恩选集1卷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作为近代城市,至少在三个方面与乡村有着本质的区别:1.人口的集中性,指一定地域空间的人口达到远远超出乡村的密集程度和规模;2.居民的社会性,指常住人口不再是按血缘或宗教联系而是由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所组成;3.劳动力的非农业性,指常住人口多以从事第二、三产业为主。
所以城市与乡村这两种居住形态一经分离,便各自按自己的内在规律运行,而生活方式即维系生活、摄取主要生活资料方式的不同则成为区别城市与乡村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的形成过程就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换过程,城市的形成就是这种生活方式转换过程的完成或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确立。
在哈尔滨城市形成过程中,由原来以传统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过渡或转换进行的相当迅速。1898年以前的哈尔滨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区域。1898年6月,随着中东铁路工程局迁至哈尔滨和中东铁路的全面开工修建,这一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大批俄、华人口通过各种渠道迅速汇聚于此,使这里的人口呈几何级数骤然增加。1898年哈尔滨究竟有多少人口,目前尚未发现准确可靠的记载。但光绪24年2月29日,东省铁路公司造路总监工茹格惟志就与中国人蔡连璧“订立合同”由蔡“于本年夏间招雇工头九十名,雇带人夫一万五千名”,前往吉黑筑路,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曾为此转饬沿途地方官“勿行拦阻”(1)。同时俄国人一到哈尔滨也能马上从周边地区招募劳工,这样加之当地原有人口,1898年底,哈尔滨的人口总数估计在1.5-2万之间。其次,这里随着铁路工程局开始大量征用土地,原来的分散、无序的地域状态开始向集中的有组织的城市地域模式和空间结构演变。1898年当年俄国人就曾制定了香坊规划,并在埠头、新市街、香坊进行了最初市区规划,修建了若干道路、桥梁。与此同时,工厂、银行、车站、码头、气象站、教堂、学校、俱乐部、商行、店铺纷纷建立。第三,这一地区的主体人口的生活方式,即人的维系生活、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筑业、机械修造业、木材加工业等非农业产业和商业、金融、文教等非生产性职业开始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总之,1898年哈尔滨地区骤然增加并相对集中了大量人口,随着这一地区逐渐向城市空间格局和地域模式的有序演进,在当年基本完成了由原来的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换,城市生活方式在这一地区的确定标志着哈尔滨从此成为一种新的聚落形式——城市。哈尔滨的城史纪元自然应当是1898年。
六
哈尔滨这座城市是否形成于1898年之后呢?
城史纪元作为城市自身历史的起算年代,自然是城市形成的标志。如果我们不否认二者之间的共时态关系,那么,对城史纪元年代的不同选择实际上就是对哈尔滨城市形成时间的不同认定。
我们要在把握城市与乡村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分清城市的形成过程与城市形成后其自身的早期发展过程。就城市的早期历史而言,这两个过程极易混淆。一般说来,前者是由乡村状态向城市的过渡。以主体人口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换为主要内容,是质变过程。后者则是量变过程,是新确定的生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如前所述,1898年哈尔滨地区的主体人口,在不断有序化的地域范围内,完成了生活方式的转换。作为这种转换的外在表现就是以中东铁路工程局为主的各类工业企业、以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为代表的金融商业机构及全新的文教设施等近代城市所特有的功能组织的出现。1898年以后,无论是铁路全线通车,还是开埠通商,或是城市功能组织增加,都只是对1898年确定的新的生活方式或新构建的城市社会整体框架的量化的肯定、完善和发展。所以,以1898年作为城史纪元是对哈尔滨这座城市作性质上的界定,若以1903年或1905年作为城史纪元则只能是对其城市发展程度的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中枢,是沙俄在华施行殖民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因而从形成之日起便带有相当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由于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特殊的外力和诱导因素的作用,开始其特殊的城市形成过程的。这样在其急促而又短暂的转换过程中,其城市诸构成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出现顺序倒置的结构失衡。例如,一般情况下,城市作为一定地区的政治中心其行政建置往往被视为城市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1906年以前,哈尔滨地区却没有明确的行政设置。直到1906年清政府才在此设立滨江道。但是,仔细考察哈尔滨的早期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从城市规划,到基础设施的修建,从违反《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而派驻在哈的俄国“护路队”指挥,到华俄道胜银行非法在哈发行货币,均由中东铁路工程局操纵,中东铁路工程局实际上就是当时哈尔滨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事实上,1906年滨江道在哈设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哈尔滨的市政管理大权仍操纵在中东铁路管理局手中。所以,在确定哈尔滨城史纪元时,必须把握其自身历史发展中极为特殊的多种因素,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毫无疑问,哈尔滨是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而问世的,不像大多数中国城市那样在传统形态的基础上开始其近代化过程,没有经过较长的积累、准备,而是在相当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其城市形成过程。
七
城市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搞了建城庆典。应该说这对于加强当地文化发展与建设,弘扬地方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即便是所谓一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之举也是值得称道的。但是这一切必须以对历史事实的正视和尊重为前提,因为对历史事实的漠视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在探讨确定哈尔滨诞生日——城史纪元的时候,许多人总不免担心与沙俄侵华的产物中东铁路联系起来,刻意回避哈尔滨城市历史上的“耻辱”。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完全没有必要。众所周知,1840年英国殖民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满清帝国的大门,但中国近代史也就由此开始。难道我们也应该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1840年的屈辱而提前或拖后到没有屈辱的年份吗?难道以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张目,或者是无视中华民族的耻辱吗?
哈尔滨诞生日——城史纪元只是这座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时间上的启始标志,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含义,人们应该记住这个时刻,但是否应该“纪念”它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与哈尔滨早期城市发展有着几乎相同命运的城市——大连。了解东北近代城市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哈尔滨和大连都是因中东铁路修建而兴起的近代城市,1999年大连市举行了大规模的建市百年纪念活动,冷静地回顾了这座城市当年在殖民者手中的屈辱,热烈地庆祝了回到人民怀抱后城市的巨大发展。1999年3月江泽民同志亲自为大连建市百年题词:“百年风雨洗礼,北方明珠生辉。”大连人的冷静、客观、果敢和胸怀实在是令人钦佩!
历史是真实、客观的,它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回避或掩盖而发生任何改变。历史又是一面镜子,只有勇敢、冷静地正视自己的过去,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昔日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屈辱,从中汲取教训,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才能激励人们更好地把握未来!
注释:
(1)《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