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北京高校的同事
文 陈 洁
鲁迅与北京高校的同事
文 陈洁
鲁迅在与北京高校同事的交往中,写下了大量作品。除了高校同事交游和约稿有激发灵感和促进写作的作用,与论敌的论辩也是激发鲁迅写作的一个动力。
郁达夫回忆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他所能记得的是“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郁达夫:《回忆鲁迅》)
鲁迅与郁达夫同任北大教员,因而相识。鲁迅在北京高校任职的同事,很多都是当时文坛上的活跃人物,他们之间产生思想的共鸣成为文友,或者在报刊交锋,成为论敌。在北京文坛这一城市空间中,他们是同事的这层社会关系常常被遮蔽了。
一
1920年8月,鲁迅受聘为北京大学讲师。12月开始,他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自编讲义《中国小说史略》,并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学理论,任教至1926年8月离京为止。
在鲁迅日记中记录下的北大同事就有五十多位,多为当时文化界名流,包括:郁达夫、钱玄同、冯汉叔、马幼渔、马叔平、邓以蛰、朱先、朱蓬仙、伊法尔、刘子庚、刘半农、刘叔雅、江绍原、许季上、李大钊、李玄伯、吴虞、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张凤举、陈垣、陈大齐、陈独秀、陈慎之、邵次公、林语堂、罗庸、周作人、赵少侯、胡适、夏元、顾孟余、顾颉刚、钱秣陵、徐以孙、徐旭生、徐祖正、徐悲鸿、爱罗先珂、高一涵、陶孟和、黄季刚、萧友梅、康心孚、章、章廷谦、廖翠凤(林语堂夫人)、黎锦熙、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何植三等。
北大英文系的陈源、徐志摩等教授,虽然没有在鲁迅日记中留下交往记录,但他们在文坛上屡次交手,成为论敌。
1923年许寿裳出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聘请鲁迅任教职。经过调整的女师大师资很多来自北大等校以及教育部,多数教员是兼任教职。该校国文科教师阵容引人注目,以北京大学国文系教师为主体,包括“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二周”(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林语堂、徐祖正、黎锦熙、郑奠等(陆晶清:《鲁迅先生在北师大》)。北大教员张凤举、冯汉叔、徐旭生、陈大齐、罗庸,英文系陈源等也受聘为女师大教员(参见《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职教员通讯处一览》1926年4月、《女师大教职员通讯》1924年冬)。鲁迅在北京多所高校任职,与高校同事的交往主要集中于北京大学和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对周氏兄弟与北大同事的交往,沈尹默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先、半农诸人。……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竟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
拜年的明信片,鲁迅总是以二弟周作人的名义发放。这样的宴集,也常常是由周作人出面邀请的。
顾颉刚在日记中,叙述过鲁迅与北大教授的交往情况:
鲁迅虽任教北大,且为《新青年》作文,而与北大诸教授不相往来,不赴宴会,虽曰高傲,而心理之沉郁可知。(《顾颉刚日记》,第1卷)
此段描述是顾颉刚1973年时,对1926年日记的补记,叙述中有过激情绪,但也从一个侧面描述鲁迅的交往情况。同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沈兼士1936年写文章悼念鲁迅,两次提及鲁迅不好应酬:“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的时候,他任科长,在办公时间外,从不作无谓酬应,只作学术上的研究”;“先生是不好应酬的一个人,他在北平时也不大和人来往”。(沈兼士:《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 上册))
民国时期北京高校师生思想活跃,新文化运动即以北京大学师生为主体展开。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同事冯汉叔、胡沅东、朱希祖均到北京大学任教(参见杨莘耜:《“木瓜之役”摄影题记》,收入《鲁迅在杭州》)。1913年,留日归国在教育界任职的包括鲁迅在内的六名章门弟子,在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中顺利通过议案,带动了章门弟子进入北京大学,其中包括钱玄同。
钱玄同和鲁迅有同乡之谊,并同为东京时期的章门弟子,熟知鲁迅思想、文学。钱玄同“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钱玄同:《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在钱玄同的约稿下,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加入了《新青年》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并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欣赏和认同,继而与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有了进一步的交往。
1930年代,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回忆了《新青年》编辑会以及与《新青年》同人的交往。

鲁迅为学生讲课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鲁迅和李大钊的相识也是在《新青年》编辑会上: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鲁迅:《<守常全集>题记》)
鲁迅与北大同事交往的模式以书信、文稿为主要形式,并有宴饮、聚会、拜访等活动,交流的内容倾向于思想文化层面。
周作人当时在北大专职任教,在钱玄同向鲁迅约稿过程中,曾做过中间人。1923年,周作人致信钱玄同,除了谈及自己前往北大交稿事宜,还告诉钱玄同鲁迅近来所发的议论,也有意作文批评所谓国学家,请钱玄同去约稿:“鲁君仿佛亦有借此破口大骂所谓辜倭合庶倭合几哑合之意,但敝人尚不能断定其何日下笔,足下如欲其早日做成,似可‘侧闻……’云云之信催促之,并与以一截止之日期,则庶乎其告成之望也夫!特此告密,不宣。”(《周作人致钱玄同》,1923年1月1日)“辜倭合庶倭合几哑合”,即指国学家。周作人在信中提及交给钱玄同的文章应该是作于1922年12月31日的《汉字改革的我见》,刊于《国语月刊》第7期。这篇文章中,周作人批评了“所谓‘国学家’”。
《语丝》创刊于1924年11月17日,同年12月13日《现代评论》在北京创刊。《语丝》和《现代评论》创刊后,鲁迅和他的很多高校同事都是这两个刊物的撰稿人。周作人作为专职的教员,与成员多为高校同事的现代评论派有较多交往。这在周作人的日记中有记载。周作人写有《志摩纪念》,登载于1932年3月《新月》第4卷第1期。1930年,为胡适四十岁生日祝寿的就有钱玄同、周作人。鲁迅和现代评论派则由疏离发展成为论敌。
1925年,林语堂在《给玄同的信》中借用刘半农描述钱玄同等人之语来描述三种周刊:“温文尔雅,《语丝》也(此似乎近于自夸,故置之);激昂慷慨,《猛进》也;穿大棉鞋与戴厚眼镜者,《现代评论》也。”这三种周刊形成了一个报刊环境。
周氏兄弟在1923年失和后,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刘半农等教授,与专职任教的周作人接触更多。他们更多地聚集于苦雨斋,与鲁迅则较疏离了。1925年,在《语丝》第二十期登载了刘半农致周作人的《巴黎通信》,并附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刘氏信中回忆了北京风物观音寺青云阁琉璃厂,忆及启明、玄同、尹诸位老友,却没有提及鲁迅。刘半农在信中称周作人寄来的《语丝》为“应时妙品”,述及近期刊载的文章:周作人和钱玄同议溥仪的文章、周作人与江绍原讨论的女裤问题——亦即“关于女子衣裳的礼”、周作人《林琴南与罗振玉》等。这几篇文章分别登载于《语丝》第一、三、四、五期,这几期中登有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说不出”》、《野草(一秋夜)》、《野草(二至四)》、《说胡须》、《“音乐”?》、《我来说“持中”的真相》,却未被提及。
1925年展开了对《语丝》文体的讨论,孙伏园(《语丝的文体》)、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等都撰文讨论。林语堂在语丝谈话会上主张《语丝》扩大范围,评论政治社会种种大小问题;孙伏园则指出语丝同人所写的思想学术言论,其实是更深层的政治问题。周作人对林语堂此议也做出回应,指出《语丝》谈的是政治上的大事件,如溥仪出宫、孙中山去世等;对于小事件,如“那只大虫”在教育界跳踉,则只是个人在日报上发议论,不曾在《语丝》上提到;他并进一步提出《语丝》的“费厄泼赖”精神(《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林语堂在继续讨论《语丝》题材范围时,终于涉及鲁迅的“胡须”与“牙齿”,但放在众话题之末:“有时忽而谈《盘庚今译》,有时忽而谈‘女裤心理’,忽又谈到孙中山主义,忽又谈到胡须与牙齿,各人要说什么便说什么。”(《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
针对林语堂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发表于1926年1月《莽原》半月刊第一期。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将笔锋指向“今之论者”——即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但真正的论敌其实是《现代评论》派。此文虽以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play)”起笔,但费厄泼赖以及不打落水狗,在林文中都已指明是周作人之意:“‘费厄泼赖’原来是明的意思。”(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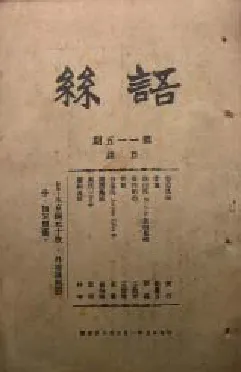
《语丝》
二
但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钱玄同和鲁迅一起站在了章士钊、杨荫榆的对立面,并批评钟鼓派、东吉祥胡同派,因为他们“捧之舐之” (《周作人为女师大风潮事致钱玄同函》,未刊书信)。1925年,杨荫榆担任校长期间发生的女师大风潮,在文坛上的表现就是《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1924年2月,许寿裳被段祺瑞政府无理革职,继任校长便是杨荫榆。1925年8月,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与友人论章杨书》,批评章士钊、杨荫榆。《猛进》社参与了《语丝》社的聚会,在随后的一期《语丝》上,周作人的文中便引用了《猛进》的一段话。这一时期,鲁迅也参加《猛进》社的聚会。
1925年2月7日,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中使用的“水平线”一词,此后被多次使用,成为《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论战中的一个利器。该期刊登的《<现代丛书>出版预告》中说:“《现代丛书》中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
1925年10月,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中便用了“水平线”这个典故:“我现在虽然也弄弄笔墨做做白话文,但才气却仿佛早经注定是该在‘水平线’之下似的,所以看见手帕或荒冢之类,倒无动于中;只记得在解剖室里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尸体上动刀的时候,可似乎略有做诗之意,——但是,不过‘之意’而已,并没有诗,读者幸勿误会,以为我有诗集将要精装行世,传之其人,先在此预告。”
1926年1月,鲁迅在《有趣的消息》中再次使用这个利器:“归根结蒂,如果杨荫榆或章士钊可以比附到犹太人特莱孚斯去,则他的篾片就可以等于左拉等辈了。这个时候,可怜的左拉要被中国人背出来;幸而杨荫榆或章士钊是否等于特莱孚斯,也还是一个大疑问。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的坏人(如水平线下的文人和学棍学匪之类),似乎将来要大吃其苦了,虽然也许要在身后,像下地狱一般。”
1926年,《语丝》第六十三期登载了元月17日晚署名“爱管闲事”所编《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其中位于狄更斯水平线之上有段祺瑞、章士钊、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等,位于水平线之下者,仅有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及未写明的“其他学匪”。《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展开笔战。《语丝》第六十四期登出鲁迅《学界的三魂》、刘复《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某前辈)》、明《陈源先生的来信》。随后,在《语丝》第六十五期,又登出鲁迅《不是信》。
《语丝》第86期,开始在《语丝》上公布《现代评论》社收受章士钊的一千元事件(周作人:《“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书后》)。并在《语丝》第90期做郑重声明“,《现代评论》社收受章士钊一千元一节全事实。”(明:《我们的闲话》三)这是《语丝》对《现代评论》的有力一击。
鲁迅在与北京高校同事的交往中,写下了大量作品。除了高校同事交游和约稿有激发灵感和促进写作的作用,与论敌的论辩也是激发鲁迅写作的一个动力。在《<坟>的题记》中,谈及《坟》结集的第二个原因时,鲁迅写道:“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厌恶我的文章。”在鲁迅手稿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又”这些字是后增加的,可见鲁迅写这句话时,先写下的是“是因为有人厌恶我的文章”。
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
责任编辑刘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