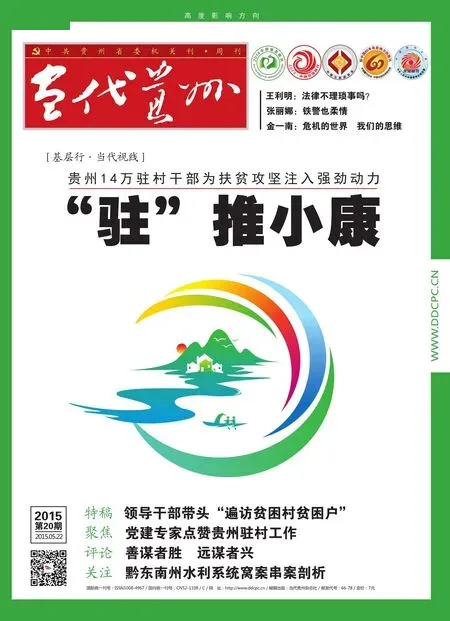德国人的两面性及启示
民族品格和人的性格一样,是与生俱来和后天养成两者的共同产物。但近现代的事实告诉我们,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制度的设计或引进,虽改变不了文化和民族的性格特征,却可以改变国家、民族、个人的习惯 。这方面,德国是最成功的例子。
徐圻教授、博导,贵州省首批核心专家。孔学堂理事会理事长、党委书记。历任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贵州省文化厅厅长,贵州大学哲学系主任等职。
我第一次思考所谓的“国民性”这类问题,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民族,而是从德意志民族开始的。那时是“文革”的后期,我还是一名“蹉跎”着岁月的青年工人;我读到了威廉·夏依勒的不朽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几十年来,这部书,是我阅读次数最多的文献。
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段歌德的话:“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这段话是一个引子,作者意在用歌德的声音昭示德意志这个民族、这种文化的特征,同时引导读者在阅读那段惊心动魄、扑朔迷离、血雨腥风、大起大落的历史的过程中思考:德国究竟是怎么回事?德国人是怎么回事?德国文化是怎么回事?
而霍尔曼·沃克的姊妹篇长篇历史小说《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作者非常写实地描绘了各式各样的纳粹分子——他们有的是嗜血的虐待狂,有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匪徒——如何对犹太民族实施肉体迫害、精神摧残和集体虐杀的,这个过程优雅而冷酷、理性而残忍、按部就班而毫不留情,充分显示了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的内在张力。
德国曾经向人类奉献过康德、歌德、海涅、贝多芬、马克思、爱因斯坦这些灿若星辰的大师,也派生出了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这样的千古恶人。究其根源,德国的文化以及从这种文化衍生出来的具有鲜明两面性的德意志民族性格,导致了这些互不相容的现象。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二战”刚刚结束时就指出,追究纳粹德国的反人类暴行,不能仅仅盯住希特勒和他的那些著名党徒以及党卫队、盖世太保等等组织,还必须从德国文化里面找原因、从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面找原因。否则就不能解释:这样一个高度理性的、智慧的、有教养的、对人类文明贡献甚多的民族,怎么会在那么短时间里对希特勒的纳粹理论和纳粹实践深信不疑甚至如痴如醉,跟着一小撮战争狂人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呢?
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是高素质的,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他们对事认真、待人诚恳、严于律己、一丝不苟、遵守纪律、坚韧不拔、善于思辨、注重荣誉;他们严谨、古板、执着、天真、傲气、善良;他们有贵族气、有幽默感、有历史情结、有终极关怀。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德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经常显露出诸多由“集体无意识”派生出来的恶的品行。德国人的严谨和高效,既创造了19世纪以来科技、工业和民生的奇迹,也留下了闪电战、恐怖空袭、集中营、毒气室等斑斑劣迹。德国人富于思辨、见解深刻,曾经出过许许多多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但同时又太天真,对很多浅显的谬误缺乏识别、对人性的虚假不假思索。《我的奋斗》里面宣扬的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和犹太、斯拉夫民族的劣等性,是非常拙劣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却使得不仅德国普通老百姓,而且知识界、精英层的无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这就为纳粹德国反人类的暴行找到了“合理”的心理依据。而一旦整个民族被绑上了这架战车,原本自由、理性、独立、热忱、可爱的德国人民,从此就变成了拘谨、麻木、冷酷、狂热、可怕的一个群体,发生了“集体无意识”,他们亦步亦趋地跟在强权后面,干下了挑战宗教权威、践踏人类尊严、冲击道德底线、残害生命个体的种种行径。
作为一个高尚的、理性的、深刻的民族,浩劫之后的德国人能够直面现实、自我反省,做到从善如流、洗心革面。这是“二战”以后德国留给世界的一道迷人风景。1970年,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向犹太受害者下跪、谢罪,这是良知的体现,也是对过去历史的交代。作为德国总理,作为纳粹德国在历史和文化时空中的继任者,勃兰特敢于代表他的国家和民族来面对波兰及全世界的犹太人,敢于对已经过去了的那段历史作出交代。他手持鲜花,双膝跪地,向死于奥斯维辛的六百万犹太人和更多活着的犹太人谢罪。从那个时候开始,新的历史篇章翻开了。
民族品格和人的性格一样,是与生俱来和后天养成这两者的共同产物。民族性当中的一些本源性、支撑性、特征性的要素是很难改变的,但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民族性也可以发生变化。近现代的事实告诉我们,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制度的设计或引进,虽改变不了文化和民族的性格特征,却可以改变国家、民族、个人的习惯,可以通过法律的规约,发扬人性中的善、遏止人性中的恶,可以对民族或文化的两面性实施引导、矫正。这方面,德国是
最成功的例子。(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