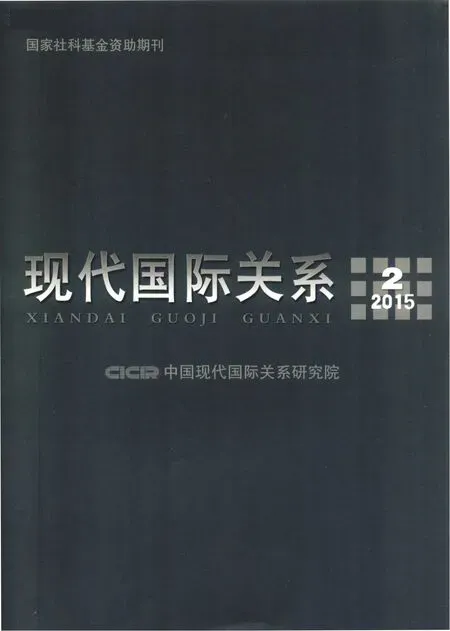美国外交是否正进入“后奥巴马”时代?
王文峰 (《现代国际关系》执行主编、研究员)
2014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奥巴马进入“跛鸭期”,在国会参众两院都被共和党控制的情况下,舆论普遍预期奥巴马未来两年的施政将面临极大困难。但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总统在外交领域比内政上有更大的独立行动的权限,有能力不受政治的困扰而有所作为,即使在任期的最后两年也是如此。在较近的历史上,里根就是一个典型,其在任最后两年在外交领域取得了不小成绩;克林顿与小布什也不同程度地都是如此,“跛鸭期”中外交比内政更有作为。那么最后两年的奥巴马会怎么样?如今的美国外交正在进入“后奥巴马”时代吗?
2014年的中期选举虽然选的是国会议员,但实际上是对奥巴马的一次全民公投。美国选民通过投票宣泄了他们对奥巴马的种种不满,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认为他在外交上过于软弱,在纷繁复杂、动荡多事的国际形势下,没有发挥强大的领导力,没有让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突出的领导角色。这一点在民调中清楚地显现,美国民众对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支持率之低更甚于对其总体工作的满意程度。奥巴马外交上软弱的形象被共和党树为靶子猛烈抨击,民主党内也出现不和谐之声,希拉里·克林顿和前国防部长帕内塔等人出于各自目的,纷纷对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内容和决策风格提出批评。一时间,奥巴马在外交上成了“孤家寡人”。
岁末年初,奥巴马却在外交上难得地施展了一下身手。一是在2014年12月17日宣布美国放宽对古巴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制裁,启动与古巴恢复正常关系进程;二是以保护言论自由不受侵犯为名,强力鼓动索尼公司公开放映电影《刺杀金正恩》,并宣布对朝鲜进行制裁。这两件事一柔一刚,似乎又让人们看到了美国总统在外交领域无人可及的主动性和行动能力。然而,到2015年1月份,由于其本人和其他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未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反恐大游行,使美国在如此重要的国际场合缺席,奥巴马再次沦为国内舆论声讨的对象。人们对奥巴马在外交上的领导能力再次打上问号。
在外交思想上,奥巴马与美国国内的主流之间始终存在一定距离,其“奇异”之处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方面。首先从理念上讲,奥巴马的思想与美国外交中传统的理想主义有较大差别。作为美国外交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理想主义强调的是美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以及将美国式的制度与价值观向世界传播的使命感。但在奥巴马的外交理念中,美国与世界有着另一种关系,美国是世界上与别人平等的一员,所有国家、民族都有权认为自己是特殊甚至优越的,它们和美国一样都可以有自己的“例外论”。以美国政治的话语讲,奥巴马的思想实质是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一种表现,它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否定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文化的优越性。在现实的政策实践中,奥巴马外交理念中的这一特点表现为不愿强调美国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特殊与优越,不愿在意识形态层面贬低和攻击对手。比如即使在美国与国际社会面临严重恐怖威胁的情况下,奥巴马也一直不愿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挂钩,以致连“伊斯兰极端主义”这样的词汇都很难说出口。在外界看来,奥巴马似乎认为“美国价值观”不是体现在美式民主制度的推广,而是体现在拒绝虐待关塔那摩的囚犯以保护他们的人权。这对美国国内保守势力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即使面对主流媒体舆论,奥巴马也不会因此而在政治上得分。
其次从手段上讲,奥巴马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比较排斥,不愿靠武力彰显美国是世界的“领导”。奥巴马从入主白宫的一刻起,就以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为重要战略目标,全面撤军始终是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攻打利比亚时的“后排领导”而非身先士卒,到对叙利亚化武问题划下红线而又无法执行;从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坚决以经济而非军事手段对付普京,到为打击“伊斯兰国”而半遮半掩地向伊拉克增派部队,都让人感到奥巴马在军事力量使用上内心的犹豫踟蹰。美国所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其外交的坚强后盾,尚武是美国历史文化中一个重要特征,奥巴马“不做蠢事”的标签与此相矛盾。如果说六年前奥巴马上任之初结束战争的努力是对小布什政策的扭转,总体符合美国民众的意愿,那么他在随后几年中的表现则很难有助于他树立强势领袖的形象。
第三,从政策重点的选择拿捏上讲,奥巴马没有表现出灵活、适时的调整变化。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让美国从中东和南亚的泥淖中脱身,转投亚太这一对世界政治与经济最为重要的地区,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找到新的支撑点,一直是奥巴马地缘外交中的重要使命。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外交战略中最大的手笔,在成功除掉本·拉丹之后,奥巴马政府曾急不可待地宣布恐怖势力的削弱以及美国战略重点由此而必须进行的转移。但事实远不如奥巴马所愿,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伊斯兰国”的兴起,使奥巴马难以全力推进其亚太战略部署。但他又不甘就此放手,反复强调的仍是战略转向亚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愿应景般将中东和俄罗斯置于美国外交政策中最突出的地位。中东在美外交上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同时近年来美国内总体对普京和俄罗斯持强烈的负面情绪,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在外交政策表述上不善于处理迫在眉睫的矛盾与长期战略目标间的关系,难以说服和引导舆论,外界对他外交上的判断能力和适应能力的质疑也必然加深。
奥巴马外交中有被美国主流思想视为“异类”的因素,在国内引发争议。他对美国的传统外交理念构成了一定挑战,而过去六年的执政不足以形成有利于他的政治共识。这对他掌控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权形成障碍,未来两年的国内政治环境则会将这种障碍进一步放大。但客观分析,奥巴马思想中与美国外交主流思想不尽合拍的成分都有其合理性,除了奥巴马个人因素和政治派别因素外,也体现了美国各界对外交政策的反思,反映了美国战略思考的前瞻与远见,同时折映出美国外交面对国内的现实与当今世界的新发展、新变化而存在的困境。在一些议题上,与其说表现出的是奥巴马的无奈,不如说是美国的无奈。在财政拮据、实力地位相对衰落、国际权力分散态势明显、大国应对新型威胁局限性突出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国外交难免会遭遇未曾经历的困难。比如人们从奥巴马的言论中能明显地感觉到,他在谈论亚太“再平衡”和应对中国崛起时的熟练、自信、有套路,与他谈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时的左支右绌,缺乏完整战略之间存在鲜明对比。这何尝不是美国整体外交战略面对新老不同议题时思维水平差距的体现。
2016年美国大选的序幕即将拉开,在外交上,为了提振选民的情绪,共和党、乃至民主党都可能会抛出以“去奥巴马化”为主轴的外交政策纲领,向美国传统外交路线回归。在这种国内政治形势之下,奥巴马能否掌控美国外交政策主导权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例如他在一些具体政策议题上能取得多少突破,让他能以议题上的推进弥补理念上的劣势,以政策上的成果化解政治气氛的压力?此外,未来两年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是否会出现重大的国内或国际危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是否会出现突出的威胁来源,使美国国内凝聚共识的过程明显加快?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是否会有展示领导力的机会?这些都是可能的变量。
大的时代变动使美国外交面临着转型,也使奥巴马注定是美国外交史上一个带有过渡性色彩的人物。面对新的内外现实,美国外交的思考与摸索绝不会止于奥巴马,成型的适应新形势的美国外交思想与战略,或许会伴随着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仍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辩论、博弈、实践、调整才能最终形成。
对于中国来说,无论美国外交是否或何时进入“后奥巴马”时代,在未来两年的对美外交中,与奥巴马政府打交道与关注美国国内政治、政策环境的整体变动,为“后奥巴马”时代早做准备同等重要。同时,中国应当特别留意不要掉入奥巴马和美国熟悉的套路,不计战略成本地吸引美国的恶意关注,以避免成为美国政治共识的指向。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本着长期经营、“功成不必在奥巴马”的心态,在持续不断推进的同时,很好地把握节奏,夯实基础,争取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