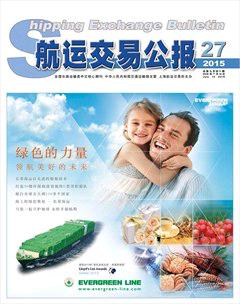剪不断的国际关系
乐之
其实我对所谓“关系”始终是“无感”的,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统统都懒得去思考。这很像《海权浮沉》中一句形容中美两国特性的话: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而中国人只能是中国人。意思是说美国文化是外向的,其致力于把自己的价值观向世界输送,而中国人则有着悠长的城邦思想,是内敛的,某种程度上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而不屑于与外界交流。
在这种内敛的文化下,中国向世界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迫的。
然而不管是否被迫,开放又似乎是必须的。
的确,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又岂能离开世界。认识他国,同构于自我认知过程。只有在此项工作完成的基础上,中国人才能重新构建基于自己视角的全球格局体系,从而探索自我的利益所在,为世界规模的和平治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也正是包括我要介绍的《海权浮沉》在内的《大观》系列丛刊试图做的。《大观》是一份介于专业的学术刊物与通俗的大众出版物之间的思想性丛书。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包括我在内的读者都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硬着头皮”去了解国际关系。
《海权沉浮》全面剖析了英美德俄等国海权的潮起潮落,对当下中国颇有借鉴意义。
16—19世纪的近四百年里,来自葡萄牙、加利西亚等国的探险家扬帆起航,驶过非洲西海岸,朝美洲以及太平洋的“新世界”挺进,直至以欧洲为中心、以海上力量为载具的世界秩序初步得到确立。在此过程中,英国凭借对海运和殖民利益的攫取,建立起独一无二的具有海上统治力的强大舰队。在16—19世纪的近四百年里,“谁控制了海洋,就可以迫使其他国家为该国的利益纳贡”。
而无力控制全局就注定失败的结局。
《海权浮沉》中有一篇长文《海陆两难:日本帝国的兴衰》,详细解读了日本控制与失控太平洋的历史和缘由,以及英美两大海上强国对日本控制太平洋这种企图的利用与打击,都是缘于一个原因——英美两国都看不得太平洋由一个统一的国家来控制。
日本因为打赢了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从而奠定了其在太平洋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这与英国为了削弱俄国力量而与日本签订英日条约相关。然而当日本决定继续走远,试图挑战美国等海洋强国时,注定了其走向灭亡,“到1947年1月1日,当和平的新年曙光时隔15年后再度降临日本列岛上空时,辽阔的太平洋上已经没有一艘日本军舰了。”虽然如此,但是如果了解日本意图控制太平洋的前因后果,就会明白日本对这一海域的“觊觎”始终不应被忽视。
19世纪末之后,技术和生产开始取代贸易成为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此时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再是海战,而是在堑壕中投入人力、物力的总量以及持久性,海权不再是唯一的神祇。尽管海权早已不像马汉所言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比陆权拥有永恒的优势,但海上统治权依然与世界影响力直接相连,并将继续影响和塑造历史。
就以太平洋战略而言,从前英国选择该区域的盟友是在日本与俄罗斯之间摇摆。现在中国显然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而如今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虽然对于中国政权存有敌意,但其如今在太平洋上的盟友宁愿是中国也不能是俄罗斯——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战略智囊们,显然认为中国内敛的性格相比俄罗斯的侵略性格,更有利于美国的价值观。
这里读者也许如我一样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还是如今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俄罗斯这个民族始终不予信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见国际关系在历史与文化上的传承。了解历史、了解文化,大概在很大程度上也能看清现在和将来。
《海权浮沉》主编邱立波,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7月至2006年10月,在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工作;2006年10月至2008年9月,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2009年11月至今,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工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