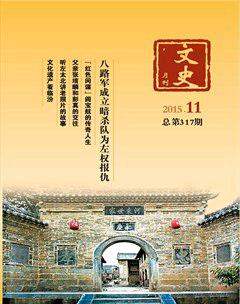约翰·马吉:拍摄日军南京暴行的美国牧师
王桂英



2007年的11月初,众多中国媒体报道了一则来自日本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东京法院判决:东中野修道和出版商展转社对夏淑琴女士构成了名誉侵权,需支付赔偿金400万日元。在审判中涉及到的一部被称为《南京暴行纪实》的原始纪录片,其中4号影片的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日军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为我们留下这宝贵原始纪录片的,是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约翰·马吉牧师。这个纪录片成为夏女士控诉日本法西斯并直接暴露他们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谎言的最有力证据。
医治伤者 解救妇女
约翰·马吉(John Magee),1884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一个律师家庭。马吉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获得学士和神学硕士学位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1921年与在中国的英国女传教士菲丝结婚。
从1912年来到中国,直至日军占领南京,他一直在南京下关挹江门外的道胜堂教堂传教。1937年底,随着战争阴云逐渐笼罩南京,在宁的外籍人士纷纷逃离。美国驻南京使馆的官员也再三劝说他前往安全的地区,但是马吉选择了留下。他与拉贝、魏特琳等在宁外籍人士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被选为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主席。在那些地狱般的日子里,面对在城内游荡的数万丧失人性的残暴日军,他和另外20多位外国人,用他们意志的力量和灾难时刻迸发出的人性光辉,从日本人的屠刀下拯救了20多万南京的平民百姓。 随着战线迫近南京,在宁的外籍人士认识到战争和无政府状态将会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危险,他们自发地行动起来,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无助的中国难民。仿效法国饶神父的上海难民区,他们计划在南京也建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11月22日,十几名在宁外籍人士开会,正式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拉贝当选为主席,马吉牧师为委员。他们在战时极艰苦的条件下,迅速展开难民区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日机轰炸南京开始,马吉牧师就忙着救助被炸伤的南京市民和上海方向逃过来的受伤难民。12月8日,他发现一名来自无锡一带的老妇人,双手被炸弹严重炸伤,就把她和她的女儿送到鼓楼医院,在那儿她的一个指头被切除了。他还组织储备药品,以供不时之需,并开车到处寻找受伤难民,将他们送往医院救治。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马吉牧师领导教会在下关接待照顾前方退下之伤兵,每日千计。 南京沦陷之前,不少外国人都认为日本军队是一支“现代”“文明”的军队,甚至期盼日军进城后会给在南京的外国人生命和财产带来更多的保障。12月13日之后发生的事实,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想法。马吉牧师在19日的信中写道:“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他更难以想到的,是灾难远未结束。 日军进城后,带来的并不是外籍人士所期望的秩序恢复。战斗停止了,中国平民的伤亡却远远没有停止,日军的暴行让他们感到震惊,灾难才刚刚开始。
马吉牧师亲眼所见到的是,日本兵在整个城市里到处放火,除了安全区外,城市正逐渐被烧毁,滥杀无辜更是随处皆是。“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只有当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堪与比拟。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屠杀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两个日本兵刚刚枪杀了一个中国人,却“一直在抽烟,谈笑风生,杀一名中国人就像杀死一只老鼠”。在鼓楼医院里,马吉牧师看到“一个七岁男孩的尸体,肚子上被刺了四至五刀,已无法抢救”;“一名19岁的姑娘,怀了六个半月的身孕(第一胎),因反抗日本兵强暴,脸上有七处刀伤,腿上有八处,肚子上有一处深约两英寸,正是这一刀导致了流产”。 从日本人手里营救被抓的中国人成了他的日常工作。马吉的努力往往劳而无功,甚至要面对日本兵枪和刺刀的威胁,但他还是不放过任何机会。为了救治受伤的人,12月13日,也就是日军占领南京的那一天,以马吉牧师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立。在15日给日本大使馆官员的信中,他们表示:“目前已经有大量士兵和平民受伤,为了能够应付由此形成的困难局面,我们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现在我们恳请您,帮助我们获得南京日本军事当局的批准,以便我们开展人道主义工作。”马吉没有能力阻止日军的罪恶行径,但他利用他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和手段,帮助和救治中国人。他领导下的南京红十字会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受伤的南京难民获得医治的主要途径。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原南京军政部、外交部等处的伤兵医院里,还留着很多中国伤兵。他们没有办法逃走,也无人照料。日本人没有给这些伤兵治疗,连维持生存的食物和水都没有,反而将其中的一部分拖走杀害。马吉牧师领导的国际红十字会承担起了照料伤兵的人道使命。“该会接收在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伤兵医院,成立红十字会难民医院,收容千余名重伤伤兵”。马吉和一些日本军官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医院不藏匿士兵,医院将受到尊重,放下武器的士兵也不会受到伤害”。但事实并非如此。马吉牧师在给国际红十字会的电报中写道:“日本人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向全世界公告,被安置在外交部的中国伤兵受到他们的关怀。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国医护人员以及病人的食品一直都是由我们提供的。”红十字会对伤员的帮助也遭到日军毫无道理的阻挠,马吉牧师必须随时跟着救护车,因为一旦没有外国人在场,汽车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抢走。在一次帮助中国伤兵的过程中,他带着载满伤员的救护车赶往外交部,准备将其他地方的伤员集中到这里。当时,马吉牧师正扶着一名中国伤员走上台阶,“一队日本兵来了,其中有些像是野兽……一个日本兵把他从我身边拖开,猛地扭他受伤的膀子,把他的手捆在一起,并把另一名伤员的手也捆在一起。幸运的是,我发现一名刚过来的日本军医,我指给他看伤员身上的血衣。他会德语,我用不流利的德语说这是伤兵医院。他叫日本兵给伤员松了绑。”运第二批伤员的时候,又遇到了日军的刁难:“我们在门口遇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军官,在这以前我从未见过这种人!他说话声音听起来像狗吠。如果我是可燃品的话,他的那副模样就像要把我烧掉。”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马吉牧师凭借着道德与正义赋予他的力量和勇气,从日军的屠刀下一次又一次抢救着伤者。占领南京后的日军四处抢劫、任意杀人,“但现在最可怕的是强奸妇女”,“日本人并不认为这是可耻的事。军队长官并没有采取实质措施,如果能枪毙几个倒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我才不信他们会那么做,因为很显然,整个军队并不认为强奸是犯罪,或是很残酷的事……目前就我所知,他们对强奸的态度是,只有被发现并刊登在外国报纸上才算是最大的罪恶。”“日本人以最无耻的方式干这些勾当,街上到处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兵。”日军进城后的一天,马吉牧师和德国人施佩林走进一间房子,“有位妇女正坐在地上哭泣。人们告诉我们她被强奸了,并说楼上还有一个日本兵”。马吉牧师冲到那个房间,愤怒地敲门,“房子里的日本兵有一些反应,我用英语和德语大声地喊‘开门,随后施佩林也来了,敲门并喊‘开门。最终那个日本兵出来了,他下楼时我喊道‘畜生。”
面对全副武装、失去人性的日本兵,马吉牧师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着中国妇女。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约翰·马吉把一封信和一把日本步枪刺刀放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信中说,一名日军士兵用这把刀威胁一名中国妇女,当我们委员会的3名成员撞见他的时候,他撇下刺刀不要了。”“类似的可怕的事全城都有发生。”但当马吉牧师“把这些事告诉刚从美国来的日本总领事时,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告诉《朝日新闻》的记者时,“他也说:‘这是不可避免的。”马吉牧师住的地方是中立国的财产,日本兵多少有些顾忌,不敢肆意胡为,因此成为中国妇女的避难所,住满来寻求庇护和他从日军魔爪下拯救出来的中国妇女。“楼上楼下的房屋里都住满了人,连卫生间里都住进了一对母女”,“其中包括几个尼姑”。
拍摄影片 揭露暴行
当我们今天寻找日军南京暴行的证据时,除了正式的文书、报告之外,我们发现留在南京的很多外国人的书信和日记。他们有的此前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其后也没有再写过日记,但是面对他们亲眼所看到的一切,觉得自己在经历一个必将被历史记载的灾难时刻,他们有义务为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面对日军暴行,在帮助中国人的同时,马吉牧师也没有忘记对日本人的暴行留下证据。 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牧师写下了很多文书报告。他与拉贝等其他委员一起,向日本在南京的使馆提出了很多口头和书面的抗议。12月21日下午2时,包括马吉牧师在内的“全体外国侨民,在鼓楼医院门口集合,形成一个整体队伍朝日本大使馆进发”,呈递的一封信,要求日本当局“1、制止在城市大部分地区纵火,以免尚未被毁坏的其余城区继续遭到肆无忌惮的有组织的破坏;2、 一周来,日本军队给城市造成了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这种破坏秩序的行为必须立即得到制止;3、抢劫和纵火已经使得城市的商业生活陷于停顿,全部平民百姓因此而拥挤在一个大难民收容所里”,“我们别无所求,只请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住房、安全和食品!” 与此同时,他还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间,给他的妻子写了很多信,这些信件中没有多少家常,几乎全是他对日军暴行的记录。此外,他还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那台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记录影片。他要用摄像机来保留日军罪证,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方式。 当时日军对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行动严格控制,对暴行的摄影记录当然在绝对禁止之列。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该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他冒着生命危险,躲过日军的监视,偷偷拍摄了这些记录影片,包括前面提到的夏淑琴的画面。 当时,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家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牧师的注意。他和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一起去门东新路口5号(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实地查看,并用摄影机拍摄了夏淑琴家劫难后的惨状。对此,许传音在东京审判作证时说:“一个年轻姑娘在桌子上被强奸,而且我看到她还在桌子上流血;后来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尸体。这些尸体被丢在离那个家几米远的地方。马吉牧师和我都对这些尸体拍了照片。这些尸首赤身露体,显然是受了致命伤而死的。”当时的拍摄条件极端恶劣。菲奇的外孙女回忆,菲奇曾告诉她,马吉牧师是怎样通过窗口拍摄到日本兵赶拢平民、妇女们在一旁跪倒求饶的情景的。马吉也说:“假如有更多胶卷和更多时间的话,我就会拍下更多的场景。”即使如此,短短的影片中反映出的日军暴行也足以让世界人民感到恐怖和震惊! 日军为了掩盖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相,严格限制外籍人士的出入。几经努力,在宁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乔治·菲奇才得到日军的允许,可以乘火车去上海。1938年1月19日,马吉牧师拍摄的一部分胶片由菲奇带到了上海。为了躲避车站日军的检查,菲奇将胶片缝在了驼毛外套的夹层里。正在上海的田伯烈参与了编辑影片的工作,他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并且是最早在国际上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他们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并给影片的各部分加了英文标题。这部纪录片由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一部送给了英国“调解联谊会”的女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一部给了德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罗森;一部由菲奇带回美国;还有一部辗转送到了美国国会,被存放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上世纪90年代日本NHK电视台寻找到了7位看过她的影片的人。送给德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罗森的拷贝,目前下落不明。在著名的《罗森报告》中,罗森描述了亲眼所见的盟友日军暴行,并且提到了马吉牧师的影片,还附上了英文的影片镜头目录,要求将影片放映给元首看。在美国,菲奇和马吉回国后都曾放映过这部影片,据说看到那些暴行镜头时常常有人昏倒。胶片中的近百幅画面被翻拍成照片,有10幅照片还被刊登在1938年5月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1946年8月15日,东京的远东国际法庭审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马吉牧师曾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种种日军暴行。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时,曾在励志社会堂放映过弗兰克·库柏编导影片的《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回到美国后,约翰·马吉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圣约翰教堂(通常被称为总统教堂)担任牧师。在任职期间,他曾在白宫主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葬礼。其后,他在耶鲁大学和匹兹堡的卡瓦瑞教堂担任教职。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
屠城铁证 重新发现
由于种种原因,1948年以后,南京大屠杀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很少被提及。马吉的记录影片也为世人所遗忘。1990年《罗森报告》的发现,使人们重新认识到这部影片的存在。1990年底,纽约对日索赔基金会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征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启事。乔治·菲奇的女儿爱迪斯·菲奇看到启示后,和基金会取得了联系,讲述了他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之后,美国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从爱迪斯·菲奇那里得到了乔治·菲奇的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其中详细讲述了他将马吉拍摄的胶片偷偷带往上海、制作4份拷贝的过程。乔治·菲奇的外孙女汤娅·昆顿向联合会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捐赠了影片的复本。
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到此,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唯一纪录片的原始胶片和拍摄工具被发现,这成为了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马吉牧师用来记录日军暴行的那台摄影机回到了中国南京,大卫·马吉将它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为了感谢马吉牧师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给予南京人民的人道主义帮助,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第十二中学的图书馆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永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