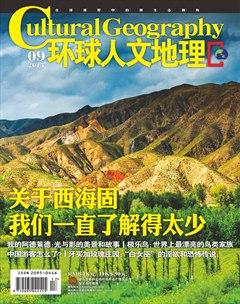历史城市的空间形态
唐晓峰
在地图上,城市都是大小不同的点,但实际上,城市是一个社会空间。讲城市如果没有把“空间”讲明白,则城市还是一个符号或者“虚体”。地理学研究城市,总是脚踏实地研究城市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的空间形态各有不同,背后依托的社会制度及礼法观念也不一样,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才能把城市的一些基本问题说清楚。研究今天的城市是如此,研究历史城市也是如此。
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是最重视城市空间形态的,在这些学科的研究中,总要画出城市的平面图,虽然是些不甚完善的复原图,却也令人有一个清楚的空间印象,知道古代城市是什么“样子”。有些研究,说了半天城市,到头来,还不知道城市的东南西北,这能说对城市有“深刻认识”吗?
比如说,知道秦始皇定都于咸阳的人很多,但秦始皇的咸阳到底是什么样子,恐怕能讲明白的人并不多。知道咸阳城的样子有什么用?知道了咸阳城的样子(也就是空间形态),才能理解中国历史的那场时代巨变,才能知道中国第一位皇帝是何等人物,才能体会他在“统一海内”后“得志而小天下”的气派。
秦始皇的咸阳是一个极宽广的地带,著名的阿房宫,仅其中的一座前殿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而在阿房宫的基础上,又“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贾谊形容秦始皇“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崤函为宫”就是以崤山函谷关之内的整个关中地区为宫室。果然,后来阿房宫向南的建筑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终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这种无限扩展的都城宫室空间格局,反映了大帝国胜利者无拘无束的宏观视野。
又如,汉代名臣萧何曾为刘邦设计未央宫,“宫阙壮甚”,但底层出身当皇帝不久的刘邦不理解,问萧何:“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城市空间的样式,不是一件毫无想象、可以随意而为或无意而为的事。《考工记》是讲王朝城市平面规矩的一部书,做皇帝、做大臣的无人不知。另外,每个朝代掌权的人又各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比如曹操,对他的魏都邺城就有一番独特的想法,结果造出一座平面空间形态整齐有序的城池,与前朝的城市都不一样,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后来的隋唐长安城都受到邺城规划的影响。
当今的人文地理学家说,世上有三类基本的记录与传播知识信息的“文本”,一是口传文本,二是书写文本,三是景观文本。在景观文本中就包括了我们所说的空间形态问题。我们“阅读”空间形态文本,可以明白或发现许多东西。例如,到北京大街转一遍,就知道当年皇亲国戚与草根阶级天壤悬隔,大宅门与小胡同各有分辨。
任何社会生活形态在完熟的过程中,都会相应地形成一套空间行为规范,从家庭到社会,从一人到千万人,无不在空间系统中建立规范。一个时代有一个空间系统,一段历史有一段空间进程,没有空间进程不成其为历史。
西方的一些左派地理学者早已把资本主义的地理进程分析补充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他们认为,马克思原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忽略了空间问题,因此他们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涉及全球的地理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不深入完整地观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形态,会被许多表象所误导,以为那里的城市普遍繁荣、遍地光彩。地理学家不承认有“均质空间”,比如美国城市地理学家就不断提醒人们注意那些繁荣城市的“烂掉的心”,即城市内部的贫民窟。大都市空间中的“腐烂”部分与“腐烂”过程是美国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总之,城市空间形态是城市研究中不可忽视、也不可浅尝辄止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对一座具体的城市没有什么空间讨论,对于城市社会的各个层次只有纵向而没有横向的定位,这样的城市研究只能算是半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