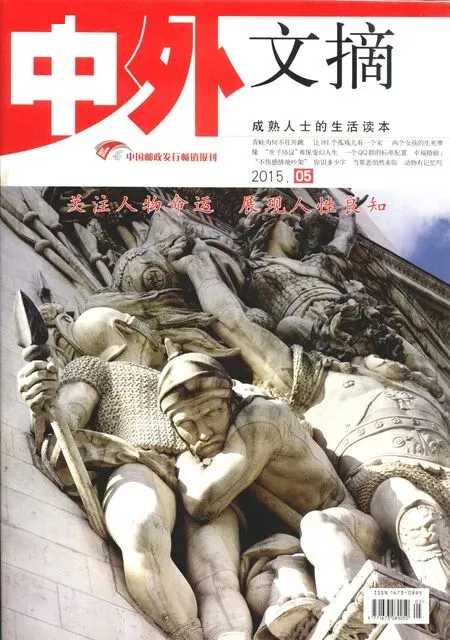读书偶得
读书偶得
同室编稿的阿明,最近不知哪根神经发烧,又开始重读四大名著,看来是走火入魔了。隔三差五给我复述一段,精彩语句背得烂熟。大观园里各色人等,主子下人、嫡传庶出、旧爱新宠,那说话的语态或骄横、或谄媚、或冷嘲热讽、或绵里藏针,阿明字字句句把玩,让我也听得出了神。“主编”只是阿明的名片和饭辙,他是写小说的,已有多部长篇出版。读《红楼》这是第四遍,越读越觉大师遥不可及。
跟阿明一比,惭愧许多。我读书很杂,五行六路皆能入眼。长不了学问,只能长点见识。每个月读三四本吧,不紧不慢,跟日子同步。我从未思索过读书的意义,更不留意别人在读什么;它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如同吃饭穿衣。近日读了曾彦修《平生六记》、申赋渔《逝者如渡渡》、章小东《尺素集》,准备读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本“言必称”级别的书,全世界只有我没读过。
《平生六记》是本小册子,行宽字稀,三个钟点便可读完。曾彦修今年96岁,在文化出版界任职多年。五七年“反右”时,他正在人民出版社当头头。山雨欲来,曾嗅出味道,知道自己有几件事开罪了上面,这次在劫难逃。但左等右等,只闻风声,却不见帽子。后来“指标”下来了,单位“反右五人小组”躲不过,在四合院的小屋里确定上报名单,中选者三四人。时任小组长的曾表了态:把我也报上去吧,单位好过关。于争论和沉默中捱过了两个时辰,在曾的坚持下大家“挥泪斩了马谡”。曾老说当时他的心情是坦然的,从全社大局看乃聪明之举;但他接着落笔:“我们这小会结束时,院中寂静无声,唯有树枝摇曳作响,院东已是残阳一抹,竟然有点像个秋天的样子了。”
曾在书里回顾了土改、打虎、镇反、肃反、四清等运动里,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纠正冤假错案的经历,及屡屡碰壁的无奈。1951年镇反,曾在《南方日报》当社长,某晚忽接省公安厅通知,次日要公审处决一百四十多人;每人的罪状只两三句,不外乎“一贯反动,罪大恶极”,要报纸同步宣传。深度报道怎能连夜突击搞出来?况且名单里有的人明明是主动回内地的旧官员,许多人都知道。编委们饿着肚子开会到深夜,最后决定冒险顶一回,由曾打电话请示“203”(叶剑英)。凌晨一时,各路人马被召到叶的住地。争辩异常激烈,警方坚持天亮即处决,毫不退让。叶不禁正色道:“我们要记住中央苏区的教训呢,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党委手里,还是掌握在保卫部门手里……”最后拍了板。
我比曾老差了一个辈份,若遭此类事,是息事逢迎、还是有所坚持?在长辈们眼里轻重很分明:承担风险事小,人头落地事大。
1956年整风期间,曾社长费尽周折给业务骨干戴文葆摘掉了“特嫌”帽子,却为他本人日后挨整埋下了祸根。在“四清记实”一节,他不惜篇幅地讲述了如何为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等类的怀疑或帽子。10个小故事娓娓道来,曲折、生动而辛酸。他说这些事让他终生难忘;而“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一位为党的文化事业躬耕70年的职业出版家,最为自豪的竟是在一次次运动中挽救他人的政治生命,其余均列入“而已”了!
109岁的周有光给他题了字:“良知未泯”。做人的本分,却成了对人格最高的褒奖。
“未泯”即“尚存”吧。不知我们这些后来者,良知究竟泯灭多少、又尚存几何?我们也做过一些终生难忘的事么,或只是一天天兢兢业业地“而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