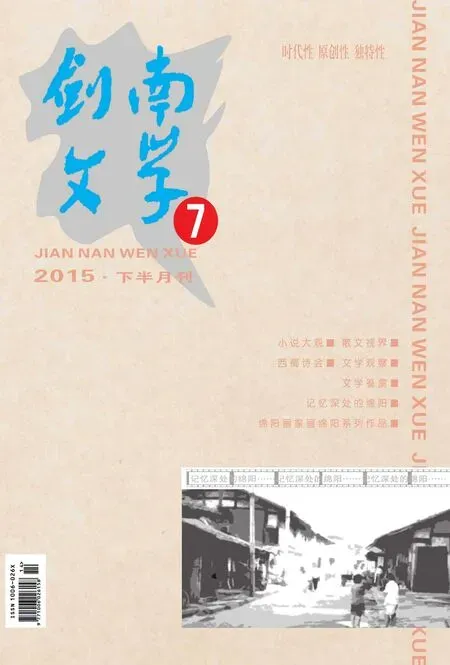从Gul-liver's Travels看译注的功能
■李 杰
从Gul-liver's Travels看译注的功能
■李 杰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译注的实际运用,并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加以深发。具体地,将《格理弗游记》作为此论文译注研究的载体,原因有二:一方面,《格理弗游记》是Jonathan Swift (1667-1745)的代表作,不少学者对它从文学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本论文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译注现象,并强调译注在体现译者身份构建和文学作品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该作品的中译版本比较多,这为版本间的对比研究提供了便利。
一、导言
提到“译注”,首先要面对的是这个名词的由来。中国最早出现译注的形式是在三国时期,当时虽有佛教流行,但“经多梵语,未尽翻译”,而且“译文朴质,义理隐晦,难以索解。而此时,洛阳有支谦,他十岁学书,出烦拔萃,其同学莫不叹服。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语,各方面的基础都很扎实。”(《内明》第213期,静华,慧如2004)。他广泛收集佛经,译成汉文,并将未译的补译,已译的进行订正。同时,还帮助天竺僧维只难、竺将炎译经。自东吴黄武至建兴中约三十年间,共译出 《维摩》、《大般泥洹》、《瑞应本起》经等多种。而且他还首创合译和注经,使经义更加通俗易懂,受到后世高僧道安的赞扬。而西方最早的译注出现在圣经翻译中。
二、四译本中的译注对比
这本书的特色在于译者要如何权衡这么多的译注。笔者认为作者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充分站在读者的角度在思考,例如,第二部《大人国游记》第一章第二段描写海上遭遇飓风,用上许多当时航海的专业术语、设备及描述,以示写实。作者在这里添加了很多注解,例如,“斜杠帆”,作者解释为 “‘Spritsail’,一种以往使用的帆,悬挂在船首斜桁(bowsprit)下的帆桁。”,此外,作者将“Missen”、“the Fore-sheet”、“got the Star-board Tack aboard”,等等,都译为较为专业的词汇,并用较为浅显的语言注解,但是张建和杨昊成的版本都没有译出,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而单德兴的译本标明,“此段中译主要参照辜和特纳的注解本勉力而为,其实此节对于全书的理解和诠释影响不大,作者以此修辞策略故作写实状。(单德兴2004:123)”。笔者为探寻译注的功能,分别从两个方面对四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这里引用的英文为Jonathan Swift原著),即文化常识类和影射讽刺类,其中文化常识类包括人物、地名、度量衡,而影射讽刺类分为人影射、物影射和事件影射三大类。笔者将从以上方面对文本进行分析比较。
1、人物类:
Flimnap the Lord High Treasurer attended there likewise,with his white Staff.
度支大臣弗林那普(Flimnap这是指当时的宰相罗伯窝尔坡尔爵士 Sir Robert Walpole;这是作者所最反对的——译者注)手持白权杖随扈(伍光建1934:18)
财务大臣弗凌纳普也出席,手持白手杖。(脚注30:白手杖为英格兰财务大臣一职的象征(PT 304;ABG 359;IA 56))。(单德兴2004:92)
财政大臣佛利姆奈浦手里拿着他那根白色权杖也在一旁侍奉。(无译注)(杨昊成1995:43)
度支大臣佛林奈浦也手里拿了白色手杖,随侍在旁。(无译注)(张健1948:51)
在上诉这段话中,只有伍光建对“Flimnap”这个人进行注解,并且加上自己的感想——“这是作者所最反对的”。单德兴是加注的“white Staff”,杨昊成和张健是没有译注的。通看整部作品,文中的人物名称很多,单德兴版本采取的策略是在序中加上 “人物与地名表”(单德兴2004:177-180)的部份,而伍光建的版本因为是节选,所以有些地方没有,但是他一般只会对具有影射含义的人物加以注解,杨昊成的版本在这部份也没有加注,张健的版本全文译注都比较少。
2、度量衡类
I perceived it to be a human creature not six inches high.
我看见一个人不过六寸高(无译注)(伍光建1934:2)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人形,不到六吋高 (脚注26:小人国与欧洲的比例约为1:12,书中一直维持这个比例。由此可估算格理弗本人约六吋高。但书中格理弗并未对自己的外形有所描述,......)(单德兴2004:32)
竟发现一个身高不足六英寸...(无译注)(杨昊成1995:5)
发现一个身长不满六吋的,.......(无译注)(张健1948:5)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单德兴版本描述度量衡的方面非常详细,事实上,这部作品中描述度量衡的用语非常普遍,而单德兴译本对此都做出了译注。笔者认为外国的数量单位与中文中的数量单位有所不同,因此注释是有必要的,但是,其他三位译者都未对此做出注解。笔者认为这与译注所要表达出的功能作用是极其相关的,明显的,单德兴的版本做到处处精确,可充分服务学术研究。
三、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文学翻译译注的多元功能。余光中曾经强调过:“一本译书只要够分量,前面竟然没有译者的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译者如果通不过学者这一关终难服人。(余光中谈翻译2002:10)”他还在同一篇文章里谈到,有些译者在译文后加注解,“以补不足,而便读者,便有学者气象。”他这番话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理想译者应该达到的境界。这不仅让笔者想到单德兴老师的译本是何等的高度,他充分的印证了如何尽自身最大的努力以保全原作不容有失。经典文学作品是传承了浓厚的文化和历史,承载着原作者的伟大理想,作为一名合格的译者,应当以最大的努力保全这份珍贵。为了这个梦想,有多少译者殚精竭虑,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力图将国外优秀作品以理想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在这一努力中,作为副文本之一,文学翻译的译注虽然看似无足轻重,却也在服务读者、方便研究和帮助译者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诸多方面默默地发挥着自己的积极作用。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