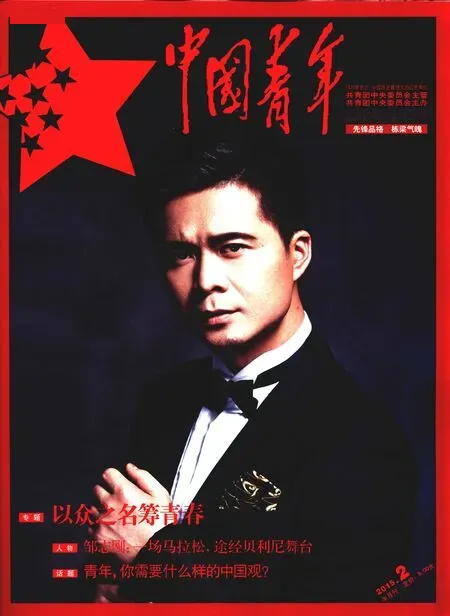王强:用勤奋科研澄澈祖国蓝天
采访/本刊记者 赵涛
王强:用勤奋科研澄澈祖国蓝天
采访/本刊记者赵涛
拳拳报国心,溢于言表。这个80后的年轻教授有着理工科男生典型的踏实,话语不多,质朴无华,却用行动让人们看到行胜于言的力量。
冬日北京,暖阳晴好,APEC蓝的纯净明澈,令人心醉。北京林业大学的校园里,抬头能看到悠悠西山。对王强的采访,从空气质量开始。
王强教授的办公室在环境楼,一座苏式建筑,有意无意间,提醒着人们,这是学院路八大院校之一。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需要工科技术人才,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削减原有的综合性大学,以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这样的形势下,中央选定在北京海淀区集中建立第一批八所高校,他们的名字后人皆知,农大、北航,也包括王强执教的北林大。
走进环境楼,映入眼帘的,是展板上的校训:知山知水,树木树人。这样的校训显示了北林大的文化与优势:先知山知水,再治山治水,最终美山美水。
王强办公室的白板,排满了课题组两年来发表的论文,满满当当。办公桌上,最显眼的是一张合影:王强抱着儿子,妻子偎依在身旁,三口人指点着满树樱花,幸福洋溢。
生活中,他是稳重踏实的人夫人父。球场上,他是激情四射的边前卫。科研上,他有着怎样的故事和经历?
将所学转化为先进技术
王强1981年出生,今年33岁,北林大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15年前,高考的时候选择环境工程专业,除了知道这是朝阳产业之外,更跟王强的经历有关。他的家乡在山东鱼台县,这片因鲁隐公观鱼钓鱼而得名的土地,紧靠微山湖,河道纵横。王强读高中的时候,微山湖周边有不少造纸厂,污水肆无忌惮地直排,颜色褐红,味道发臭,鱼虾一度绝迹。
王强触动很深,他觉得面对污染,不能无动于衷,应当通过技术手段加以干涉。
1999年夏天,王强从山东来到了黑龙江,就读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的六年读书生活,对他的影响很大。“哈工大这所大学,科研能力很强,给人的感觉很踏实很勤奋,无论是学风还是做人。这六年对我很重要,影响了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离校九年,王强的心中依然充满了眷恋。
2005年,硕士毕业的王强考入韩国浦项工业大学,开始了四年的博士学习。
“出国的时候,国内的硬件设备比较差,国际认知度也一般,我们对外界的了解非常局限。”王强说韩国四年,自己最重要的收获是,坚定了做科研的人生规划。
初到韩国,王强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谁知,刚进入实验室就遭受当头棒喝——导师先给了他一个有关“电厂烟气脱汞”的课题。他花了半年时间,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几乎把能找到的文章、专利、报告全都通读了一遍,正待大展身手之时,导师突然告诉他要换课题,让他去做“汽车尾气处理”。
王强心里非常排斥新课题,他知道,在西方国家这是一个冷门,毕业后不好找工作。面对固执的导师,沮丧之后的王强没有放弃。他给自己做工作,虽然研究方向是冷门,但是对于材料的研究都是相通的。为了学到技术的精髓,他开始了早上9点进实验室,晚上11点离开,四年如一日的勤奋钻研。
除了埋头苦学,作为球迷,王强也有自己的放松方式。浦项有支亚洲著名的球队——浦项制铁。每逢中超球队去韩国打亚冠比赛,王强都会去加油助威。韩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很好,王强对于韩国青年人的意志力感受尤其深。“身体素质并没有多少优势,但他们有一股永远不放弃的态度,总会拼到抽筋。我们留学生的球队跟他们比赛,踢到最后,都互相提醒,一定要顶住,他们不到终场哨响起就不会放弃。”王强做实验很苦的时候,总是想一想韩国人的意志,告诉自己,忍一下,就过去了。
2009年博士毕业时,王强已经发表了近10篇SCI论文,并申请了一个国际专利。
毕业之后,出于开阔眼界的想法,王强选择了去新加坡科研局工作,在化学与工程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
“在新加坡工作两年,拿到绿卡绝对没问题,但我没有申请。因为我看到我们国家的空气污染日益严重,我博士期间的方向都成了研究热点。况且,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科研资助、政策扶持的力度都很大,我想应该回国工作。”王强说。
回国的主意已定,问题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和成果回国。王强觉得应该去名校学习。2011年,他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化学系DermotO’Hare课题组从事博士后研究。
2013年,博士后出站后,王强谢绝了导师的挽留,放弃了几十万年薪,被引进到北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主要从事纳米功能材料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应用基础研究,比如汽车尾气氮氧化物及碳黑颗粒催化转化去除、二氧化碳捕集、污水处理等相关研究。
小小的纳米材料,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作为催化剂,把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也可以作为吸附剂,把有毒有害的物质如重金属、染料、污油等分离出来。
对于频频造访的雾霾,虽说机理尚不完全清楚,但共识已经基本达成——不管汽车尾气还是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酸、细微颗粒等是诱发雾霾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强和课题组的工作跟此类污染物的分离和催化转化有关。比如在汽车尾气排气口加催化剂,把有毒有害的氮氧化物和碳黑颗粒转化成无毒无害的氮气和二氧化碳。
王强学术成果颇丰,目前已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SCI论文80余篇,总影响因子高于300,H指数19,被引用1600余次。主持各级各类课题9项,申请国际专利6项,撰写英文专著章节2个;担任30多个国际著名刊物的特约审稿人,回国工作后,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入选国家第五批“青年千人计划”、“北京市科技新星”。2014年,入选第七批“北京市青年优秀人才”和第一批“环境保护部专业技术青年拔尖人才”等。
2008年,时在韩国留学的王强获得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他在获奖感言中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国家为了建设一个更为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大量环境和能源领域的优秀人才!我真心希望能将自己在国外的所学、所见、所感转化为具体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祖国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贡献一份力量。
拳拳报国心,溢于言表。这个80后的年轻教授有着理工科男生典型的踏实,话语不多,质朴无华,却用行动让人们看到行胜于言的力量。
治理污染需要时间,更需要主动努力
《中国青年》:APEC会议闭幕,“APEC蓝”这个词却成为热词流传。想请教一个问题,APEC蓝的出现,是因为排放减少,还是天公作美,即使不限行不关停污染企业也能如此?
王强:肯定跟减少排放有关系。北京周边的电厂、钢厂,排放得多,污染就严重,有风的时候会好一点,没风的时候就有可能形成雾霾天。天气是不可控的因素,治理污染不能靠这种不可控的因素,还是要主动努力。
《中国青年》:向雾霾开战,以一个研究者的视角来看,是前路漫漫还是比较乐观?
王强: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难题。涉及面很广,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有国家层面的。要想经济发展快一点,污染物排放就会多一些,污染治理和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
《中国青年》:六十年多前,伦敦发生过千余人丧生的雾霾污染,如今治理得很好。你觉得目前中国的雾霾只是有一个历史阶段吗?
王强:肯定是,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发展得太快了,大量用煤用钢用水泥,排放就多。另外就是我们的治污技术还不够发达。发展得快,排放就多,也想治理,技术不够,所以就造成了这么个阶段。国外的情况跟咱们恰恰相反,本身排放就少,治污技术也不错。
前两天,一个学生问我,国际上氮氧化物的研究文章为什么发的少呢?我说,因为发达国家已经走过重污染的阶段,基本上研究完了,氮氧化物带来的问题,对他们已经构不成问题了。他们手里的技术咱们也可以买,但是特别贵。所以现在咱们国家特别重视氮氧化物去除。
《中国青年》:学以致用,在国外氮氧化物的研究应用的市场已不是很大。这种研究,对于我国来说呢?很前沿的课题?
王强:不算前沿,也做了不少研究。我们现在需要什么呢?有我们国家自主产权的有效的催化剂或者技术。
《中国青年》:你有六七项国际专利,成果转化方面有怎样的进展?
王强:目前来说还没有。材料出来了,到实际应用还是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稳定性、寿命、成本。
我在牛津做博士后的时候,支持项目的泰国公司发现我的两个专利应用前景非常大,效果很好,一旦投入应用,每年的利润在10亿美元。预计明年会用这个技术做一些产品出来,2017年会有中试(中规模的试验),从小试到中试到生产应用,这是循序渐进的谨慎的过程。你不可能从实验室一下子就跳到工业生产,实验室用大概可能是几克、零点几克,工业用可能是几吨,跨度非常大。
《中国青年》:我发现办公室墙上的论文都排满了,目前你已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SCI论文80余篇,科学情结从小就有吗?
王强:应该不是从小就有的。学习过程中,接触的东西多了,了解深了,慢慢就喜欢上了。我觉得真正打算搞科研,是在读博士的时候。尽管确定比较晚,但我很坚定,也乐在其中。
如果最初选择环境工程,还考虑就业收入之类的话,读了这么多年书,我更看重价值体现,特别是我国已经意识到青山绿水重要性的时候,我更觉得研究有意义。
成功=知识的积累+勤奋的催化
《中国青年》:你去牛津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段名校背景对你有什么影响?
王强:牛津很厉害,这个厉害包括软件硬件。一个科研工作者,能做出优秀成果,不是说硬件够了就可以了,我国现在的硬件一点不比外国差,硬件是可以用钱买的,但历史传承、师资力量是买不来的。
牛津的教授非常牛。你想问一棵树,导师会告诉你一片森林,我把极性物体分散到非极性溶液中的实验,发现了新成果,判断不了它有无价值,还在迟疑的时候,导师很确定地说,我们要申请专利。可见他们的视野与深度。
《中国青年》:回国两年了,觉得这两年的生活和在国外有什么不同?
王强:空气是我最不满意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比较满意。
前段时间,牛津导师问我,你现在觉得自己的生活跟当初的想象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后悔?我说,我的实验室、团队已经建起来了,科研经费很充足,住在学校附近,没有多大压力,不用天天为生活奔波,也不用像过去在国外那样,只能通过涮火锅解决乡愁。其实,我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说,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的中心了,还有比这更大的平台吗?
《中国青年》:从农家少年成长为环境专家,一路走来,你觉得成功的关键词有哪些?
王强:勤奋。所有的成功都是始于知识的积累,加上勤奋的催化。从量变到质变,你说天赋,大家真差不了多少……
《中国青年》:科研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你?
王强:科研最吸引人的地方,有点类似探宝。当你发掘出一个新东西的时候,那种快乐无法形容。当然,如果能应用到人类生活中,这份快乐会放大十倍百倍。
我常跟学生说,我期待你是第一个涉足某领域研究的人,无论实验效果好还是不好。第一个做某项研究,比你在别人的基础上做一些修修改改要更有价值。发现比完美更重要,诺贝尔奖往往只颁给那些第一个发明者,就是这个原因。
《中国青年》:你的科研中,这样的首次体验有哪些?
王强:博士阶段,我首次开发出基于阳离子层状材料钛酸钾的汽车尾气处理催化剂。还包括首次发现插层有机阴离子可显著提高类水滑石的高温二氧化碳吸附能力。
在牛津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极性材料分散到非极性溶液中,即类水滑石材料在非极性溶液中的高度分散。打破了一直以来的观点,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分散,事实上,做一些表面的改进就可以。这让我的导师都感到不可思议。
《中国青年》:刚才你提到诺奖。2014年的诺奖刚评完,我们再一次“隔岸观火”,羡慕嫉妒恨五味杂陈,你的看法呢?
王强:我感觉没必要纠结于何时获奖,功到自然成。我们国家真正的科技发展,才短短三十来年,诺贝尔奖是一个时间的累积,你看类似蓝光LED这样的诺奖发明,都是二三十年前做出来的成果。我给你五个亿,两三年时间,让你拿出个诺贝尔奖来,这不现实,中国科学界需要踏踏实实做事情,打好基础,静待花开。
《中国青年》:作为一个80后青年,一名博导,怎样看待当下的中国?
王强:8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能吃饱穿暖,但吃不好穿不好;1999年我上大学的时候,买个二手电脑需要寝室8个兄弟一起凑钱;我们之间联络是用BBQ;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卖IC、IP、200卡的。但是看看今天所处的时代,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国家领导人勇于开拓创新,我坚信未来将有大把的机遇,广阔的舞台等待我们施展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