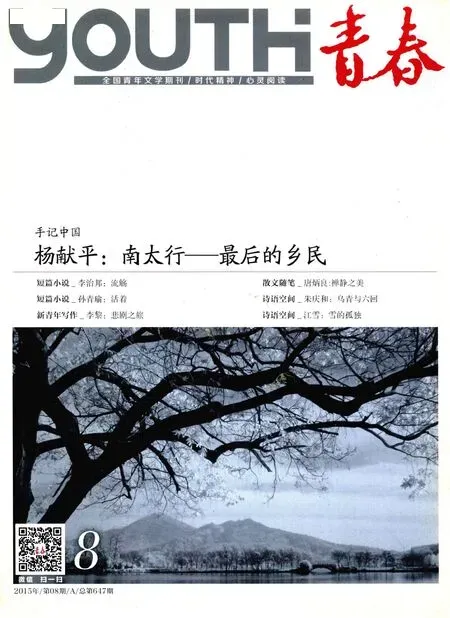流觞
李治邦
一
李重3岁才张口说话,这期间,他父母到处找医生给他看病,怕他是一个哑巴。李重张口说话的第一个词汇,我饿了,而不是喊爸爸妈妈。那一句我饿了,把他父母吓得脸色雪白没有明白什么意思,李重又重复了一句,我饿了。
李重父母都是市里重点中学的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这就是天作之合。所以李重6岁上小学时,家里人都认为他是个不用怎么下工夫就能成为好学生的孩子。可没有想到他语文和数学总是排在全班倒数第二或者第三,弄得他父母没有颜面。可李重就是一张好嘴,讨得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他。到了他上中学,父亲已经是学校的校长,就想方设法给李重弄到自己学校,他要亲自看着孩子有没有长进,因为再没有起色就可能考不上大学。李重依旧不怎么样,有次考数学竟然不及格。为此,他母亲大哭一场。父母让他跪搓板,李重就跪在那开始叨叨,天文地理,说得乱七八糟,就是不停嘴。最后父母无奈让他起来,因为实在忍受不住耳边的聒噪。到了高中,李重的成绩依旧不见好转,倒是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演讲中一鸣惊人,拔得头筹,他演讲的题目是:你要到巴黎和伦敦看看。就这么一个不着边际的主题,听得大家聚精会神,鸦雀无声。他父亲也不明白,李重这个逆子怎么有这么好的演讲能力,其实就是在台上胡说八道,因为他说的很多巴黎和伦敦情况都是他自己瞎编,因为他带着李重去了一趟上海和厦门,里边的很多事情都发生在那里。李重上大学的成绩居然一跃千丈,考进了省重点大学,他父母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模拟考试还排在全班的三十几名。李重觉得很自然,他对父母说,我就是不努力,一旦我努力了,上帝也会微笑。
李重大学毕业后没有歇脚,考到了上海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考到了市文化局的公务员。他结婚了,爱人叫皮特,其实是一个上海人,居然跟着他抛弃了大上海来了这座小城市。皮特人不漂亮,也不爱说话,但料理家务是一把好手。李重父母都退休了,有次吃饭,李重父亲对皮特说,你的话都让李重说了,他这个小子太能说了,死人都能说活了。皮特笑了笑,我喜欢他能说,我就是一个不爱寂寞的人,就是想找一个能说的男人。
李重当科长没几年,就当上了副局长,这个副局长是他竞聘上岗的。当时竞聘,给他的题目是怎么能争得文化强市。李重演说了半个小时,他是第一个上去的,下边的人再上都战战兢兢,因为李重的口才吸引了所有评委。评委是不能鼓掌的,可所有评委都热烈鼓掌,以至于下边的竞聘者是在李重的掌声中上来的,两分钟竟然没有说出话。
也就是四年,局长调走了,李重就当上了局长。
二
春节了,全城都在尽情放鞭炮。
皮特想回上海过节,李重说了几句,皮特就觉得说不过他低头哭了,说,我们以后不争论了,因为每次都是你赢。那天除夕,李重父母过来和他们一家团圆。这时候李重的儿子已经9岁,居然也不爱说话。父亲对李重伤感地说,你把你儿子的话也说了,这将来怎么能行呢,你能不能少说话。你看看现在多说话的下场,言多语失,祸从嘴出,你总会让人家抓住你辫子。李重点点头,说,现在不少人已经背地里整治我了,我这个人话多也得罪人多。母亲着急了,说,你是不是闭住嘴呀,你说谁谁高兴呀,背后给你捅一刀,再给你写几封举报信,匿名的署名的就够你小子喝一壶!皮特嘟囔着,我经常在家里接电话,都是骂他的咒他的,问谁谁也不说名字。李重低下头,儿子说,我们校长让我父亲去一趟,说是要给学校修修舞蹈室,花不了几个钱。我爸爸把人家说了一通,弄的校长见我就瞪眼。李重不高兴地对儿子说,你就别火上添油了。儿子不说话,拿着爆竹跑到外边去放,噼噼啪啪,李重看到窗外的儿子嘟囔着,崩死你!崩死你!
李重春节过后就觉得不能这么说话了,快到不惑之年了,应该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说完会惹祸烧身。文化局在市里就是一个摆设,哪次到市政府开会都坐在最后一排。一年给他的钱是教育局的十分之一,他觉得活得很累,累的原因就是自己不断地在装,还必须装得有模有样,自己真缺点儿生活的滋味儿。他归结自己弱点就是缺乏向往,什么事差不多就得了,很少有过认真的思考。后来,他和父亲有过一次深谈,那次是父亲给他刻了一副图章,他当时不在意。因为父亲喜欢篆刻,他觉得父亲玩物丧志。可当他把父亲的篆刻拿回家认真欣赏后,觉得父亲的篆刻给了他很大生活触及。就是父亲退休后沉湎在篆刻的艺术享受之中,可自己真退休了,除了一张好嘴,还能干什么呢。他到文化局所属的画社去了一趟,画社的社长是省里挂号的书法家和篆刻家,叫于明志。他给于社长看了父亲的篆刻,于社长说,你父亲的篆刻有杭州西湖西泠印社吴昌硕的刀锋。李重看了看于社长,严肃地问道,你说实话,别跟我一样天花乱坠。于社长笑了,我拿给你看呀。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方印,然后盖到宣纸上给他看,说,这就是我收藏的吴昌硕印章,你再看你父亲的,有没有相似之处。李重看了,果然风格一致。他给父亲打电话,问,您这个篆刻有吴昌硕的痕迹呀?他父亲惊诧地说,是啊,你小子能看出来。李重笑了,我看不出来可有人看出来。父亲说,我喜欢吴昌硕,天天就是临摹他的。李重拍了一下脑门,我也喜欢吴昌硕的,咱们怎么一样呢。父亲说,你那是喜欢,我那是崇敬。李重放下电话,对于社长说,你能临摹一幅吴昌硕的字吗?于社长兴奋了,说,李局长,我也喜欢吴昌硕呀。说着铺纸泼墨,给李重写了一副行草。李重看着不住点头,说,太像了,就跟真的一样。李重高兴之余,突然问于社长,知道吴昌硕的行草学谁的吗?于社长张口就答,取法王觉斯、黄道周,并参以欧阳询和米芾笔法。李重再问,那吴昌硕行草的特点是什么?于社长好像打了一针兴奋剂回答,纯任自然,一无做作,下笔迅疾,恣肆奔放,且又笔笔顾盼,字字呼应,篆意楷意相参而生,如枯藤如老树如斗蛇,如高峰坠石,笔挟风涛,呈雄健烂漫、浑穆古厚之姿。李重紧紧攥住于社长的手说,你就是吴昌硕再生呀,我很喜欢。李重临走前,于社长说,画社现在买宣纸的钱都不够了,再批点吧。李重说,给你十万吧。
在回去的路上,李重开车停住了,是停在一个广告牌前。这个广告牌上写着,好听的话不要听,要注意你看到的好地方。其实这是一个新楼的广告语,在广告牌后面就是戳着一幢幢新楼,确实造型别致。李重觉得自己被于社长的好听话打动了,随即就说了一个十万的数字,这对他说也是一笔钱了。原先要给五万,结果一激动给了十万。李重心头涩涩的,他觉得人家说话都是爱听的,自己说话都是人家不爱听的。
三
五一劳动节的文艺晚会审查开始了,李重走进剧场的贵宾厅,等待宣传部的刘部长。快开始了,刘部长才步履稳健地走进来,对李重说,听说晚上有法国的一个歌舞?李重说,人家去上海演出正好接过来,一举两得。刘部长说,一个歌舞多少钱?李重迟疑了一会说,十万吧。刘部长皱了皱眉头说,给了你四十万,这一个就十万,你够能花呀。李重笑了笑,总说我们创建文化强市,这不就是一个体现吗。刘部长摆摆手,你就是一张好嘴,我是说不过你。李重陪着刘部长走进剧场,看见舞台上的法国演员在走台,台上灯光昏暗。李重看出是导演特意安排这样,好区别正式的审查。剧场上空漂浮着一种外国香水气,李重顺了顺,觉得是皮特喜欢洒的那种,说不上什么牌子。总导演孟建凑过来,问李重,李局,进到剧场是不是感觉有一种洋味道呀?孟建是歌舞团的团长,一个漂亮女人,三十六七岁了,依然魅力不减,腰板直挺挺,散发着一种诱惑。她跟李重总是开玩笑,有时玩笑开得很过,李重也不恼。孟建悄声说,我看见你老婆皮特也来了,坐在后面盯着我们呢。李重要回头,孟建用手按住了他的手,说,你就不能不回头呀,好像我操作你似的。你看就看刘部长,你看他眼睛像是钉子,都钉在我胸脯上了。说完,孟建笑嘻嘻走到刘部长跟前坐下,献了一个笑,两个人说什么就不知道了。李重知道孟建就是一个高级瓷瓶子不能碰,碰一下就是粉身碎骨。她丈夫裹走了国投公司一千九百多万潜逃,临走谁都没有告诉,至今没有下落。有人说在澳大利亚,后来又传说在加拿大、塞浦路斯什么地方。但也有说孟建知道,只是封嘴。
审查演出快开始了,孟建对李重说,按说法国歌舞是不审查的,人家就是走台,完了以后就走啊。李重说,刘部长来了,怎么也得演啊。孟建说,那就多加十万。李重狠狠心,多加就多加。孟建走了,留下一个甩来跳去的臀部,李重看见刘部长的眼神还游离在那。刘部长喊着李重,你就不能坐在我身边,我又不吃你。李重过去,刘部长说,一个礼拜以后纪委调查组去你那,你要有准备。李重心里忽悠一下,问,文化局能有什么?刘部长说,你们去捷克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举报信一摞摞的。李重说,那是我们演出去呀,你批我去的,在那轰动呀。刘部长说,你在那摆了四桌招待,一桌六千,四桌就是两万四千,这是不是奢侈呀。李重说,人家都是当地华侨,集资了二十万解决我们演出资金不足,还不答谢人家。刘部长说,那也不行啊,这钱是你自己的吗,那不是国家的吗。李重说,我从二十万出的。刘部长眯缝着眼睛,人家给了就是给国家的,不是给你个人的。李重憋得喘不过气,他马上反驳道,我们歌舞团去捷克是一次成功的演出,市委张书记都表扬了,怎么现在又开始查了呢!刘部长没有说话,演出开始的铃声响了,刘部长说,张书记可能要调走,你这张牌没了。
李重的心掉到了冰窟里,越来越凉。他捉摸不透,什么时候张书记成自己的王牌了。皮特从上海跟过来以后,一直没有工作,只能在一家广告公司帮忙。后来张书记知道了给皮特调到了开发区集团,李重很是感激。其实他跟张书记不熟悉,就是省里一位退休的老领导到这里来,他奉命去陪着省里老领导才跟市委书记有了接触。老领导喜欢聊文化,张书记把李重叫来喝茶聊天,那天聊的是梁漱溟。李重说到了梁漱溟对文化的八个层次,说到了最后的通透,讲得头头是道。聊了两个小时,老领导一直在听李重在讲,从佛学讲到犹太教,从古典音乐说起了波兰的肖邦。老领导走时对张书记叮嘱道,你这个文化局长了不得,你不用就是你的严重失职啊!后来,刘部长生气地找到李重说,你都瞎白话什么了,就你这张嘴早晚会叨叨出大事。你说话又没有把门的,哪句话说错了就是事。你是不是跟老领导说了一句居民上厕所没有准备纸,这不是钱的事,这是一个城市的文明。你不是等于告张书记吗,就你懂,就你明白。你给咱们这座城市八十万人准备纸吧,你看看是文明了还是丢丑了。李重闷闷的,回到家就接到了开发区集团对皮特的调令,因为皮特是学财务的,给了一个财务副总监,尽管副总监有四个。那天晚上,皮特激动地扑倒他,窗外月亮正圆,院子里的丁香树释放着清香。皮特喃喃着,真没想到凭借着你这张巧嘴,就办成了一件大事。你就是我的伊甸园,生命中我只有你。我送给你一季的缤纷,愿你享有早春的新绿。做完爱,皮特磨着他再来一次,说,我做着诗,和你做着爱,可能是天底下女人最美的差事。
法国歌舞上来了,舞台上的一束灯光在游动,一群人在奔跑。其中只有一个女人在静静地矗立着,然后大家停止,她却在乱走着,脚步匆匆像是赶火车,又像是有人追逐她,更像是在寻找她向往的归宿。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焦灼地接触,谁都想离开,可谁的臂膀都挽住对方不放,两人撕扯着,纠结着。李重听到刘部长悻悻地说,这节目什么意思呀?放在五一劳动节晚会不合适,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呀。舞台上,一群红色的人和黑色的人在舞台上积极地交织,色彩在旋转,灯光在摇动,美丽的人体跳出美丽的舞蹈,生命的热量和广袤的原野在溶解,白天和黑夜在日转星移,然后演绎出无数动情动魄的故事。李重翻着节目单,上面写着舞蹈《生命的跳跃》。李重觉得自己好久没有艺术意识和氛围了,一场法国舞蹈的演出让他产生了生疏和新鲜。
审查演出结束了,所有的导演和主要创编都集中到前几排。李重问李部长,您说说?刘部长说,我说什么,你让我怎么说。李重说,那也得表个态呀?刘部长说,你不是挺能说的嘛,你就说吧。李重小声地说,我代表不了您。刘部长说,我哪次和你出来不都是你说,你这么能说,我再说不就是多余吗。李重看着十几个人眼巴巴的眼睛,又看着刘部长不屑的表情。他只好站起来对大家说了自己感受,他说的很内道,甚至连灯光都说到了,确实像一个专家在点评节目。刘部长在他演说的过程中悄然走了,等到李重发现追出来,看到刘部长的小轿车已经启动了,他过去拦住,对摇下车窗的刘部长说,法国的节目要不要呢?刘部长不动声色地,我不懂文学,但我知道法国作家左拉有一篇小说叫《陪衬人》,我就是那个丑陋的女人在陪衬你小子。说完,车再次启动了。李重茫然地站在那里,他看见夜色里的小轿车尾灯一闪一闪的,像是一双警惕的眼睛眨动盯着自己。
皮特走过来,对李重说,你这么能说,不就是把领导晾在那了,就不知道闭嘴呀。李重没好气地说,你别管,我不说,他不说,还审查个屁呀。皮特说,那你就少说,让领导多说几句。李重严厉地说,这么多人看着我们,我为了照顾他的面子,听不到意见,那就是我这个文化局长失职。孟建款款地走过来,笑着握住皮特的手说,你的手好软呀,一看就是贤惠的女人。皮特也笑了,说,你的手掌有力量,是拿住大权的女人。孟建搭了李重一眼,我就是一个导演,背后是你先生。说完叮嘱李重说,法国歌舞的十万你得给,要不要上国庆晚会你今晚必须给我答复。李重不耐烦地挥挥手,上啊,明天把十万打到你歌舞团的账户上,没有这个节目晚会就黯然失色。孟建留给李重一个笑靥走了,走得很慢,她的腰部收缩得恰到好处,承上启下。臀部接连着两条长腿,每一块肌肉都在尽可能地显示女人的魅力。她的脊沟深陷,肩胛骨突出,富于骨感宛如一只蝴蝶扬起双翼。皮特对李重说,不错呀,你的眼神挺有穿透力呀。李重缓过情绪,说,她被她先生无情地抛弃了,我不能再无情,这台晚会就指着她了。皮特不满地说,你对我总是疑神疑鬼的,我没说别的呀。问题是你,我看见你领导始终在看着她,我怕你再看会惹是非。李重恼怒地说,你过来干什么呀,你是嫌我还不累吗。皮特嫣然一笑,说,我就是看看你的演说能力,不错,很有煽动力,说得大家都心潮澎湃的。你别耽误了,我回家给你煮虾干面。
四
五一劳动节晚会结束后,市委张书记破例没有上台接见演员,都风传他调走了,而且是有人举报他才走的。谁举报的是一个谜团,但举报者说的有鼻有眼的,可没有人证实。李重是听孟建说的,张书记在一次会议上狠狠批评了纪委董书记,而纪委董书记有一个分量很重的亲戚在北京。李重纳闷地问,张书记批评他什么了?孟建摇头说,不知道,问谁谁都不肯说。李重走出剧场时,碰见电视台的一个导演,问,是直播还是录播呀。导演摇头,直播不可能了,估计是录播。李重奇怪地问,以前都是直播,为什么呀?导演低声说,回去要剪片子,估计张书记的镜头都不会留,而且你们请的法国歌舞也会砍掉。李重发火了,说,所有市里领导都站起来鼓掌,怎么会砍掉了呢。导演苦笑着说,你以为鼓掌就是支持吗,纪委董书记明确对我表示,我们的五一劳动节让法国人凑什么热闹。李重觉得憋气,他说,这是什么思维,五一劳动节是国际性的,说明我们对外开放的一个象征。导演摊了一下手,我得听领导的。李重觉得这二十万算是白花了,他觉得这是一个最出彩的节目。
李重拖着疲乏的身子要走,他接到张书记的一个电话,我们俩找一个小饭馆坐坐吧。李重有些吃惊,忙问,您说在哪?张书记说,你定,吃火锅,就咱俩。半个小时候,李重和张书记在一个河边的小火锅店坐定,推开窗户就能看到缓缓的河流,河面上泛着城市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快半夜了,小火锅店里没有多少人。李重问,喝点酒吗?张书记笑了,喝啊,别多,一个人半斤就够了。李重笑了,这还不多呀。两个人慢慢喝着,火锅的水滚开了,两人就这么夹着肉喝着酒吃着。张书记说,听到我什么了?李重率直地,你要走啊,说有人在举报你。张书记笑了,他喝酒很慢,但不断地举着杯子。窗外河面上有几只鸭子在游动,发出嘎嘎的声响。张书记饶有兴趣地看着,说,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表面上光鲜得意,可真的等你蓦然回首,不知什么时候早没了踪迹。一段感情要禁得住岁月腐蚀,你来是春天,你不来春风依然在。李重感叹着,我们能成为朋友吗?张书记说,不是朋友能这么坐在这里吗,你说话不拐弯,但诚恳,又一语中的,现在难得啊。李重感触地说,就是爱得罪人。张书记回答,你有担当啊,现在不少人唯上不唯下,我还没走呢,就开始冷言冷语了。李重放下酒杯问,我能问一下您在会上说了董书记什么吗?张书记笑了,很多人都这么问,很简单,我就说了一句要针对事情去找人的线索,不能针对人去找事情的线索,没想到我一句话引起千层浪。李重啊,也会有人跟你过去不去,但该宽容的要宽容,原则不能放弃。想想,对自己也是警示。我觉得举报我就能受益一些,比如一言堂,我真的就是总想自己说了算,肯定就有的地方出了问题。人的权力欲望太强了,不管你做的对还是不对,就有了犯错可能。大自然对欲望就是控制的,比如猫想吃鱼,但猫下不了水。鱼想吃蚯蚓,可鱼上不了岸。
夜深了,两个人走出小饭馆,在月光如水的街上走着。身影拉得很长,春天的声音在悄然作响,那就是树叶子唰唰在动。
几天后,张书记调走了,市长代书记。
皮特那天早晨对李重说,昨天在开发区听到不少张书记的传言,说他批评了一位省里领导,结果就是这样了。李重问,批评什么了?皮特说是省领导来开发区要填一座湖,张书记反对,省领导敲了桌子。李重没有说话,皮特每天给他准备的早点就是牛奶面包,其实他很想吃油条豆腐脑。他从来不对皮特说,因为皮特每天上班都需要一个多小时路程,没有时间给他去外边买。李重觉得牛奶发酸,就问皮特,今天的牛奶怎么发酸呀?皮特不高兴了,说放了几天了,你没有时间去买吗。李重看着电视台回放五一劳动节的晚会,确实没有张书记的镜头,法国歌舞也不见踪迹。他觉得心疼,花了二十万节目就这么删除了。孟建打来电话愤怒地问,法国节目怎么没了呢?李重说,你问我,我问谁呢!孟建说,这两天我想跟你说件大事,你接见我吧。李重看着身边皮特那双好奇的眼睛哼了哼,孟建电话那端莫名其妙地说,我看你也没几天好日子了。说完挂断电话,李重心里咚咚的,因为孟建跟市里头头脑脑打交道多,刘部长说市纪委找他麻烦的话又响在耳边。皮特看着心不在焉的李重笑了笑,我总说你祸从嘴出,你等着,就你那张不饶人的嘴会毁了你!李重狠狠拍了桌子赌气地说,毁了我就毁了我,不行我就教书去。皮特说,你教书去也得留张乖嘴呀,要不然学生家长都得找你,求你教学生少说话。张书记不就是因为放炮了才调走的吗,去了一个边缘城市。李重戳着皮特鼻梁子说,以前你不爱说啊,怎么最近你的话越来越多,不会把你当哑巴卖了!皮特突然扑哧笑了,你也知道多说话的坏处呀,你也知道人家不爱听话的愤怒呀,那你就少说啊……
李重心烦了,就到画社去坐坐。
于社长知道他每次来都要看些什么东西,就把刚买到的吴昌硕和黄宾虹的画册拿出来。李重正翻阅着,宣传部刘部长也不约而至。李重本能地疑惑为什么刘部长突然来,只知道他也喜欢字画。于社长看来跟刘部长很熟悉,就跟他说起李重喜欢吴昌硕的字,而且在临摹。刘部长嘲笑过李重,说,知道吗,吴昌硕的价值不在书法而在绘画,即便是吴昌硕的绘画也不算大师。书法里有王羲之张旭怀素米芾,学哪个不行,非找一个半罐子的,真是猪脑子。一句句敲打着李重,李重觉得不自在,可又说不出什么。刘部长看着李重说,你不是挺能说的吗,你倒是和我说说呀。李重说,我就是喜欢,提不上内道,所以就凭着自己的爱好了。刘部长拍了拍李重的肩膀说,给你长长见识,别觉得自己嘴上功夫了不得,就飘飘然。说着拿出来几幅画铺开,说,这是张熊的《溪阁觅句》,看见两个老翁在山水之间对坐着悠闲地畅饮,一叶小舟在江面上,布局这么清新,一点儿浮躁也没有。你再看看吴待秋的《山色湖光》,一个书生茅屋里而坐,背后是一丛绿茵茵的林子,山上的月影倾斜过来,那就是田园般的生活。最后一张是蔡铣的《枝头鸟语》,一对玉鸟在枝头看着浩瀚的天空,牡丹花绽在枝头下面,连树叶都是清闲的。于社长惊讶地说,这都是您收藏的?刘部长笑了,这是我临摹的,真迹都在博物馆呢。他说完问李重,知道这三个画家吗?李重说,知道一点,名头都不算大。于社长咂着嘴说,可画意深远,悠闲自在,这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刘部长点头,于社长说得极是,我就是临摹他们这种淡远的感觉,今天知道你李重来,也是给你看看。张书记走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失落?还有法国的节目没有播,你是不是也很愤慨?李重看了看没有表情的刘部长,说,你也要让我淡然吗?刘部长说,这三幅画我给你,你就慢慢琢磨吧。刘部长走后,李重问于社长,是你告诉他我来的?于社长有些尴尬,但回答也很干脆,他总问我你什么时候来这儿。李重板着脸,他要在这找我干什么呢?就是想送我这三幅画?于社长机敏地说,绝对不是,他就是想告诉你什么。李重闷闷地问,什么事?于社长说,我不知道,估计想暗示你什么。李重噘嘴,告诉我要淡然,我能淡然吗。于社长陡地提出,是不是要告诉你把事情想开点,别太在意。李重紧逼着于社长,我什么事情要想开点儿?于社长摇头,我不知道,我就是感觉。
李重回到家,打开刘部长送的三幅画,忽然觉得没有了自我,以前那种有什么说什么的日子似乎变成了焦灼和郁闷。他想起一次审查市纪委反腐倡廉节目,当时董部长就在旁边坐着。董部长说完客气地让他说,他站起来就把刚才董部长说的全否定了,他说,反腐倡廉的节目必须是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结合,不是宣传品,是艺术品。贪官不是漫画,必须是符合艺术的人物。廉政也必须可信,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他说完发现大家没有掌声,都怪兮兮地看着董书记,这才发现人家不高兴了。出门在汽车上,李重觉得自己就不懂得委婉,不由自主地骂了几句。但事情过后,他还是这么锋芒所向,说话不含蓄不隐晦。就在那天,皮特主动跟他做爱,两个人在月光撩拨下互相接吻。李重看到了皮特像是一条银鱼,情不自禁地抚摸她光滑的鳞,她透明的骨,她鲜红的脉,摸她生命的等式如此简单。两人做完,皮特意犹未尽地亲吻着他,说,你记住了,嘴不是光说话的,嘴主要任务就是接吻。说完,她哈哈大笑着,扑倒了迷迷怔怔的李重。李重被皮特这句话恍惚了大半夜,早晨起来,他对皮特认真地反驳道,嘴不仅是接吻的,如果说人是一间房子,嘴就是这间房子的窗户,必须要推开通气通风。皮特扫兴地说,昨晚白给你做爱了。李重看出刘部长这三幅画的含义,那就是让他躲进小楼,不管春秋。他看到刘部长在张帆的那幅画上有一句题词,山雨欲来,智慧对之。好像这句话是给自己写的,他铺纸临摹张旭的朱耷的徐渭的,可总是写着写着吴昌硕的字就在笔端流了出来。李重很恼火,就拼命纠正自己,但他知道自己底色就是这样袒露人生,喜欢谁都不会随波而改变。
五
孟建打了几次电话约他,说必须见你了,情况紧急。李重不好多问什么,就约定在一家咖啡馆见面。这座城市的咖啡馆屈指可数,最后找到了一家不大的咖啡馆,就在李重父母家的旁边。李重先到父母家,已经是黄昏降临了。父亲正在给母亲洗脚,这是他每天需要做的事情。有时候,李重过来帮助父亲给母亲洗脚,水是热热的,哪次母亲的脚伸进去都会变得像红薯一样。父亲悄悄告诉他,说你母亲可能得了老年痴呆症,平常话很少,很多记忆都忘掉了。父亲很难过,母亲却很慈祥地看着李重,说,这两天都是想着你的事,你小时候不会说话,我就着急逼着你说,你就是不说。后来我左右扇了你两嘴巴,你哭了,说,如果我说了你不打我就总说。母亲咯咯地笑着,李重低下头,眼眶红红的。母亲接着说,我记得你上小学那天是礼拜一,我让你买了两个苹果,因为你喜欢吃。当时给了你一块钱,你回来告诉我花了九毛,我说不对,应该是七毛。你非要回去找人家,我拦住你说算了,你说不是两毛钱的事,是不能这么做。你过去就跟人家说,起初人家不认账,你就从人家钱抽屉里翻出那一块钱,又掏出一毛钱。说得人家红了脸,你教训了人家一顿跑回来。我说,你这么爱较真长大非吃亏不可,你说吃亏就吃亏,我也不能憋屈自己。说完母亲就抽泣起来,说,你这爱说话爱较真的毛病都是受我遗传,你看我现在想说,但不知道说什么,总是跟你父亲较真吵架,我知道你父亲疼我爱我,他总让我……母亲说不下去了,眼泪留了满腮。父亲拿过来毛巾给母亲轻轻擦着,不断地擦,母亲不断地流。李重给母亲擦着脚,看见母亲脚趾头都是老茧子。他想起小时候母亲背着他,他三四岁时还背着。原因就是他不爱说话,母亲就说你要说话。李重记得对母亲说过,你要让我说话就背着我,我就说话。于是母亲就背着他,他在母亲后背上觉得特别惬意,于是就给母亲讲故事。都是他看过的连环画,讲岳飞,讲杨家将,讲关公,最后讲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这些连环画都是母亲给他买的,讲得母亲的头颅总是高昂着,她觉得儿子讲这些故事是那么光荣的一件事。
咖啡馆是在六楼,这座城市高层不多,所以显得咖啡馆的霓虹灯好像在夜空闪烁。孟建选择了一个靠窗户的小桌子,窗户外面就是河。河水在街灯的映照下,显得很悠闲。有小船在河上荡漾,有人在唱歌,歌声在水面上尽情漂浮。咖啡馆里轻声播放着乐曲《沉思》,显得万籁俱寂。远处传来汽车的喧嚣声,天上飘下细雨,与乐曲浑然一体。孟建问,知道这首曲子是谁做的吗?李重说,马斯涅。孟建笑了,你真是文化局长的材料儿。李重看见墙壁上有一张特大的彩色相片,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在森林尽头有一条幽冷静的小路。孟建说,我晚上睡觉常常半夜就醒,醒来就睡不着。我和他离婚都没有手续,其实我知道他曾经偷偷回国一次,他可能实在不忍心看我守这份孤独,就托人告诉我离婚。我对那人说,我起码要见他一面。后来那人答应他见我,我到了指定的地方没有看见他。他托的那人说给我三十万算是补偿,我没有接受。那人说钱是干净的,我说钱没有干净不干净,就是人的问题。后来他突然没了音信,我听说公安局知道他跑回来了在抓他,有人说我告的密。我不知道其中藏有什么玄机,是整治他,还是冲着我。有次,我请你和皮特吃饭。你们两个人在我面前掩饰不住幸福,逗说逗笑,餐桌弥漫着一种温馨。你们走后,我马上就陷入一种强烈的孤独气氛里边拔不出来。李重抿了一口咖啡苦苦的,其实他不能喝咖啡,喝了就甭想再睡觉。他问道,看你不是挺轻松的吗?孟建说,我表面装得很轻松,一个女人在孤独的日子里想念心爱的人简直就是受刑。我摆脱的办法就是加倍地投入到演出中,弥补那一份空白和孤寂。记得我们在捷克布拉格的查理大桥,那天我拥抱了你?李重笑了笑,换谁站在你面前都会得到你的拥抱。
咖啡店里只有他和孟建,皮特不断地发短信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李重问,你找我来不是倾诉的吧,出什么大事了?孟建说,我知道消息,纪委董书记要找你谈话。李重的眼皮有些发重,几天没有睡好觉了。他说,我知道是因为在捷克布拉格那四桌饭。孟建诧异地,你怎么知道的?李重说,刘部长提示我的。孟建说,他们是不是散风呀,这个事情说重就重说轻就轻。李重说,那是当地华侨给的赞助费,当然要答谢了,而且就是用他们的钱,你可以作证呀。孟建摇头说,不那么简单,还有人家给的琥珀呢,你是不是留了一颗,价值在一万左右的?李重有些发懵,说,不是转给你了吗。孟建说,那也是给你的,你是团长啊。李重嗓子眼干涸,就要了一杯水喝下去。他说,我不会知道价值在一万左右啊。孟建说,当时你问了值多少钱?人家说,就是一颗石头。李重说,对啊,那怎么出来一万左右呢。孟建说,我回来以后到珠宝店里问了就这个价,而且说这颗琥珀是天然的,而不是后期机制的。说着孟建把那颗琥珀拿出来递过来,李重觉得实在天生丽质,晶莹剔透。孟建说,这也是问题,你收了人家的礼,这绝对是错误。李重脑袋热热的,孟建说,我退给你,你给董书记吧,算是一种上缴。李重悻悻地,这算什么,人家问你早干什么去了。孟建说,问题是你给了我,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问题。李重说,你是歌舞团团长,演出获得成功跟你有关呀。孟建笑着,这就是有了暧昧色彩,你的问题就更是严重了。李重生气地说,我没那么复杂,你有功劳就奖给你,而且我当着不少人的面给的你。孟建说,这就是明目张胆了。李重把琥珀还给孟建,打了一个哈欠,你把琥珀退给我显得更乱了,我自己做事自己解释。
李重回到家,皮特在床上等着他。没有开灯,李重脱完衣服躺在床上,见窗外的月光很透彻,涂抹在玻璃上显出一层银鳞。皮特问,那么晚回来跟谁呀?李重说,朋友。皮特不高兴地问,是不是孟建?李重说,是又怎么样啊?皮特坐起来,刚才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和她在喝咖啡。李重也坐起来,这是谁在盯着我!皮特说,我说你得罪人都不知道怎么得罪的,而且说你们很暧昧。李重气哼哼地说,那咖啡店就是屁大点的地方,打电话的人怎么看出我们暧昧来了。皮特说,你要小心,就两个人怎么能在一起呢,这就给人家说话的机会。你现在是文化局局长,不是一个普通人。我现在跟你总是担惊受怕,就是你那张嘴不断制造麻烦。说着,皮特抱住了李重,湿漉漉的嘴唇贴在李重有些哆嗦的嘴唇上。接吻了,显得不是很火热。皮特说,我父母退休了,你跟我去上海吧。李重说,我不当逃兵,我不能自己缝上自己的嘴!李重倔强的血液在沸腾,他就是这么一个极度扩张自己不服输的男人性格。他看见窗玻璃上留着大量的雨水,一只鸟在窗台上躲着雨。他看见鸟忽然抖着翅膀飞走了,他就向往着能住在鸟居住的地方,认为那是他的王国。深夜,李重梦见在布拉格查理大桥,夕阳西下,蔚蓝的伏尔塔瓦河缓缓流淌。孟建亲吻着自己,他也投入地亲吻着她,忽然他就看见董书记就站在旁边专注地看着他们。他惊醒,看见窗台上那只鸟依然在等着雨停,他怀疑是不是另外一只,因为他看见鸟展着翅膀在雨中翱翔。
六
礼拜一上班,李重接到了董书记的电话,让他到市纪委去一趟。
连续两天的雨骤停,晨光从一层云彩的缝隙里泄了下来。在车上,孟建从微信上发来一组照片,李重看到董书记在和一些人吃饭,桌上有酒。他回孟建,什么意思?孟建回复,他也会这样。李重不在意,觉得自己不会用这些照片反驳董书记。微信上不知谁发来另一张照片,是董书记办公室墙上的一幅画,李重一眼就看出是黄宾虹的,画面很模糊。然后是一句话,在纪委书记办公室里有黄宾虹的画说明什么问题,黄宾虹的画多少钱,究竟谁给的。李重脑子有些乱,皮特打来电话,说,你能不能忍耐一点你的嘴,董书记说什么你就听着,不要解释。李重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上午要跟董书记见面呀?皮特说,有人告诉我。李重立即追问,谁告诉你?皮特放下电话,李重觉得这都是谁这么挑唆。路上不断地是红灯,李重预感今天上午会是一场激烈交锋。他把捷克那天吃饭的所有票据都带着,哪笔钱是怎么花的一清二楚。当地华侨是多少人发起的,所有的赞助钱一笔笔细目一目了然。他记起那天谁送给他的琥珀,是一个中年妇女叫倪阿年,浙江杭州人,在布拉格生活了二十年,专门经营琥珀生意。那天吃饭,他和倪阿年说起了作家郁达夫,说得倪阿年很是激动,因为倪阿年说自己就住在场官弄巷子里,跟郁达夫是邻居。那天李重站起来朗诵了一段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倪阿年流下泪。当时倪阿年摘下琥珀给李重戴上,说,记住了这是我送给你的,不值钱,就是一份对祖国的感情。后来,李重叫来了孟建,说,琥珀奖给你了,你们的演出给祖国争了光。李重觉得记忆闸门打来了,当时所有的场景一一再现,他看到的是一张张华侨洋溢色彩的脸。他愤慨是谁举报的,举报人在不在现场,为什么会从龌龊的角度看那次充满人情的宴会。他觉得悲哀,自己在拳击场上,却不知道对手是谁。但被对手打得鼻青脸肿,旁边还有这么多观众在鼓掌。
走进董书记的办公室,董书记过来问他,你喝什么茶啊?李重看到墙上那幅黄宾虹的画就居然笑了,随口说,这是你找谁临摹的,这幅叫作《云归草堂》,真迹在一个姓丰的收藏家那。董书记也笑了,我因为这幅画惹祸,就是宣传部刘部长临摹的,太像了吧,是不是以假乱真呀?李重走进看了看,说,印章作假不够,有硬伤。还有笔墨枯的部分不够,除此都很地道,还是有一派生机盎然的气象。董书记拉着李重坐下,说,你内行啊,骗不了你。但谁来了我都说是真迹,谁都相信。说完,他又哈哈大笑着。李重知道大幕就要拉开了,他从包里把票据一摞摞地拿出来放在桌子上,董书记认真地看着也不说话,然后喊了一嗓子,有人推门进来。他说,把负责宣传的黄主任叫来,就说李局长来了。说完接着看这些票据,不一会黄主任走进来,坐在李重跟前。李重认识他,黄主任是宣传室主任,市纪委半年前曾经邀请孟建的歌舞团为基层纪委干部演出了一场,就是黄主任负责。当时李重要了三万,说不能白演。后来董书记找李重,不高兴地说,还没有听说找我们要钱的。李重说,歌舞团是企业了,演出是有成本的,三万是少找你要的。董书记无奈地说,只能给你一万,多一分也没有了。李重青着脸说,没商量?董书记说,我口袋里只有这点钱了。李重说,那你就欠着我两万啊。董书记玩笑地说,你就不怕得罪我?李重说,我怕什么,又不是进我腰包。董书记指着他说,你等着,有你小子求我的时候。看着董书记这么看着票据,李重想,真是一报还一报呀。董书记看完后,看完了,很清楚。这些情况举报人都没有提到,我们要跟举报人说明情况。李重问,实名举报的?董书记点头,说,举报和实际相差很大。李重说,琥珀的事情还需要说嘛?董书记说,不用了,我们调查了当时情况,这很正常。后来也问了,这个叫倪阿年的人在当地是爱国华侨,做了很多有益祖国的事情。李重疑惑地看着董书记,那你找我干什么?董书记笑了,我找你就是你有事啊,邪门了。我们想举办一次廉政文化进基层活动,想去一百个社区,一百个村,让你给我们帮忙,是不是让文化馆的人做这件事?黄主任说,我私下跟文化馆的李馆长说了,他说必须要跟你说。李重缓口气,打个电话就不就完了,还这么神秘兮兮的。董书记诡秘地说,我想把我欠你的两万给你,你就跟文化馆说,算是他们的活动经费了。李重有了火,说,两码事。董书记说,一回事,你跟我们市纪委干活就得倒掏钱。李重站起来,我算计不过你!
董书记送李重出来,李重看见雨又开始下了。
够烦的,已经下了三天了,如一个紊乱的女人例假没完没了。李重看着董书记问,我说话直,五一劳动节的节目为什么删掉了法国歌舞?董书记眨巴着眼睛,我不管文化啊,这事你得问刘部长。李重说,你不是跟电视台导演说的吗,说让法国节目凑什么热闹呀。董书记想了想,说,是我说的,我觉得法国那节目不怎么样,实在看不明白。我说的就是自己观点,这有错吗。李重不平地说,结果就给我砍掉了。董书记说,那是张书记意思吧,他把自己的镜头也砍掉了。李重一悸,说,他为什么砍掉呢?董书记说,我就不知道了。李重再问,张书记批评你的话是什么?董书记笑了,都问我这件事,很简单,让我冲着事去,别冲着人。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以前是有些偏激。比如对你,我就觉得你太骄横了,总想杀杀你的霸气。现在想起来像你这样敢说的人太少了,都说祸从嘴出,谁都唯唯诺诺。对了,张书记走时让我盯着你,怕你改变了自己风格。李重看见雨越下越大,看见他和董书记都在雨中淋着呢,就慌忙钻进车里。他摇开车窗,董书记凑过来说,很多事情不要听别人说,要自己亲自去体验。你知道的不见得是真相,真相需要胆识和正气才能获知!
七
李重在雨中行驶着,他不知道开到哪里。
他脑子里始终在纠结着,找不出头绪。这么一个恶作剧的结果,突然他觉得好像谁在布局。他回想与董书记交往的每一个细节,真的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轻描淡写的构图。他开出城区,继续朝着郊区的一个小镇开着。这个小镇他曾经来过,就在山脚下,有一条小溪湍湍而流。他和刘部长在这里钓过鱼,他不太会钓,可刘部长满篮子都是活蹦乱跳的鲜鱼。他问过刘部长,你怎么就能钓得那么好呢?刘部长意味深长地说,首先你要放好了鱼饵,你需要诱惑鱼儿上钩。你要让鱼吃上鱼饵,刚吃就钓是上不来的。鱼还没吃痛快,你迅速起杆儿,鱼才能带着你的鱼饵上来。这需要火候,你不能太着急了,但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开到了小镇已经是中午了,因为下着雨,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湿漉漉的。他没觉出饿,但也是走进了一家鱼馆。那次在这和刘部长吃的鱼,刘部长问他是当鱼头还是鱼肉还是鱼骨头。他当时回答,我当鱼头。刘部长笑了,说,你就是想逞能,鱼头以前是被人扔掉,现在端上来是被人先吃了。我当鱼骨头,宁愿让人把我扔了,我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找了一个犄角旮旯,李重要了一盘香糟小黄鱼,一碗热面汤。他看手机,因为跟董书记谈话,手机放在了静音,发现都是未接的电话号码,足有上百个。其中打得最多的是皮特和孟建,还有局办公室主任、于社长,竟然还有刘部长两个。他给皮特回了电话,皮特惊讶地问,你是李重吗?李重说,废话,你神经啊。那端皮特呜呜哭着,哭得很伤心。李重烦躁地说,你哭什么,出什么事了?皮特断断续续地说,都说你双规了,你现在能接电话呀?李重笑了,谁双规了,我这不好好的。皮特说,我跟每一个人都说你不会双规,但你就是不接电话。李重哼了哼,说,我不接电话就双规了?皮特说,你去了市纪委呀。李重恼怒地说,去市纪委就是要双规呀。说完,李重放下电话,他继续静音,他不想回答除了皮特任何人的电话。
他吃完饭就在小镇上走着,小镇都铺着青砖,可能走得太久远了,青砖上有了很多坑洼的沟沟坎坎。雨停了,他在一处廊蓬处看见两个人下围棋。他走过去,下围棋的是两个老人,一边摆子一边聊天。其中一个说,你看着棋盘被分割成324个大小相等的小方格和361个交叉点,就是一张大网啊。这种看不见的大网密布天空,覆盖天空,也覆盖了世界。天地之间真如老子所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另一个说,没见几个真正在围棋里厮杀的,说起来都是圈地运动。谁占多了谁就赢啊,差一子都不行。那个笑了说,围棋要是圈地那就不是围棋的本意了。真正的围棋是黑白之吻。李重困了,他昨晚都是在噩梦中。他无意中走到一个街角处,有一张藤椅在摇晃,旁边有一个竹子茶几,上边戳着一把泥壶,估计是有人在这里躺着。他舒服地躺上去,没摇晃几下就睡着了。
他梦见自己飞起来了,像是那只停留在自家窗台上的鸟……
小镇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