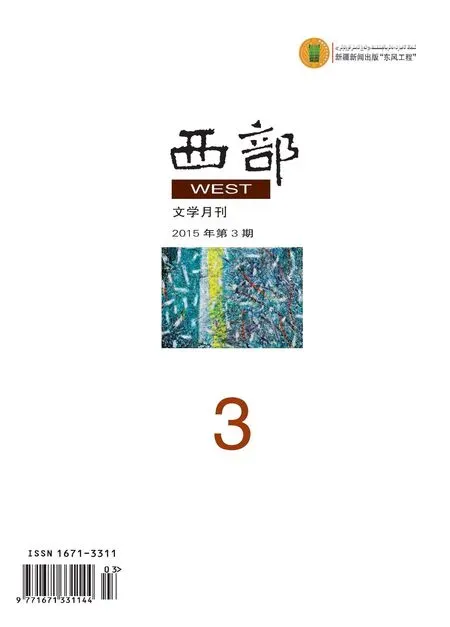人生笔记(节选)
伊甸
名字
我们的名字和我们生死相随。很多时候,我们与我们的名字浑然一体,密不可分。比如我的名字是伊甸,别人叫我的名字,也就是在叫我这个人——一个肉体和精神的我,一个有着特定职业、特定经历和特定性格的我。我就是伊甸,伊甸就是我。但我们的名字比我们活得更久长。我活着,就是伊甸活着;我死了,也就是叫伊甸的这个人死了,但伊甸这个名字还不会立刻死去,它还会在亲人和朋友们的心中,在某些纸上,活上几年乃至几十年。
名字是我们最忠诚的伙伴。爱情、荣誉、金钱都可能随风而逝,唯独名字像大山一样耸立,最可怕的风暴也难以把它吹走。哪怕是一个你已停止使用的名字,它仍然会死死地纠缠你的一生,甚至在你死后还会不依不饶地缠住你,你根本不可能逃脱。比如一个叫冯文炳的年轻人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名字,就叫做废名。”虽然他不要“冯文炳”这个名字,但这个名字还是紧紧跟随“废名”闪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在介绍废名时总不忘跟上一句“原名冯文炳”。
名字有一种神秘的作用。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叫万家宝的人能写出《雷雨》、《原野》这样深刻剖析人性的剧作,一个叫刘军的人能写出《在哈尔盖仰望天空》这样超凡脱俗的诗歌。同样,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笔名叫“仇恨”的人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网名叫“天下第一”的人能写出一首好诗。我并不相信姓名预测、姓名占卜这类神乎其神的东西,但名字确实会和人的命运、人的个性发生紧密的联系。名字的含义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微妙的暗示,它以不可察觉的方式悄悄地作用于人的行为、人的个性。另外,周围的人也会以某种思维惯性看待具有某类名字的人,这种思维惯性常常表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比如,我们遇到名叫“繁漪”、“莎菲”这样的女子,肯定不会把她们看作村姑;我们遇到名叫“翠翠”、“阿珍”这样的女子,肯定不会把她们看作贵族。我父亲的名字叫“阿毛”,他的出身大家肯定能从名字上猜个八九不离十。人们对某个名字的感觉会无意识地影响自己对待这个人的态度,久而久之,会影响这个人的性格、气质乃至命运。这种影响往往无法察觉,所以也无从提防。反过来,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和人生态度,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们对他的名字的感受。比如“爱玲”这个名字,单独来看确实俗不可耐,但今天我们说起“张爱玲”这个名字,不仅不会感到“俗”,而且在我们的感觉中,这个名字是和那些灵慧隽逸、才华横溢的作品浑然一体的,于是这个名字就有了魅力,有了光芒。张爱玲曾经说过:“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个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张爱玲”这个名字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作品,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
一些人长大后改掉了父母给他取的名字,一些作家和诗人给自己取了笔名。这些人给自己取的名字中,多多少少显示出他们的审美趣味,他们的人格境界,他们的个性、气质和梦想。现代作家许地山在他的散文《落花生》中写到落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不是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许地山以“落花生”为笔名,这个笔名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人生志向:踏踏实实做一个有用的人。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朗赫恩·克莱门斯。他曾在密西西比河上当领航员。当时轮船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通常以十二英尺水深较为安全。当水手们喊出“两倍六英尺水深——Mark Twain”时,处于高度警觉的掌舵手就有了安全感,可以放心驾驶了。为了纪念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他就选用了水手们常喊的“Mark Twain”作为笔名,表明他对劈风斩浪的掌舵职业的热爱。
名字是一个符号,但它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它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生命本身。我们的生命明亮而纯粹,我们的名字也就像溪流冲刷的鹅卵石,光洁而美丽;我们的内心阴暗,言行卑琐,我们的名字也就像阴沟里的污水,人们会捂住鼻子远远地躲开。一个高贵名字的主人,他的灵魂里倘若有泥土的踏实和淳朴,这个高贵的名字才是货真价实的;一个朴拙名字的主人,他的灵魂里倘若有一片辽阔纯净的蓝天,他的生命就是高贵的,生命的高贵会使他的名字也一点点高贵起来。
钥匙
钥匙是锁的敌人还是锁的朋友,是锁的奴才还是锁的老爷?钥匙打开锁,是对锁的征服还是对锁的服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钥匙丢了,锁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唇亡齿寒”、“生死与共”这样的成语用在锁和钥匙的关系上似乎有点矫情,有点故作惊人,但这何尝不是事实?
我们随身带着钥匙,意味着我们有权利打开某些门,我们有权利进入这些门或者支配门内的东西。婴儿没有钥匙,因为他还不懂得使用这些权利;囚徒没有钥匙,因为他被剥夺了这些权利。流浪汉不需要钥匙——除非他身上珍藏着一把家里的钥匙。有的流浪汉连家都没有,天地如此之大,世界上的门如此之多,但没有一扇门等待着他去开启。口袋里放着一串钥匙的人是幸福的,有那么多的门等待着他去打开,总有几扇门里藏着他喜欢的或者需要的东西,比如家,爱,财产,某种安定的生活方式,某种权利等等。寒风凛冽的日子或者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个人从异乡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掏出口袋里的钥匙,“咔嚓”一声,一片温暖、温柔、温馨像神话中的世界为他敞开……那真是天上人间的欢乐!
然而,并非一个人的钥匙越多,就越幸福。谁会认为管家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把钥匙意味着一份权利,同时也意味着一份责任。钥匙越多,责任越多。太多的责任会把人压得直不起腰来。况且掌管钥匙的责任和掌管大印的责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责任,前者的责任是服从和忠诚,后者的责任是谋划和指挥。前者是后者紧握在手心里的一把钥匙。掌管的钥匙一多,人也变成了钥匙。
据说某些大国的总统出行,身边总有一个随从为他提着核指令箱——钥匙当然由总统掌管。总统的这把钥匙可是关系着一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人的命运之门啊!假如总统突然发作精神病,像儿时玩玩具一样要玩玩这个核指令箱——只有他懂得怎么玩,钥匙一旋,潘多拉的魔盒就会被第二次打开……
所以跟很多人的命运有关的钥匙,是不能只掌握在一个人手中的。
丢了一百元钱,损失的就是这一百元钱,丢了一把钥匙,损失的不仅仅是这把钥匙,起码还要损失跟这把钥匙有关的锁。还可能损失这把锁锁着的门,因为砸锁的时候很容易把门也损坏。还可能损失门里面的东西——贼用你丢失的钥匙打开了你的门,他偷得十分潇洒、从容。还可能损失人的生命——歹徒在拿你的东西时你正好回来,他便一刀捅死了你。这样的推理不能说是危言耸听,因为很有可能,人家是在你的门口捡到了你的钥匙,偷心和杀心本来仅仅是潜伏在他体内而已,但这把轻易得到的钥匙打开了他体内的魔鬼之门。还有一种可能:某个居心叵测者早就在觊觎你的东西,你以为你不小心掉了钥匙,实际上是人家千方百计从你那里偷去的。我有一个做事特别严谨周密的朋友,如果他掉了一串钥匙,哪怕还有备用钥匙,他也一定把那些锁全都扔掉,换上新的锁。他害怕捡到钥匙的人会来打开他的那些门,尽管这样的可能性很小,但很小的可能毕竟也是可能,所以我对那位朋友的警惕性表示理解,并愿意向他学习。
你爱着的人把他(她)住处的钥匙交给了你,那是一种承诺,一种把自己的一切都准备交给你的信号和密约。这把钥匙比口中的誓言更神圣,更有力量——你要对得起这把钥匙。你的某位朋友把他住处的钥匙交给了你,那是一种信任,一种深情厚谊——你也要对得起这把钥匙。实际上,我们应该对得起我们的口袋中、随身包里、腰间那钥匙串上的每一把钥匙,因为一把钥匙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份权利、一份责任。好在我们没有太多的钥匙。
谦卑
谦卑是一种稀罕的品质,又是一种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品质,就像被铺天盖地的乱石、污泥和灰沙掩埋的钻石。谦卑不是那种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或真诚、或假模假样的谦虚,也不是自卑——那种像老鼠一样胆怯、犹豫和神经衰弱的东西。谦卑是对神圣和美好事物出自内心的敬畏、向往,以及伴随着这种敬畏和向往的个人的自审和自省。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中偶尔发现过这种谦卑:“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躁动的、喧哗的八十年代,一天中都可能出现四个季节的变幻莫测的八十年代,每个人都拼命地想表现自己、突出自己,这样的年代能够出现一种叫作“谦卑”的珍稀之物,哪怕如流星一闪,也实在令我们蒙尘的心灵怦然一动。
中国这块土壤很难生长这种叫作“谦卑”的植物。历史上,人们习惯了当奴才,战战兢兢,畏畏缩缩,俯首帖耳,察颜观色,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少数人混成了“老爷”,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谄上欺下,见风使舵,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无论奴才还是老爷,缺少的是平等意识和人格尊严,而谦卑这种品质只能属于那些具有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的人。一个社会愈是能够保障人们的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谦卑这种品质愈能闪闪发光。相反,一个扼杀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的社会,是很难出现谦卑这种品质的。1958年,诗人郭小川在他的诗歌《望星空》中写下了这样四句诗:“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诗人不过稍微表现了一点对宇宙的敬畏之情,就被人指责为“极端陈腐,极端虚无主义”。在喧嚣、熙攘、轻薄、愚妄的尘世间,诗人找不到为自己辩护的一席之地。当整个社会失去理性,排斥常识,容不下谦卑,容不下诚实,容不下灵魂的光明澄澈的时候,灾难就会以不可阻挡之势汹涌而至。
谦卑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猫小狗,它是一座精神圣殿,建筑在人的信念之上。谦卑的核心是心灵深处的善和自信。谦卑绝对不是软弱和胆怯,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坚定,一种超然。它是有力量的,它的力量不张扬、不引人瞩目,却像江水一般绵绵不尽。所以泰戈尔说: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一片平稳、平衡、平静、平淡、平庸之中,谦卑仍然是稀有的。然而,有一个诗人的诗向我们显示了谦卑的力量,让我们麻木的灵魂为之一震。这首诗的题目是《惭愧》,作者杨键。“像每一座城市愧对乡村,/我零乱的生活,愧对温润的园林,/我恶梦的睡眠,愧对天上的月亮,/我太多的欲望,愧对清澈见底的小溪,/我对一个女人狭窄的爱,愧对今晚疏朗的夜空,/我的轮回,我的地狱,我反反复复的过错,/愧对清净愿力的地藏菩萨,/愧对父母,愧对国土,/也愧对那些各行各业的光彩的人民。”短短的一首小诗,杨键充分地表达了他在所有善、美和神圣事物面前怀抱的谦卑之情。杨键诗歌中的这种谦卑之情并不是流星一闪,昙花一现,“谦卑”几乎是杨键全部诗歌的主题。杨键的诗歌是从他心灵深处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那么可以说,“谦卑”也是他的灵魂的主题。杨键以谦卑征服了我们,他的诗以朴素的语言传达了一种人格的力量——谦卑的力量。他的谦卑中包含着悲悯、仁慈、宽容、淳厚……这是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灵魂丢失已久的东西,杨键把它们拣了回来,让它们重新在诗歌中散发光芒,重新在我们灵魂中散发光芒。由此我更相信西川说过的一段话:“一首优秀的诗会具有宗教般的净化力量,使我们的沉默如潮涌,使我们坚信世间会有奇迹发生。”奇迹是:一个灵魂的谦卑,有可能使一百个甚至一千个灵魂谦卑起来。
记忆
记忆缺少一种独立和自由的品质,它过分地依赖于人的记忆能力,依赖于人的情感深度,依赖于情绪刺激的强弱。最近,我十九年前的学生举办同学会,他们邀请了我。一个十九年不见的女学生问我:“你还认识我吗?还记得当年你写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吗?”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在我记忆中居然没留下丝毫痕迹,更不要说纪念册上的留言了。我带着愧意摇了摇头,她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她告诉我,当年我在她的毕业纪念册上是这样写的:“二十年后我仍然认识你!”当初我这样写,也许是强调我对她的印象之深,字里行间还隐隐约约藏着我对她的美丽和可爱的赞许,但它毕竟跟我灵魂深处的渴望和疼痛无关,记忆便缺少了情感的支撑。这样的记忆自然是不可靠的,当初我太相信自己的记忆了,我的记忆轻而易举地背叛了我。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呈现了两种记忆:一种是带有情感强度的记忆,那记忆与生命同在;一种是与感情无关的记忆,这样的记忆自然会像烟一样消散。女人因为爱得刻骨铭心,她的记忆中收藏了与这份感情有关的一切细节:“每当我在楼梯上碰到你,而又躲不开的时候,由于怕你那灼人的眼光,我就低头打你身边跑走,就像一个人为了不被烈火烧着,而纵身跳进水里一样……”“你站了起来,凝视着我,十分诧异,充满爱怜。你抓住我的肩膀……”女人的爱痴迷得就像一种充满献身渴望的宗教信仰,哪怕她活上一千年,她关于那个男人的记忆也永远不会消逝。而那个男人,他一生中曾经和她一起度过四个晚上,但他从来没有爱过她,他和她在一起,仅仅是出于他寻欢作乐的风流本性。她一出门,他就会把她遗忘。当他收到女人在临死前写给他的信的时候,他依然记不起这个女人的模样来:“这些回忆模模糊糊,朦胧不清,宛如一块石头,在流水底下闪烁不定,飘忽无形。影子涌过来,退出去,可是总构不成画面……”在茨威格的这篇小说里,人的记忆完全是依赖于情感的。有多深的情,就有多深的记忆;没有情,也就没有记忆。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存在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戴望舒这首《我的记忆》中的记忆,是那种伴随着心灵的震颤、痴迷、狂欢和疼痛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当然是“忠实于我的”,它与生命同在。这种与生命同在的记忆不会很多,我活到了五十多岁,许多未曾忘却的往事,如烟如雾如梦一般朦朦胧胧、缥缥缈缈,但有些镜头却像刻在青铜上一样,永远那么清晰。比如最宠我的阿婆(奶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饥饿而死,她躺在灵床上的躯体瘦骨嶙峋,仿佛一根被烧焦的木柴;我十七岁进工厂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大口大口的鲜血吐在地上,像被狂风吹落的桃花;三十五岁始得一女,第一次把女儿抱在手上时,我用表面的庄重掩盖着内心的狂喜,就好像皇帝登基一般……这些浃髓沦肌的痛苦和欢乐,必将是我永久的记忆,这些记忆和我的生命、我的灵魂生死相随。
并不是人越活得长,记忆越多。记忆的丰富与否,取决于人一生中情感的丰富与否。有些人在三十岁时,心灵深处就沉淀下厚实的记忆;有的人活到了七八十岁,记忆依然像戈壁滩上的青草那样稀少。前者可能有过销魂荡魄的爱,有过撕心裂肺的痛,而后者很可能是平平淡淡、庸庸碌碌度过了一生。
记忆像热带雨林那样茂盛的人是幸福的。他的一生,也许抵得过几个人的一生;也就是说,他活了一辈子,等于活了几辈子。人最大的不幸是失忆。一个人失去了所有的记忆,等于失去了生命。当然,当他找回记忆的时候,也就等于找回了生命。
死亡
死亡,就是我们全都
站立在其中的一丛灌木。
——布罗茨基:《丘陵》
这是出生于俄罗斯的伟大诗人布罗茨基一首长篇抒情诗《丘陵》中的诗句。死亡,是单调、空茫的平原上那一丛黑魁越魁越的灌木,我们每一个人都置身其中,绝无例外。人的存在是短促的、变幻的、虚弱的,那一丛灌木的存在却是永恒的、强大的、不可战胜的。但死亡并不是存在的敌人,它是存在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存在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没有死亡,存在就变得非常可疑,我们感觉不到死亡,也就感觉不到存在。存在因为死亡而凸显它的意义,人类因为对死亡的恐惧才更热爱生命,更珍惜生命。没有死亡,生命的冗长、乏味、沉闷将会使喜新厌旧的人类感到忍无可忍。
但死亡必须有它自然而然的节奏,那是上帝赐予的一种和谐的节奏,一种美的节奏。如果谁破坏了这节奏,那就是灾难。人类的平均寿命如果太短,短到几个月、几年,就无法创造伟大的文明;人类的平均寿命如果太长,长到几千年、几万年,整个地球就会因为耗尽资源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坟墓。
人死后到底会留下什么?人的鲜血在死亡之后几分钟就凝固了、黯淡了。土葬后人的皮肤、肌肉和内脏在短期内就会腐化,人的头发和骨头在几十年后也不会留存。现代人的火葬,一缕烟袅袅上升之后,眨眼间就只剩下一撮灰——难道除了这撮灰,就什么都没有了?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尽管对灵魂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相信人死后还有一个灵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有极大的差异,但有一点却惊人地相似:相信坏人死后会被打入地狱,好人死后必上天堂。我们在怀念一些死去的好人或者死去的亲朋好友时总是说他的在天之灵会怎么的。即使我们从理性上知道人死后除了那一撮灰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我们还是顽固地希望有灵魂存在。苍天浩瀚无际,再多的灵魂也会有飞翔的空间吧!
相信灵魂的存在,会使我们对死亡怀抱几分超然的心态,从而对生命的法则也多几分敬畏和虔诚。一个过分怕死或者全然不把生命当一回事的人都是可怕的,因为这样的人会置任何生命的法则于不顾,会把人类的任何理想、信念、美德无情地踩在脚下。这样的人一旦具有某种能量,就会在他的能量所及的范围内,把某些人的生和死,把一个民族的生和死,甚至把整个人类的生和死当成一场无足轻重、随心所欲的游戏。
我们每一个人到底离死亡有多远?其实,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开始了走向死亡的旅程,愈到后来,行进的速度愈快。布罗茨基在一首题为《一九七二年》的诗中写道:
衰老!躯体中越来越多死亡。
就是说,无用的生命越来越多。
无用的生命越来越多,但只要完整的死亡尚未降临,躯体中毕竟还有好多好多有用的生命啊!死亡每时每刻都是一把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我们无法预测它究竟会在什么时候落下来,“嚓”的一声结束我们的生命。在这“嚓”的一声响起之前,我们赶紧生活吧,赶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不妨每一天都想象这“嚓”的一声会在当天深夜响起,今天是此生最后一天,赶快行动吧,去喝一杯自己最想喝的咖啡,去读一首最喜欢的诗,去帮助一个早就想帮助的人,去对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说出最想说的话……
当“嚓”的一声来临时,我们自己是听不到的,我们的亲友听到后就会说:他是在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时离开人世的,他是在幸福和欢悦中离开人世的……只有这样,死亡才是美的,才是优雅的,才是了无遗憾的,才是摆脱了恐惧和困惑的。它是生命的高潮,而不是生命的终结。
至于死亡是热闹的还是冷清的,是荣耀的还是平淡的,是一缕略带凉意的微风拂过亲朋好友的脸颊,还是像一颗巨大的陨星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这是我们不需要考虑更不必苦心竭力去策划的。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潇洒地走了——之所以潇洒,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生前是一个好人,我们的灵魂是能够上天堂的。
我想起普希金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和爱情结伴,慵懒地度过欢快的一生,/他没做过什么善事,然而凭良心起誓,/谢天谢地,他却是一个好人。”“谢天谢地,他却是一个好人”——愿我们的灵魂在离开自己的躯体时都能毫无愧色地说出这句话。
消逝
一切都在消逝:消逝的风,消逝的雨,消逝的童年,消逝的青春,消逝的笑声,消逝的爱情……渺小的事物在消逝,伟大的事物也在消逝。脆弱的事物在消逝,坚硬的事物也在消逝。卑鄙的事物在消逝,崇高的事物也在消逝。
有些事物一经消逝便永不出现,比如一个人的童年、青春、光洁的额头、又黑又亮的头发……它们不是在一个早晨突然消逝的,而是在人们毫不察觉的情况下蹑手蹑脚地溜走的。等到人们有所察觉时,它们已无影无踪。有些事物消逝后还会再来,比如风和雨,比如春天,比如爱情。但实际上,重新回来的风和雨已不是往日的风和雨,重新回来的春天和爱情已是另一个春天,另一种爱情。所以哲学家说:人不可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
有些事物消逝得愈是长久,在人们的回忆中愈显得珍贵。比如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回忆一生的时候,很少回忆退休以后喝茶、打麻将、晨练这些眼前的事物,甚至不会太多地回忆中年时期的热闹和辉煌,他们在回忆的银幕上不厌其烦频频放映的镜头,常常是童年的顽皮和情窦初开时的羞涩。年代逝去得愈是遥远,这些镜头便愈是清晰,愈是意味隽永,愈是让人陶醉,同时让人心头隐隐作痛。
生命的消逝是否标志着一个人的彻底消逝呢?柏拉图的生命消逝了,李白和杜甫的生命消逝了,但丁的生命消逝了,文森特·梵高的生命消逝了,贝多芬的生命消逝了……但他们用伟大的思想、智慧和人格所创造的东西,并没有随着他们生命的消逝而消逝。他们活在人类的文化史上,也活在人类那些纯粹和高贵的灵魂中。只要人类存在,他们的光芒就不会消逝。以他们为代表的人类的爱和人类的创造精神,使“永恒”这个词具有了意义。但对于我们这些无法影响人类进程的普通人来说,生命的消逝,启动了我们彻底消逝的程序。我们的精神和物质可能会给自己的儿孙带来一些影响,但这些影响会很快消失,就像水消失在水中,沙消失在沙中。我们活着的人,有几个记得太祖父太祖母的名字?恐怕记得曾祖父曾祖母名字的人也寥寥无几。
不断消逝的事物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迷惘、虚无甚至是凄凉的感觉,但实际上,正是事物的这种短暂和易逝的性质,使许多事物凸现出它们的美好与珍贵。试想:如果柏拉图一直活着,每天向我们宣讲他关于灵魂马车、太阳和洞穴的学说,我们肯定早就厌烦了。假若我们那青涩的初恋不是稍纵即逝的话,我们会铭心刻骨地怀念吗?一段肝胆相照的情谊,一个欲仙欲死的吻,一次出生入死的经历,几幕电光石火般闪过的离别、重逢、狂欢、荣耀的画面……之所以成为我们终身难忘的回忆,成为我们一生的骄傲和欣慰,就是因为它们已经消逝,而且永远不可能重温旧梦。
北岛在一首诗中写道:“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北岛在年轻时就写出了这首苍凉然而睿智的诗(就凭这首诗,他就值得我献出毕生的敬意),这是一位有洞察力的诗人以诗歌的形式对“消逝”作出的哲学阐释,二十多年来我的灵魂踽踽独行在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朦胧诗消逝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喧哗和骚动消逝了,许多梦想消逝了,许多人消逝了,但仍然有无穷无尽的人和事物吸引着我们。我们在不断的消逝中走向迎接,我们又在不断的迎接中走向消逝。有消逝才有迎接,有迎接才有生命和世界的崭新气象。
我的黑发正在消逝,我的野心正在消逝,我写下的诗歌和情书正在消逝,我一切的秘密都在消逝……它们在消逝中凸显生命的神奇和美丽。呵,我知足了,我在万物的消逝中看见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