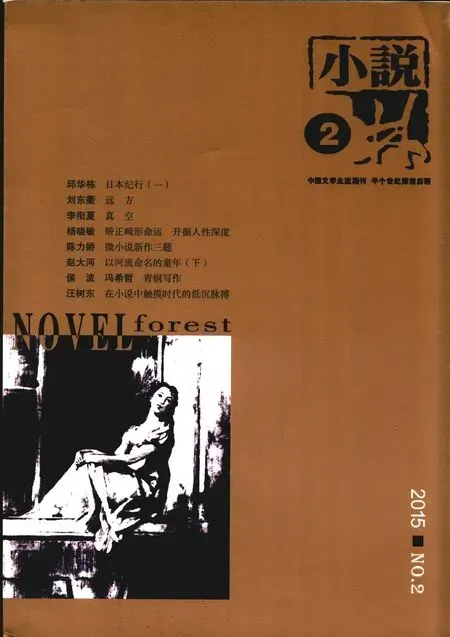青铜写作
——《延安文学》主编侯波访谈录
◎侯波 冯希哲
青铜写作
——《延安文学》主编侯波访谈录
◎侯波 冯希哲
核心语:我喜欢青铜,李贺有一首诗,“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我曾多年为此沉迷,后来刻了一方印章“铜之韵”。我希望个人的写作像青铜一样,在外表看似温润的光泽下有着硬邦邦的质地。一件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埋入地下上千年,今天发掘出来,是剑,我们仍能感受到它的锋芒;是鼎,我们依然能感知到当初士大夫的奢华。
——这就是青铜的本质,即使过上几千年,世事沧桑,岁月不再,但青铜依然是青铜,他当年铸造时的信息还是能够完整地给我们传达出来,散发着恒久的魅力。
侯波: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学员。1986年开始写作,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谁在那儿歌唱》《稍息立正》《太阳花开》《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和长篇小说《流火季》五部。代表作有《春季里那个百花香》《2012年冬天的爱情》。现为《延安文学》杂志主编。
冯希哲:1970年出生,陕西韩城人,现为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陕西当代文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陕西作家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享受“三秦人才”津贴专家,陕西省委理论讲师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同时从事文艺批评。
冯希哲:侯波,你好。你的系列中篇小说应该是近年来陕西文坛与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其贴近生活、朴素而真挚的现实主义书写,对文学理想的孜孜以求及其行姿,使人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深沉的敬意。请问,你是近年来才开始的文学创作么?
侯波:不是。我十六岁开始写小说,十八岁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处女作短篇小说《黄河之歌》发表在1986年第一期《当代》杂志上。算起来,从1986年到现在,我写作将近三十年了。我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我始终觉得不是任何题材都可以入小说的,所以对写什么心存戒意,对题材是非常挑拣的。我从1986年开始写作起,到现在一直没停过,每年都写几个中短篇。你说的近年来我的几个中篇小说在全国文坛有反响,但在我看来,这些小说与我先前的小说写作具有一种连续性与一贯性。也就是说,从开始写作的那一天,我的追求,我对小说的理解一直到现在几乎是一脉相承的,从来没有改变过。
冯希哲:从读你的《上访》开始,到《春天里那个百花香》《2012年冬天的爱情》《贵人相助》等这些优秀中篇小说,可以观察到你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文学信念,写一个是一个,写一个成一个,篇篇乡村气息浓郁,字字文心宛然。在我看来,如此接地气又富有高水准的艺术结构能力与叙事水平,置之于被功利裹挟的文学创作大气候而言,似乎格格不入的,但这正是真文学的真谛所在,是真作家的使命意识使然。
侯波:你说的非常对。我在上文中说到我对小说的理解,对从事作家行业的理解一直没变过。我认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最根本的要直面生活,直面时代,要有担当意识,要有社会责任感。我这些观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陈旧的,但我从写作那一天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也是一直这样坚持的。否则的话,作家这个行业就与娱乐明星没什么两样,就没有存在的特殊必要性了。我当初开始写小说时,读的多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到现在我依然爱读这些作品,尤其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的所有作品我读了再读,前年在北京上学,我还专门把他几本代表作又重新读了一篇。我写作上秉持的是现实主义写作,并且我一直认为,现实主义在中国远没有过时。现实主义,在我认为就是冷静客观地观察社会,贴近现实,陈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我很喜欢这种小说创作理念,它展示的是与社会现实平行发展的另一种现实,是一种可与我们自己生活互为真实性的存在。它面向普通百姓,书写普通生活,甚至深度介入普通生活,它关注的是弱势群体,是一种有态度的有情怀的文字,是一种有鲜明的作家倾向与价值判断的文字。我一直认为,小说就是大众化的,面向大众的,他不应该只满足于文人雅士的一种欣赏、消遣,或者只是纯粹小众的一种审美作品。但现实主义又不是为生活唱高调,唱赞美诗,它是具有批判性的,它对现世社会秉持着不合作、不苟同的态度,既是近距离的,又是明显疏离着的,它怀有慈悲,同时又有情怀,它的价值取向清晰明了,无奈感也异常沉重。
所以,在写作上,我更注重的内容是什么,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对形式上的创新比较轻视。这种看法可能在一些新派作家眼里落伍了,但我是不赞成那种为了创新而追求形式上创新的做法,小说的内容与形式说到底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一切的形式都是为主题服务的,没有了主题,要形式有什么用呢?今年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当代》主编周昌义说过一句话,最漂亮的女人是不穿衣服的女人,我觉得这话非常对。
另外,我认为真实性是作品的生命力。对于作家尤其是小说家而言,远离生活本身而生发的对生活的虚假想象,不仅脱离生活本身,失去生活的鲜活性和真实性,也使文本矫情而虚伪,经不起推敲。真实性永远是衡量小说文本长短的最后底线。一旦失去真实性,再细腻的描述都是海市蜃楼,都是对文学的伤害。在我自己的小说里,我一直追求烟火气息,跃动着鸟鸣与炊烟,有着当代农民的心跳与呼吸,不仅如此,对现存的矛盾不回避、不遮掩、不教条,真实而客观地呈现社会转型期乡村世界的喧哗与骚动,反映底层干部与群众的困惑、焦虑与阵痛,我认为这些才真正是立足民生的为人民写作。
冯希哲:你的小说写得根深叶茂,读者读后,原汁原味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体现出了一位优秀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把握能力。看得出,你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作家,对人世心存善意,作品中你所塑造的那些人物,一个个都似乎是你的亲人邻里,一路信笔拈来,为他们画像,为时代立此存照。请问,你的小说原型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吗?
侯波:写现实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这是我一贯的文学观点。我小说中所写的生活场景、具体人物其实都和我的生活密切相关。1986年,师范毕业后,我一直在一个离城很远的小乡镇工作,当过教师、文化馆员等。当年,我还在村子里承包了几亩土地,栽上了果树,利用星期六与星期天和妻子一起下地劳动。由于个人的生活经历,所以我对陕北农村的生活非常熟悉,对小乡镇生活非常熟悉,对农村这么多年来的变迁与农民的心理发展历程非常熟悉。在写小说时,我写着写着,人物的形象就活起来了,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眼前了。这是写作的基本方面,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主观方面,在写作时,我认为一个作家必须对自己所写的人物投入感情,就像谈恋爱一样,你如果从心底里喜欢对方,那么,你在他或她身边的一言一笑,举止动作就会和别人不一样,对方也就能感受得到你这份真心。
中国有句俗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一个作家自己都不喜欢你塑造出来的角色,对人物没有情感,仿佛陌路,那么如何让别人喜欢,如何能打动别人,如何能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呢?
举例说吧,《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这篇小说中有个女主人公叫红鞋,这个角色写出来以后受到许多人的好评,大家都觉得这个人物是有生命力的。而这个人物恰恰来自于我的生活,我认识这个人,那年她要排秧歌时,她找的我,我给请的老师。我和她接触,发现她是个有能力、有个人想法与追求,对生活充满爱心的人,也很有号召力。但并不是说小说中的所有事情都是她的生活经历,只是说,通过对她的观察与了解,我觉得把她的性格吃透了,写作时,她就自然而然地跳入到我小说中了,在我的小说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我们读一篇小说时,有时会有一种陌生感,读完以后,这种陌生感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比较深。但陌生感并不是说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而往往是作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一些被我们自己忽略或者未曾注意到的细节。增强这种陌生感就要求作家要写出自己对事物的独特感受,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悟。我的创作素材都来源于我的生活经历,如《春季里那个百花香》中写到“传播邪教”“正月排秧歌”“村民赌博”等,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或者耳闻目睹的事,因而写起来得心应手,充满了激情。自己写得顺手,读者读时就会非常流畅。常常有读者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说他一口气就看完了我的小说,说他看得舍不得放下,上厕所看,做饭时、吃饭时也看,就是这个道理。我写小说,具体细节都来自于个人生活体验。一篇小说的创作从头到尾好像登一座山坡,目的地在最高处,到达目的地就必须先要登一个个台阶,这些台阶都是实实在在的,需要你一步一步往上攀。只有通过大量的独到的细节铺垫起来,大家才会相信大故事的真实性,才会感受到你在顶端要传达的那些想法。胡编滥造的小说,读者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是没有力量感的,你骗不了读者,甚至也骗不了你自己。
冯希哲:陕西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文学重镇,先是有柳青、王汶石等著名作家开启了当代陕西乡土文学叙事的先河,以其直面新现实,歌吟新生活的独特追求,为陕西当代文学铸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也为中国当代文学添加了浓重的陕西元素。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因陈忠实、贾平凹、路遥、邹志安等人的承继与创新,陕西的这种乡土叙事不仅重新得到接续,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这样一个重要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代际断裂,明显青黄不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你的小说出现了,以其率性地直面乡土现实,浓烈的现实主义气息,让人们看到了陕西乡土文学叙事传统在新一代作家身上的生根发芽。比如,在你的小说中,目前农村裂变的当下现状,乡土异动的种种实情,几乎都做了顺藤摸瓜式的跟踪与细针密线式的反映,对农村基层运行系统和民生精神困境进行了密切观照,完全可以说是你的小说是当下“农村精神困惑及其抉择艰难的文学镜像”。我认为,你的小说创作,是陕西乡土文学叙事传统在当下时代的新的复活。
侯波:冯教授,你的认识非常深刻。不过,我觉得不能因我写了几篇关于农村的小说就归到乡土作家行列。我个人认为我关注的不是某一块地方,或者某些具体的人,而关注的是我们这个大时代当下所有人的精神世界。你说的小说反映乡土这一块,反映农村人的精神世界,这些也只是我关注的一部分而已。另外像我其他一些中篇,比如《婚内婚外》《猜火车》《流火季》等等,显然不是写农村的,而是写小城市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这些作品只是没有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而已。关注当下人的精神走向,这是一个大概念,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我也会一直关注下去。
之所以大家对我有乡土作家的印象,可能是以为我写乡土题材的多一些,我对这一块更熟悉一些。我老家在农村,现在村子人都富起来了,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盖了新房,买了车,但伴随这种物质条件改善而来的是他们整天在干些什么呢?男人有钱了就赌博、勾引良家妇女、吸毒等等,女人打麻将、信耶稣,甚至信邪教的,人人生活得很空虚、无聊。精神很迷茫,道德滑坡,文明丧失,人们除了追求物质感官刺激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下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不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的一个部分,我没进行过仔细研究,但这个现象我想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如果长此发展下去,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是一种灾难。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作家,不关注这些我们还关注什么呢?
2012年,我的中篇小说《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被《小说选刊》头题转载了,在给《小说选刊》写创作谈时,我提到了“院墙”这个概念,我认为原来的中华传统的一些文化道德观念就是一道院墙,我这样写道:“当工业文明铺天盖地来时,首当其冲的是传统乡村的文化秩序。这种秩序就像农村中家家户户的院墙,可能是土筑的石垒的砖砌的,尽管院墙不够坚固,不够高大,但有了这墙,家家晚上就能睡得安然,鼾声四起。曾几何时,院墙被撞塌了,于是围绕墙的建与不建、什么方式建、用什么样材质建就都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而院内人在旧墙已倒、新墙未立之时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他们缺乏安全感,焦虑不安,甚至有几分迷茫,无可适从。”我的《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肉烂都在锅里》《贵人相助》,甚至包括《2012年冬天的爱情》正是写出人们的这种无可适从感与迷茫感的。
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作家,不,所有的新时期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探讨这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重建乡村或城市文化伦理道德,为我们的民族重新筑起一道院墙来。
另外,我虽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乡土作家,但还是想对乡土写作说几句话。新时期以来,写作,尤其是乡土写作,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尽管充斥着我们视野的是大量的乡村题材,然而真正触摸到农民命运本质,以及乡村发展现实的作品还是太少了。许多作品只停留在表面的恩怨悲欢,很难触及到乡村世界的内核。新世纪以来,农村问题伴随着社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失调,伦理道德失序,日益严峻。作为有担当的作家,这些深层次的矛盾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应该用我们的作品进行思考的。作为当下恶劣的精神活动的一种抵抗、补充和矫正。我们如今的社会,精神虽然遭受到伤害、困境,但还没有到崩溃和绝望的地步,我们灵魂虽然迷失、变态,但还没有到撕裂和疯狂的地步。我们社会的富人越来越多,穷人越来越少,这更加凸显了穷人的悲哀和我们对贫穷与底层的忽略。何况,穷人在如今依然是一个庞大的、触目惊心的群体。我认为,怜悯仍然是作家的美德之一。在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轻佻,越来越浮华,越来越麻痹,越来越虚伪,越来越忍耐,越来越不以为然,越来越矫揉造作,越来越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某一部分平衡我们时代精神走向的责任,并且努力弥合和修复我们社会的裂痕,唤醒我们的良知和同情心。
冯希哲:你说的我完全同意,作家就应该直面人生,直面社会。你的小说的确在关注着乡土中国社会的秩序重建,有一种文化反思的精神向度和哲学思考。从风格上来讲,我注意到了,你在承继陕西传统经典性元素的乡土叙事小说以外,你小说艺术上呈现的总体特点是,结构以审美传统为基,注重故事性的叙述,情节经常出现“黑色幽默”式的成功穿插,在启动故事本身的内在意蕴驱动之时,辅以明快的节奏和淳朴的文风,使文学表达的张力得以增强。正像一个评论家评论的,小说写得轻松自如,貌似黑色幽默,但读来令人悲凉,发人愤怒。
侯波:一个人的写作风格不仅和他的修养与学识与个性有关,还和地域文化相关,你说我小说写的轻松,我觉得主要来自于我个人的性格。我在生活中是随遇而安的一个人,老想活得轻松些,爱调侃,爱开玩笑。所以,小说中一般不写沉重的事件,即使事件是沉重的,我在处理时,也要做到轻轻松松。之所以给大家感觉到“悲凉与愤怒”,我觉得主要来自于地域文化和我自己对小说的认识,你可以看一下,陕西的几个大家,路遥、陈忠实、老贾的作品都是这样的,追求作品的厚重感,有沉甸甸的分量。尤其是《白鹿原》与《平凡的世界》,这种表现就更突出。什么地里长什么树,什么树上开什么花,我在追求厚重感这一方面和陕西的这些作家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和文化底蕴有密切的关系。
在此,我尤其想提一下,我的老乡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是他的学生,我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足可以与国外的《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相媲美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质朴而又充满了魅力,无疑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小说,截至目前,它的巨大价值及意义还远远没有发掘出来。
如何使作品具有厚重感?我认为最主要的要在小说中渗透作家的思想。写小说要有故事,但故事充其量只是个载体,就像一辆架子车,车是什么样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车上拉的那些东西。拉的是什么呢?就是作家的思想,我觉得一个作家与哲学家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作家不过是把自己的思想幻化成具体的形象而已,说来说去,都是在传达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伟大的作家都是站在思想前沿的,也都是思想家。路遥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用《人生》《平凡的世界》来探讨一代农村有才华的青年出路何在。《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最后从城市又回到了农村,他没有找到出路。说明了这不是高加林个人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制度出了问题。好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平台,是能够充分让每个人发掘自己潜力的。这个小说当时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鸣与轰动,它也预示着这个社会必须变革,如果不变革,就会埋没人才,许多优秀的青年在这个社会里都没有出路,就会制约社会的发展。莫言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就是有他自己独特思考的,他的代表作《蛙》其实在写计生工作在某些程度上是对人性的一种践踏。在大家都认为一些事物合情合理的时候,他提出了质疑。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发现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所在。而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利用一个农民思想家的眼光来看历史,于是就有了“翻鏊子”一说。这些作家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与思想,也就是我通常说的,思想的深度决定作品的高度。要立志成为一名作家,首先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前几天,在一个研讨会上,我提出了“青铜写作”的概念。我说,我喜欢青铜,李贺有一首诗,“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我曾多年为此沉迷,后来刻了一方印章“铜之韵”。我希望个人的写作像青铜一样,在外表看似温润的光泽下有一种硬邦邦的质地。一件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埋入地下上千年,今天发掘出来,是剑,我们仍能感受到它的锋芒,是鼎,我们依然能感知到士大夫的奢华。
这就是青铜的本质,即使过上千年万年,世事沧桑,岁月不再,但青铜依然是青铜,他当年铸造时的信息还是能够完整地给我们传达出来,散发着不朽的魅力。但怎样让其成为青铜呢,就是要融入个人的思想。
冯希哲:我近期读了你的《春季里那个百花香》《2012年冬天的爱情》,我认为这两篇小说都不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经典性的中篇小说,能谈谈这两个中篇的创作过程吗?
侯波:《春季里那个百花香》,是我在老家过年时,有三件事情触动了我。一是我的一个本家,病得非常重,都不能出门了,但在过年之夜,却参与赌博去了。好笑的是他根本没力气走到赌场去,他就让自己儿子用三轮将自己拉到了赌博场。另一个是大年三十晚,我家里突然撞进来几个女人,她们言说是来送“福”的,但要我们跟着她们举行一个仪式,我们当时就拒绝了。但在第二天我了解到,她们是来传播邪教的,许多人都被蒙蔽了,都跟着她们举行了仪式,信了她们的神,然后她们送他们七粒米吃,说吃了后神可以保证来年全年无灾。第三个感触就是正月里村里闹秧歌,你村里到我村里,我村里到你们村。但这些秧歌组织都是每个村的基督教组织的。这三件事引发了我一些思考,然后我就写了《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这个中篇小说。小说发表后,被转载了许多次,后来收入到各种年选本,年度小说排行榜也收了,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声誉。大家都认为,经济发展与文化的不成比例,物质与精神的极大反差,正是当下农村最为真切也更为严峻的现实图景。
《2012年冬天的爱情》,是2014年才发表的一篇小说,后来也被《中篇小说选刊》与《作品与争鸣》转载了。这篇小说的素材也来源于我的生活。有一次我回到小县城,几位朋友请喝酒,结果有一个朋友没来,没来的原因正是他那一段时间每晚都要悄悄地监视上访人,怕他们偷偷离开村里到北京去上访。当时听了这件事,我心里有所触动,后来就写了这个中篇。但在怎么把握这个题材上个人考虑了很长时间,后来构思时,把大学生村官加了进去,把我关于农村人的精神走向这个话题的探讨加了进去。一对青年男女村官,监视有可能上访的老钟夫妇俩,他们尽管没打算去上访,但在监视者的眼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似乎要上访,最后弄出了一场啼笑皆非的笑话。整个事件尽管是“乌龙”,但两个年轻男女倒因为这场监视成就了一份爱情,小说颇具有一份黑色幽默的特质。
冯希哲:是的,我认为《2012年冬天的爱情》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在深刻的隐喻性穿透后,艺术结构与叙述臻于美善,具有经典意义。老钟夫妇多次上访但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他们对现实失望了,转而信仰基督教,这恰好与《百花香》有一脉相承之处,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乡村传统价值伦理沦陷,人们精神空虚之际集体意识上的迷茫和空虚。基督教让老钟夫妇放弃了上访,帮小董完成了“政治任务”,还救了小董一命。老钟夫妻在生活中无奈的现实面前寻找不到精神寄托,由于意识的自我救赎需求,促使他们自发地在宗教里感遇知音,良善没有改变,只是他们对现实的看法逆转了。因此,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中国社会历史本来最稳固的民间心理结构之所以在嬗变中走向虚妄,其诱因不只是精神沦陷这个维度,复杂的原因集中在整个社会秩序失范状态,尤其是现实所提供的合理正常的价值系统坍塌,最终使社会心理结构发生深度变异,从而使这篇小说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应该说这是一篇可遇不可求的经典性小说。
侯波:在今年九月份的小说研讨会上,李星老师、周昌义老师也这么说。
冯希哲:还有一个问题,你现在是《延安文学》主编,作为纯文学杂志的主编,你对杂志的风格与追求有些什么想法?
侯波:我们当然和其他纯文学杂志一样,希望能发好小说,好散文,好随笔,借助《延安文学》这个平台推出更多的作家。但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每个人的认知却是不一样的。通过刚才的谈话,你可能了解了我对小说的认识与追求了。我现在是《延安文学》杂志主编,我们杂志所发的小说也只能是我个人认为的好小说。一是要有可读性,小说是大众化的,要让大家能够读下去是第一位的。可读性就是故事性,但小说又不仅仅是故事,要在故事中塑造人物,要让人物立起来,传达自己的思想、看法等等。二要接地气,有生活气息,故事及人物心理要经得起推敲,要有生活逻辑性,写自己实实在在的生活,写自己独到的发现。三是要有暖意,就是俗话说的要有正能量,而不是挖空心思地编造故事来反映所谓的人性善恶。
有探索性的先锋小说我们也发,但只是参考性的,不是我们杂志的主流。我们杂志更多发的还是具有现实性、批判性的,关注弱势群体的,有自己独到思考的小说作品。
冯希哲:对了,还有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已有自己风格的成熟的作家对青年写作者有什么好的建议。
侯波:说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来,我认为写作这东西没什么诀窍,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顿悟以及写作的经验别人很难用得上。要我说,写作最需要的是个人多读、多写,在多读多写中自然而然就琢磨出来了,就提高了写作水平。在读书上,我倒觉得与其博采众长,不如狂热地读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作家的作品,多读几遍,写作就自然而然琢磨出头头道道了。
至于写作,鲁迅说得非常好,“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不卖弄,”写小说就要绝不故弄玄虚,绝不哗众取宠,也绝不油腔滑调,更不伪饰媚俗,自己写自己的,不要想着走捷径,读者是非常聪明的,你耍弄点什么小聪明读者一下子就能感受得到的。
写作需要想象力,但更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生活,用自己的眼睛,独具慧眼地从自己生活中发现别人未发现的东西。
写作就像一棵苹果树,要想结出色泽鲜艳、圆润饱满的果子来,就先得把根扎进泥土里,这是一句俗话,当然也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大道理。
冯希哲:还有一个问题,你的作品中有一些方言,你不觉得方言的运用有过时之嫌吗?会不会阻碍读者的阅读兴趣?
侯波:许多读者也反映这个问题。但我有时用普通话没法准确地把我的感觉写出来。同样的动作与语言用普通话表现觉得缺少一种表现力,缺少一种韵味,比如说,我们本地方言中关于“水”的形态就有十多种词汇,但普通话中没有这么多词汇,或者说至少是我不掌握普通话中的这么多词汇,所以在写作时就只能用部分方言来写,为的是准确地把我的感受传达给读者。
冯希哲:我注意到了你关于写作的一些说法,“作家凭的是个人的思想深度、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感悟能力”,“写小说如同养娃娃,好娃娃需要的是好种子,好土地,漫长的孕育过程。”如此接地气、有底气的认识,使你能够始终把写作之根深扎在乡土的泥壤中,汲取着最为鲜活的生活的养分。根深必然叶茂,叶茂源于根深。因而,你的植根于生活深处的小说写作,总会开出新花,总能结出硕果,也是我们完全可以期待的,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认为你目前的小说有什么缺陷与不足?
侯波: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不足,但自己很可能难以发现自己的缺点。就像一个人,个性成熟以后,他个人认为自己所做的事都是有道理的,但这个道理符合不符合大家的共识,与其他传统观念冲突不冲突,有时往往是自己发现不了的。
冯希哲:我是一个评论家,说话素来不留情面,当然我非常肯定你的小说与追求,但同时,我觉得你尚有三个问题需要自我反刍:
一是历史观问题。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必须具备清醒而前瞻的历史观。历史观是灯塔,可以照亮作家在丛林中的行走路线,以俯视和反观的姿态对待历史和当下诸多问题。模糊或者缺失的历史观,只能匍匐在素材里难以自觉,最终损伤文学精神的高度和穿透力。其二是价值取向问题。你的小说艺术上成熟有个标志性的地方就在于能将创作主体隐藏起来,而不是跳在前台。但同时我也注意到你对人与事件叙述过程作为创作应持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很明晰,这样对文本的精神指向无形中造成了一定的削弱。第三是艺术风格问题。虽然你的小说语言叙述很纯朴自然,有质感,但有时我觉得少了汉语本身的飞扬感和飘逸感,也因此有损于语言表达功能的整体美感。
侯波:谢谢你的意见。你有你的看法,我也有我的道理,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敢于直言的人,就是朋友,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我也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