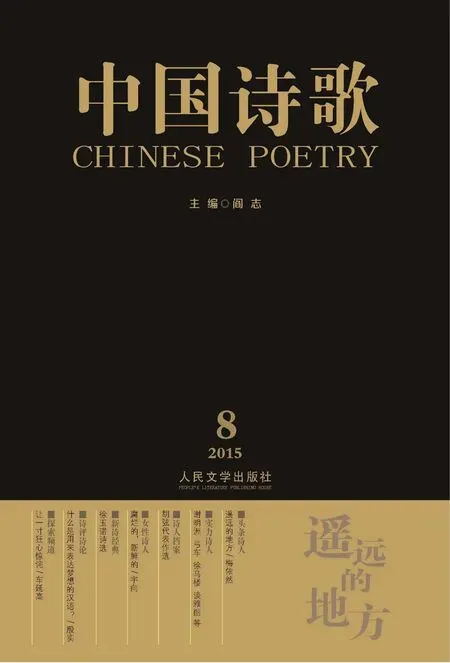徐马楼的诗
徐马楼的诗
童年便纷至沓来
苍凉
我知道有一天我
可以肋生双翅战胜众神
与梅花一起育春天
我相信到秋天
故乡所有高粱衣冠整齐
饱蘸大地最后一缕鲜红
看日月交替
我明白风停驻之后
部首与偏旁散落华北华南
河流应运而生
像嘹亮的马鞭呼号驱赶
众生毕至
我知道
小院烟火
残破的红砖小院
反锁的旧时光
母亲辫梳的玉米串倒悬檐下
深嵌时间的生锈铁钩坚韧而温暖
陈年的记忆摇晃秋末的夕阳
一把锁据守住光阴
腐烂的门内是我隐秘的庄园
暗语,藏在书房角落的灰尘里
用温度适中的语气,轻嘘
一墙之外,烟熏的厨房,
是病情加重的口吃患者
吞食芜杂柴火后
冰冷的灶台重吐生硬的火焰
铁锁囚不住,小院升腾的烟火
与秋尽处的烟雾交媾、混合
逃脱迷离的人世间
不在自己村庄里忧伤
1
时光就蹲在那块粗石板上
阳光一走远便起来数青苔
而茅草早早骑上屋檐
试图解开瓦楞与星星间的方程式
平行的不远处是我最初演习汉字的老学校
加号从那间破教室写到现在
我仍没算出生活这道数学题
2
乌鸦的灰翅膀错过了多少好日子
我祖先坟前盗土的真凶另有其人
直到头发灰白我才幡然醒悟:
村庄内外这些黑得不怀好意的家伙,
一直忙于盗走黎明前的黑,以及
夕阳西下前的白
否则,它们怎能躲过时间追捕鲜活依旧?
3
时间正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深渊
我沿着村西那条路进村时发现的
曾经是怀疑驱使我出走
以为带足了粮食和文字
现在又是怀疑驱使我回来
两手却空着
计算离村后一路迷失的时光
4
说不清池塘涸于何年何月
群鱼盗窃村妇梳子一案扑朔迷离
塘边垂柳就栽在梦的边沿
一次次帮我打开村庄的入口
再没有温暖的淤泥值得回味
尽管我的脚一直沉陷在异乡泥沼里
5
我曾在秋后把羊群赶上避水台
枯草萎靡泥土松软源于季节恩赐
各家晾晒的谷物、红薯干大同小异
却边界清晰,像针脚凌乱的鳞甲
我看到风与云正从空中往南方逃遁
常担心披着如此盔甲的避水台
能否抵御今年寒冬的进犯
6
所有企图进出村庄的水
均需挖空涵洞长长的心思
我趁洪流拍马远去的旱季摸进去
盗走由蟾蜍及乱蛇看护的伙头鱼
发现它围困着大批乌黑的时间和悬浮声响
它自此展开报复
把我成年前的梦境反复拖入淤泥
把已被时间遗忘的祖奶奶也带离人间
(祖奶奶被积攒了九十六年的心事缠乱
她来自山西先天缺水的某地
自杀前,她清楚村里机井被填埋后
涵洞是惟一有水且致命的地方)
7
狂风在回收用旧的树叶
最后的绿退隐村后
路边的黄叶像害怕什么却无处躲藏
麦苗试图粉饰日渐萧索的初冬
时间把曾丰盛的村庄伪装为萧索
太阳开始歪歪斜斜靠在天边
扶正它要等一个名叫春天的村民赶来
8
那些从郊外回村的人
试图用锄头带回什么人的记忆
他们自知什么都无法带回
连同那些不识路途的风
整个八月都星光黯淡
可我
不愿意在自己村庄里充满忧伤
坟下——送外公
他选择与一棵树为邻
旁边撒些不知名的草
左侧是秋天将尽时的晚霞
右面是妈妈鼻孔里滴出的眼泪
我知道我们都将如此
只是能带走多少人或者是什么人的眼泪
这就是区别,也是目的?
他一直顽强,健硕
留下了六个儿女
仅以失去三根手指的代价
他用剩余的七根在旭日东侧
与一行茅草结为兄弟
与羊群骡马同行
细数每一棵火红的高粱
我知道从村口往西数三万多步
还有一个世界
那里也有我们没有眼泪
二舅的拖拉机
二舅是出了名的硬骨头
凭锄头与螺丝刀的交互作用,将
三分之二的子女送进大学校门
最危险的是岁月不是空中作业
年老的二舅被逐出工地
他迎着骄阳重拾锄头
却被尊严与开销挤入墙角
二舅婉拒名目繁多的援手
花光积蓄从城里买回辆拖拉机
二舅的拖拉机精确驶入农闲的缝隙
穿越田垄断行处的公路与村庄
巧妙地躲避鲁豫交界的盘查与刁难
辗碎东明黄河大桥上的露珠与乱风
满载六千八百块山东泥土化身的红砖
嵌入河南新建的墙基里,二舅
每次获利三百三十六元
硬骨头的二舅把砖钳舞成弓箭
他敲碎疲惫,踩低油门
躲开晨雾与暗夜的纠缠
将餐桌简化成骨瘦如柴的方向盘
省略了无名指被红砖夹断的疼痛
对姥姥与二妗心疼的泪水视而不见
仰天笑笑将我们的劝阻一笔带过
二舅几近疯狂地装卸,也许他在梦里
拖拉机已载他无限接近昔日荣光
清明节前的麦苗没鸦,田畴湿滑
二舅和拖拉机都没出门
他终于在丰盛的餐桌前安坐下来
用完好的左手生硬地夹菜
另一只手刻意下潜
我端起满溢的泪水和白酒
二舅笑着说:拖拉机春后就卖,
上面要搞新农村建设,没人再买砖翻盖旧房。
说完,他的泪水抢先一步滚落酒杯中
一个人的对峙
我们约好这泡茶味淡时就道别
茶室躲在芜杂的城市深处
有株绿萝不知深浅地寄身墙角
禁不禁忌的话题均有涉及
只是结论没比上次明晰
我们互相揶揄处世方式
质疑对方信仰不稳的逻辑与动机
交换遮羞布一样的爱情观念
找许多形而上的棍棒支护鼓胀的物欲
深陷政治沼泽折断了方向感
我们眼看走向差距过大的控辩立场
急忙迫不及待地道别
不锈钢水壶的口哨兀自空响
哄沸的水一次次栽倒在自己嘴里
服务员尾随呼叫器赶来
账单已算清楚:绿萝忽略不计
茶室里始终独我一人怔怔地
望向两只茶杯的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