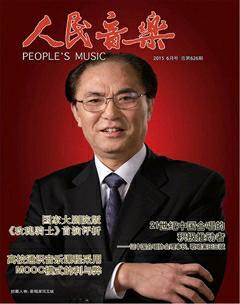《声无哀乐论》:一个音乐哲学咨询文本
一、引论:基本材料与研究方法
三国时期音乐思想家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可堪称一部音乐哲学,作品不仅是对先秦儒家音乐伦理哲学倚重“礼制”偏向的作首次批判,还开创“自问自答”式音乐哲学咨询先例。在“清谈”视野上,作品努力建构出中国古代音乐哲学的“思想分析”方法论及“知识生产”模式。
那么,何谓“咨询”?在语义层面,《尔雅》曰:“咨,谋也。”《左传》又曰:“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1}《晋书·孝友》载西晋名士刘殷告诫子孙曰:“宜上思召公咨询之义,下念鲍勋触鳞之诛也。”{2}说明“咨询”主要是指服事君主的谋略性与服务性之活动,并注重“对话”的技巧与方法,后逐渐成为一种国家备顾问(参谋)的幕僚“言官”对话活动,并延伸至社会诸领域的咨询活动。在中西文明中,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倚重咨询。《尚书》中早有“询事考言”(《尧典》)与“询于四岳”(《舜典》){3}的记载,尧舜之“询”或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咨询活动。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则是希腊口头传统最有力的见证,先秦《诗经》与《论语》就是中国口头对话传统的文本体现。在春秋时期,孔子的教育活动实则为思想咨询活动,即以对话为形式,旨在启迪学习者思想为宗旨的咨询活动。人类早期文明对咨询的敬畏反映出人们倚重口语的力量。{4}
在学术研究领域,诸如心理咨询、哲学咨询等已被纳入理论研究视野,尤其是“哲学咨询(Philosophical Counseling)”或“哲学咨商”,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实践哲学研究。毋庸置疑,尽管我们对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但从“对话”的视角整体揭示中国古代音乐哲学咨询的文字已然罕见。在以下讨论中,本文拟将以《声无哀乐论》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初步勾勒它的“音乐咨询”之理论特征、对话程式及口语力量,以期更多学者关注与研究被人遗忘的中国古代音乐咨询思想,深入获得音乐咨询的“知识生产”偏向与“思想分析”方法论。
二、《声无哀乐论》:“清谈”语境下的
音乐“知识生产”
在理论形态层面,中国古代哲学咨询是一种信息咨询,它有独特的对话程式、话语理论与哲学思想。譬如心理咨询(或心理咨询)如西汉枚乘《七发》中 “太子”(被诊断为心理疾病)与“吴客”(用“七件事”治疗)之间的主客对话程式;人生哲学咨询如孔子《论语》之对话式咨询活动;玄学咨询如魏晋时期名士的对话活动,他们主客之间的对话被称为“雅谈”或“魏晋清谈”。
“魏晋清谈”是魏晋时期一个较为复杂的哲学咨询形式。“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5}可见,“清谈”是魏晋玄士清议论辩之风,也是魏晋时期玄士对哲学(玄学)问题进行析理问难的咨询活动。魏晋社会“清谈”咨询哲学的兴起主要导源于魏晋社会政治的压力及其玄学的昌盛。士人为了自身的地位与理想,他们选择了适合政治“高压”的文艺活动——“玄谈”,这种文化选择的根源大致有三:一是随着大汉理想的破产,战争对人性的泯灭,人们对汉人的“大有”情怀开始怀疑。此时“三玄”思想成为填补他们生命空间的替代物。二是汉代大一统的国家政权砰然倒塌,士人的集体空间意识也因此转向以个性为诉求的审美需求。《世说新语》之《伤逝》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6}王戎之“情之所锺,正在我辈”就是魏晋士人个性自觉的写照,反映士人对偏重时间的玄学十分青睐。三是清谈玄学并非是对社会政治咨询的拒绝,而是随着权力争斗以及政治气氛的凝重,士人必须以忠于个体的哲学谈话形式标榜自己的社会理想与身份,否则连自己的生命可能也因此受到威胁。在“魏晋清谈”的语境中,作为“清谈”音乐哲学的咨询文本,嵇康是站在音乐哲学的立场反思属于他自己时代的文化。它的问世必然有其久远的学术渊源、深刻的历史背景及音乐艺术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律。
第一,在学术渊源上,《声无哀乐论》的“清谈”体例形式是西周以来“乡议”发展的产物。在口语系统发达的先秦社会,口头“对话”是文化与思想传播的主要形式,因此,“巷议”或“乡议”就成为古代知识传播或舆论监督的有效手段。“对话”作为一种咨询哲学对文学艺术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作为魏晋政权反对派的“名士”成为“清谈”的主体,他们以回归自然为态势而注老释儒,力主思想与个性的改革。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是正对《礼乐》之“乐政”一体与“乐心同源”而发难,指出“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的音乐哲学思想。
第二,在历史语境层面,《声无哀乐论》是先秦儒道思想遭遇社会转型的一个文本形态,抑或说,《声无哀乐论》是先秦儒道名教音乐思想在魏晋发生折变的一种玄学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清谈”与战国时期“公议”相比,前者具有“个性”特色,不具备公共性。嵇康《声无哀乐论》无疑是向儒家“公议”的音乐理论宣战,抑或说,嵇康围绕“声无哀乐”的个性自主立场阐释音乐艺术的自主性以及对艺术的超越性。竹林名士的这种思想“超越”,与其说源于他们对音乐之社会功能的思想,不如说导源于他们对魏晋动荡的社会及其政治压力的一种焦虑。
第三,在知识生产层面,《声无哀乐论》不仅传达出嵇康主体的自然性,还能透视出作者对先秦音乐哲学批判与革新的理论自信。嵇康“审贵贱而通物情”的音乐思想是对儒家国家立场上的音乐思想的质疑与反思,进而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音乐哲学理论。嵇康试图通过玄学,对传统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乐论的摧毁,无疑是对当时朝廷音乐哲学的政治宇宙持以否定态度。这样,先秦的音乐哲学思想被排挤在士人的社会宇宙之外。换言之,《声无哀乐论》不过是以音乐脱离政治而被纳入音乐形式本身,进而寻求“竹林清音”(即“个性独立”)的文本形式。
总之,包括嵇康在内的魏晋玄士常用哲学咨询的方式去思考当时的社会及其文化,玄士们看似远离社会,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思考与接近那个时代的文化。
三、《声无哀乐论》:哲学咨询的“思想分析”法
在“清谈”玄学影响下,作为音乐哲学咨询的《声无哀乐论》,它在方法论、对话模式及咨询艺术形式三个维度上建构出中国独特的音乐哲学“思想分析”形态。
首先,在方法论视角,《声无哀乐论》的音乐思想分析法以当时流行社会的音乐思想“结症”为对象,以“解惑”为研究旨向,为发展音乐哲学提供了一种中国式独特的“思想分析”法。在本质上,嵇康等竹林贤士的“思想分析”属于本体论哲学范畴。面对名教之乱,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学术主张或政治目标,实际上是嵇康无视音乐的社会调解作用,而试图建构“自然”的本体论。或者说,嵇康的音乐哲学思维方法论是试图从“自然观”来否定“名教观”,从而阐释自己的玄学“社会观”。它的进步意义在于“越”名教与“任”自然,而不是“反”名教与“返”自然。
其次,在对话模式上,《声无哀乐论》采用的是“自问自答”的主客“清谈”对话模式,这种“清谈”对话模式,又被称为“自为主客”。在文学修辞的视野里,“自为主客”,即“设问”;在汉赋体例视角,《声无哀乐论》有似于枚乘的《七发》制“七体”;在玄学对话模式下,《声无哀乐论》即是“清谈”的一种。在某种程度上,竹林名士选择“清谈”对话模式讨论音乐不仅是一种政治选择以回应玄士的学术身份与地位,还是一种学术选择以回应魏晋政治压力下的紧张与焦虑。
最后,在咨询艺术层面,《声无哀乐论》在八个回合 “主客问答”中显示高超的“对话”技巧与辩论艺术。在“清谈”结构上,《声无哀乐论》八个回合有“谈端”(与“应之”)、“发难”和“辩答”构成。第一回合由“秦客”首先“叙理”发起“谈端”,即秦客提出“清谈”主题,然后由“主人应之”提出殊解。后面第二回合至第八回合,均先由秦客“发难”,即客方“送难”,然后主人“辩答”,即主方“覆疏”,也就是主人举“谈证”进行多“七番”之“辩答”。
“秦客”在“谈端”部分首先提出传统音乐观念:一是“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该观点为传统儒家音乐思想,《礼记·乐记》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二是“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即孔子闻《韶》,提出韶乐之“尽美又尽善”的观点。《论语·八佾》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三是“季札听絃,知众国之风”,即季札出使鲁国听众国之音而知众国之风。很明显,传统儒家音乐哲学思想精髓为“声有哀乐”,该思想的核心体系是:“乐(治世之音或乱世之音或亡国之音)”—“心(安乐或怨怒或哀思)”—“政(治世或乱世或亡国)”的“三位一体”。这里涉及音乐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是音乐的本质问题;第二是音乐的功能问题。前一个问题的核心观点:“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即“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后一个问题的核心观点:“尽美,又尽善也。”也就是说,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它不仅具有道德的属性(“孔子闻《韶》”),还具有一定的审美认识功能(“季札听乐”)。对此,以下“答辩”,主方从“立场论”、“方法论”、“认识论”、“解释论”、“现象论”、“价值论”等多个层面进行咨询辩论。
层面之一:“立场论”。在第一回合中,“主人”首先批驳人们对经典音乐文化的顺从,导致历世“滥于名实”,这是一个对音乐文化的态度问题,即对音乐文化的“立场论”。“主人”指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
层面之二:“方法论”。在第二回合中,“秦客”发难,举“伯牙理琴”、“隶人击磬”、“鲁人晨哭”、“季子采诗观礼”、“仲尼叹韶音之一致”等“前言”以为“谈证”,进而说明“声有哀乐”。“主人”对此反驳指出:“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道。理已足,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耳。”在此,“主人”在“方法论”(“推类辨物”)视角上指出“秦客”之“发难”站不住脚。
层面之三:“认识论”。在第三回合中,“秦客”继续从“公论”出发发难,指出“夫观气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较然可见。故吾子不疑。”即,我们不能对“天下之通用”的“较然可见”的理论持怀疑态度,并说:“声音自当有哀乐,但暗者不能识之。”也就是说,声音有哀乐,只是“暗者”没有看到而已,这关涉到音乐理论的“认识论”问题。“主人”对此反驳道:“尔为听声音者不以寡众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为异。”说明“主人”对自己的观点“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持以“自信”。
层面之四:“解释论”。在第四回合中,“秦客”以“葛卢闻牛鸣”、“师旷吹律”、“羊舌母听闻儿啼”等“咸见录载”的“前言往记”,反问“若能明其所以,显其所由,设二论俱济,愿重闻之。”这实际上,给“主人”设置了“二论俱济”的“激问”。对此,“主人”从“解释论”视角对“前言往记”一一批驳,指出阐释传统有的阐释不清(即“前论略未详”),有的阐释有误(即“犹译传异言耳”,或“不为考声音而知其情”),有的阐释偏离于心(即“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有的阐释过于牵强(即“异域之言,不得强通”),有的阐释辞不达意(即“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这些“谈证”说明阐释学知识不足以可信,或引以为“证据”。
层面之五:“现象论(一):物证”。在第五回合中,“秦客”似乎被“主人”的“解释学”驳倒,于是,他从“史”为“证”的“众喻”中回到了“现象”之“实”,发难曰:“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也就说,不同的乐器会产生有差异的情感,相同的乐器用不同的曲调也会才产生不同的情感。“主人”对此反驳曰:“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因为,“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即音乐是以平和声音为体(或组织),而情感是一种应感而发的现象。换言之,这一回合“主人”批驳了“秦客”只见“现象”,而未见“本质”。
层面之六:“现象论(二):人证”。在第六回合中,“秦客”以“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之“定理”现象出发,发难“二情俱见”之“激问”。对此,“主人”以“一爝之火,虽未能温一室,不宜复增其寒”为例,进而指出:“火非隆寒之物,乐非增哀之具。”因为,“夫言哀者,或见机杖而泣,或睹舆服而悲。”换言之,触发悲哀的因素有多重,音乐只是一种而已,若“以偏概全”,断定音乐有哀乐则是错误的。
层面之七:“现象论(三):乐证”。在第七回合中,“秦客”以“齐楚之曲,以哀为体”为证,指出情感由哀与乐之分(即“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同理,“声音有哀乐”。对此,“主人”以“笑噱”之不显于声音,岂独齐楚之曲耶?”之问间接回答了“秦客”,认为并非只有齐楚之曲是“哀体”。
层面之八:“价值论”。在第八回合,“秦客”以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理,以问“移风易俗果以何物耶?”之难,并以“郑魏之音,击鸣球以协神人”为证,“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移易,奚由而济?”对此,“主人”辩答曰:“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先王用乐是为了“心安志固,从善日迁”,或“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这不过是先王治国之策,并非一定关乎哀乐之声。
《声无哀乐论》八个回合的“自为主客”辩论显示:“声无哀乐”。这个命题的核心观点直指:音乐是自然之音,它的自身不能产生哀与乐的情感。换言之,音乐之美在于形式之美(“声音和比”),而不具情感之内容,也不反映社会之风俗。不过,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嵇康将音乐的情感内容排挤于音乐本质之外,显然失之偏颇。
四、结语:《声无哀乐论》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清谈”是魏晋士人社交文化活动领域里的一种集体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清谈音乐哲学咨询文本,《声无哀乐论》透视魏晋士人独特的文艺活动及其独立自审的玄学风格,彰显出中国古代哲学咨询理论进入一个较高的理论层面,即“清谈”哲学咨询层面。同时,《声无哀乐论》式的“清谈”咨询哲学成为魏晋名士明哲保身的一种对话智慧,它不仅缓和了当时紧张的社会矛盾,还为玄士在高压政治空气中指明了出路。特别是嵇康反对人们对经典文化及其阐释的顺从,反对世人对理论本身的不自信,反对人们只见现象不见本质的“形而上学”以及夸大音乐对社会的作用,这些思想在魏晋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在音乐文艺层面,《声无哀乐论》的“清谈”哲学咨询注重言辞,倚重道德情操,并敢于褒贬社会黑暗与政治腐败,对魏晋文艺发展提供学术发展土壤与空气,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与引领魏晋文艺的发展与传播,使得魏晋文艺出现了一次小型的“复兴”,嵇康《声无哀乐论》等典范之作显示出魏晋文艺发展的繁荣景象。
在音乐传播层面,《声无哀乐论》式的“清谈”是一种“美谈”或“雅谈”,它对言语传播技巧与声韵之美有严格的规定,虽然它的方法是一种辨名析理的抽象方式,但是这种“善言谈,美音制”的音乐传播美学对于转型社会风尚与学术思想具有推动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清谈”具有传播意义上的积极历史贡献。
在音乐理论层面,从东周“巷论”到东汉“清议”(有时也称“乡议”),再发展至魏晋“清谈”,它是古代哲学咨询在理论上的一次较高层次的发展,尤其在对话修辞、咨询形式及其传播特质上对于当代我国音乐理论自信、民族音乐发展以及“微音乐”的文化传播理念等研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1}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2}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卷一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页。
{3} 冀昀主编《尚书》[M],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9—12页。
{4} [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5} 唐翼明《魏晋清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6} [南朝]刘义庆[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江苏师范大学“153”人才引进工程科研支持项目(项目编号13XWR009)阶段研究成果之一]
潘天波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