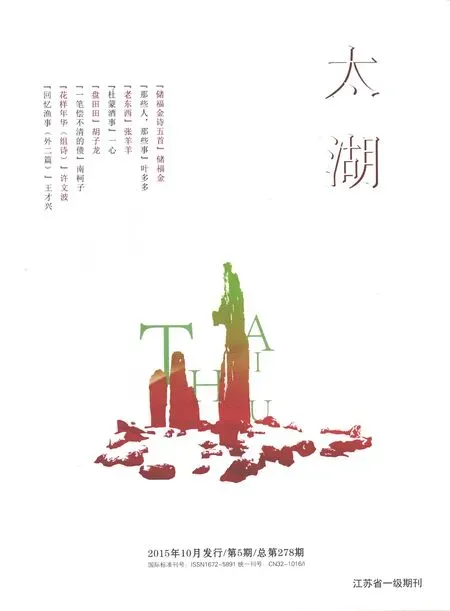转经路上
王瑛
转经路上
王瑛
写在前面
天亮就要出发了。依旧是一个人。朋友都劝我不要单独远行。但心底的渴望无法停止。我依旧是那么任性。在城市里我总是浑浑噩噩。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样的。哪里才是真正的心灵的故乡。
我怀念在路上的时间,在别处的生活。怀念那些单纯的眼睛。
就让我匍匐在卡瓦格博的脚下。
(一)车窗外的世界
在长途卧铺车的颠簸中醒来,不觉已是半夜。车里温暖,四周的人都在熟睡。把车窗拉开一些,只听得尖利的风声呼啸过疾驶的车,夹杂着巨大的流水声。在静夜中轰鸣。
夜色发暗,我看不清茂密的树丛、岩石后,那条河流真实的模样。该是金沙江吧。我探身去看,虎跳峡镇的招牌在夜色中飞快地擦身而过。
湿润而冰冷的空气透过车缝扑进来,我呼吸着异乡的气息,感觉遥远而陌生。想到自己已在路上了,心里平静充实。这次旅途请假不易,很是珍惜。
接近凌晨时,后排小婴儿突然醒来,哭闹着。我被惊醒,心像被猛地揪了一下。睡在孩子身边的老人含混不清地拍他,哄他睡去。小孩子睡一会儿,闹一会儿。车子无声无息地停进了中甸客运站。
夜,仍是黑得无边无际。心脏极不舒服,感觉到疼,且不能呼吸。平躺着闭上眼睛想忘记。
天色微微发亮。车子又驶在路上。窗外已能看到远处,半坐着眺望。开阔的山谷间有村庄错落,随着光线的渐渐清晰,白色的炊烟袅袅。我看到巨大的湖泊荡漾在连绵的山间,像一幅淡彩,云低低的,草甸嫩绿。湖水中藏有天空的湛蓝。昨天上车时,同车的男孩和我换了个铺。古古为我提前买好的票是靠窗的,这下如愿换到了下铺,如此躺着看外面倒也舒服。我是很喜欢这样的长途卧铺车的,常常觉得这样才是远行的开始。
天亮起来,太阳也升起来,车上的人还在睡梦中。快九点时,车停在一个小镇上吃饭。
我下车洗漱,心脏已无大碍。没有去吃东西,拿着相机四处晃悠。阳光很暖,我懒懒地在土路上闲逛。这边的山像是皱着眉头,令我想起怒江。那穿着枣红色衣服的男子蹲在路边,看着两个同伴把砖从土窑里搬到卡车上。那条绿树依依的小径上,卖梨的女子脸蛋红红的走过。藏屋前的野花开得热烈。我买了几个梨,那女子说这里离奔子栏还很远。上车,慢慢开始盘山。路如同丝带般在山体上蜿蜒起伏,远处的小镇慢慢退到了谷底。不断拐着弯,渐渐地,我这边的窗外再也看不到山了,全靠着山崖。回过头去,车窗的另一边,巨大连绵的山就像是一幅幅壮观的画,我们的车子就如同在画中驶过。窗那边的男子睡得浑然不觉。而我早已惊叹得坐了起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有气势的山,心中欢喜。
远远的高山顶上有大团的云层,看不真切,似有积雪。我一直看着那里,想着途中将要经过的那些垭口,祈祷着神山护佑。能让我通过时有个好天气。
随着山勢的越来越高,植被也悄然发生了变化。高山草甸,原始森林转眼进入眼帘。就快到白马雪山垭口。
我一直在拍照,拉开车窗,手冻得冰冷。几乎要僵掉。而窗外的景色让我不断地想按快门。车开得快,风很大,只能拍几张,然后关窗暖和一下。我靠在身后的枕头被刮进来的风吹到了地上,却浑然不觉。车上的人还在睡。本地人对于这样的景色早已习以为常。
山谷间的秋色已显露。高原的山色彩很丰富。车行在这里,真是种享受。远远的有雪山,草甸的颜色一层又一层。伴着清亮的溪水流淌在山野。我躺在铺上,就这样慢慢过了白马雪山。
在这样雄浑的景色下会觉得人的渺小和外面世界安静的力量。而我此刻,需要如此简单的心情和纯粹的旅行。中午时分望见有座模样奇特的高山挡在眼前,寸草不生,土红色,山顶的排排石柱像张开的手指。我想那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说拉山口。
车子又开始拐弯,毫无准备,我忽然看到了卡瓦格博,他就那样昂然而亲切地注视着我。白云像是系在胸前的哈达,冰川蜿蜒着。很感动。能在路上就看到神山。多么幸运。
离德钦越来越近了,心中又念起菜菜,不免有些难过。曾答应过菜菜一起去梅里雪山,如今他已离去。总是悲伤,总是心情沉入谷底。我已不再那么热情,也不再能笑得纯粹。我看到镜子里自己那颗灰暗的心。
我一无所有。此刻,我所能做的,只是认真转好这次经。
(二)决定
中午,十二点半,行驶二十个小时后,长途车转过一片山谷,我看见德钦,镶嵌在绿色的山谷。像航拍的照片。卡瓦格博一直在路上相随,我的视线总被他深深吸引。在藏文经典中,他又被称为:“绒赞卡瓦格博”,意为 “河谷地带险峻雄伟的白雪山峰”。千百年来,淳朴的藏民认定卡瓦格博地区就是藏传佛教密宗最著名的本尊之一——胜乐金刚的宫殿。在藏文的经卷中,梅里雪山的13座6000米以上的高峰,均被奉为 “修行于太子宫殿的神仙”。而主峰卡瓦格博是藏区八大神山之首,相传他原是无恶不作的煞神,后被莲花生大师收服,成为藏区的护法神。掌管着人世间的幸福和死后的归宿。
从见到他的那刻起,心被强烈震撼。我深深相信雪山是有灵性的。终于明白为何当藏人说起卡瓦格博时都那么崇敬。他们双手平举,称他为:“阿尼,卡瓦格博……”(我的父亲,卡瓦格博……)。藏族人相信,每座雪山上都居住着神灵,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灵所赐予的。而神灵需要凡人去供奉和朝拜。这是藏族人世世代代朴素的信仰。据记载,自从活佛噶玛巴希的第三世 “罗尼杜吉”活佛开启了神山朝圣之门,这条环绕主峰卡瓦格博的大小转经路已有了七百年的历史。每年秋末冬初,一批批来自青海,西藏,四川的香客络绎不绝,他们虔诚地用身体开辟了一条条从遥远家乡延伸至卡瓦格博的朝圣之路。藏民族非常看重来世。在来转经之前,我查看过一些资料。每年都有在转经途中因体弱多病或精疲力尽而倒在路上的藏民,但他们并不以此为不幸,反而觉得这才是最好的结局。在朝圣途中陨灭意味着灵魂得到解脱,直接进入了天堂。没有哪个山地民族能像藏族这样,为了信仰能舍弃一切,甚至是生命。在如此圣洁的雪山面前,我对即将到来的旅程充满了期待。心里暗暗决定就算再苦,也一定要将外转之路走完。能沿着神迹,匍匐在卡瓦格博的脚下,是何等幸福的事。
我想起曾看到过的一句话:“每个转经人在转经途中,都是轻松愉快的。”我相信那会是一场自然的盛宴。在噶玛巴活佛所作开山祈文:《绒赞卡瓦格博圣地赞》中,我记得有这样一段经文:
“光交错的地界,法台上雄踞绒赞山神卡瓦格博,其形如众戟林立,其顶似雪,祭品林列。其色像飘逸的洁白哈达,在神山空行母静居处,都是明持纯洁,处处布满空行勇士。乐器奏响,悲歌响亮如倾盆之雨。观音行善如云聚笼罩。祈请绒域山神卡瓦格博引向涅磐乐土,至此不再入阴间,护送死者径直升入西天极乐世界。”
我看到这段经文时,心里一动,想要为菜菜做点事。自他在北京因意外离去已整整十个月。每每想起他的灵魂还在异乡飘泊,心里就无比感伤。我想完成当初的诺言,了却他的心愿。选择外转经的方式,也是自己心灵的需要。
午后一点。灼热阳光下,车抵德钦。不宽的街道,来往全是藏人,这里有我喜欢的安静生活气息。在客运站查看了时刻表,不久就有去羊咱的班车。但我不想太赶时间,在德钦休整,明天一早出发。还有些东西得准备。住在德新藏家楼,安静的楼里只我一个住客。偌大的三人间空空的,窗户对面的山谷里可以看到一个叫卡博宫的地方。高原的阳光晒得我有点晕,四周深色群山环抱,我喜欢这个地方。洗澡,出门买点东西,回来睡了一会儿。醒来发现有俩外国小伙子同屋了。当晚是中秋。昨天出发时,冬来送我,还要帮我背包。临别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个包装好的月饼,这个80后的小男生见面话总是很少,却让我感觉温暖。这里过中秋倒也热闹,放烟花。街上游荡的年轻人很多。客栈的老板邀请我一起看电视,一起吃桌上堆得高高的瓜果点心。老板的小儿子和我聊着天。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说了会话就要去念经做功课了。一直记得他和小孩子说话时耐心好听的藏语声音。
回屋前在楼顶抽了支烟。四周一片黑暗,远处山上的房子里隐隐有些灯光。月亮很圆很亮。在街上溜达时并没看到多少汉族人。去别的客栈也问了,最近并没有去转经的汉族人。发消息给密蜡说看来是一个人走了。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并不感到孤单。本来就没打算约同伴,想一个人安静慢慢地走。在别人看来这很不靠谱,密蜡总说你至少要结一个牢靠的伴。
下午给付老买转经筒的时候,遇见一个坐在店门口的藏族男子,他戴着深色的软泥藏帽,眼睛很深。他以为我要去雨崩,结果得知我要去外转。劝我一定结伴而行,要小心。千万不要一个人走。
密蜡很早就提醒我发征伴启事,他说你需要帮助。我是倔强的,心里认定的事,就不会改变。这次外转是很快做出的决定。当我慢慢看资料时,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密蜡曾问我,你就一点没打过退堂鼓么?我答:想好的事就要去做。虽然我知道自己毫无经验,只有一颗虔诚的心。祈望着神山赐给我好运。我情愿一个人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同转经这样的方式,何况是外转。我自己怎么都可以。常常觉得旅行是自己的事。在出发前添了些路上必须要的装备。我从来就没露过营。对此一窍不通。除了去年走怒江时,路上碰到师傅和悟空,在怒江边扎营两晚,但那也是人家带的东西。我的包在机场过磅,足有三十斤重。还不带帐篷和垫子的重量。如同一块巨大的石头。出发前总让我看着默默叹气。我如何能背得动它呢,但十几天在外,不带又不行。
但密蜡说不算重不算重。我自己也满怀希望地想,到了羊咱村找到向导就好了。行李往骡子身上一扔,空身走路多轻松。可在昆明出了机场,搭公交车走了半小时到新南站客运站,背着大石头,我的衣服就都湿透了。早上六点半,黑暗中轻轻起身收拾。街道很安静,德钦还未醒来。发往维西的车隔天一班,七点发车。车上坐满了藏族人。天亮了,一上路就开始盘山,这条路不好走,车子蹦来蹦去的,有些路面很危险。坐车的人很多,位子都没了,我把大包放倒在地上,让一个男子坐在了上面。很快,车的右面出现了雪山。我目不转睛的看着,真美啊,和卡瓦格博很不同。我问身边的女子,那是什么山,回答是缅茨姆。原来是卡瓦格博的妻子。车过云岭后,又行了一段,两小时后到达羊咱桥边。在桥边小卖部我掏出向导顶真的照片向人打听,得知他就住在上面查理顶村。羊咱桥看上去破破的,两边拉着经幡,在风中好似向我招手。右边山上有白塔,那里是上山进村的路。桥下便是湍急的澜沧江,上桥便开始外转的道路,从此跨越澜沧江,转过怒江后再回澜沧江来。我无限留恋地在桥上逗留了一会儿。前方未知,出门前第一次给自己上了份保险。听从唐唐的话,留了份行程表在家中。还是没有告诉父母实话。
过桥便上坡,我开始不争气地喘了。手里提着捆在一起的帐篷和垫子。到了上面索性把帐篷等绑在了包下面,脱了衣服。在村子问了人,得知那个曾带密蜡转山的向导顶真就住在前面。我向前走去,在村口看到五六个藏族人坐在路边喝茶。想他们也是来转山的。向他们笑笑就准备走过去。
有人喊我,哎,你要去哪里?我停下来。那个长着白白的脸,胖胖的女子,在正午太阳下眯着眼问我,她看上去倒不像身边黑黑的藏族人。我说要去找向导。女子说你也是来转经的么。我们一起走好了。她喊我:“一起坐下来喝茶嘛。”我想起磨房上毛栗的话:“藏族人很热情,会邀请你一起吃喝的。”
我也想过跟着藏族人走的,但毛栗说了,包控制在二十斤以下。我对女子摇头,指着我一卸下来就如释负重的石头说:行李太重了,非得找个向导和骡马。跟女子对着坐在旁边,脸很黑瘦,头发乱糟糟的男子用藏话说了几句。那男子朝我看,笑了。女子说:我们做你的向导吧。请向导多贵啊。我摇头,不行啊,自己走的话我背不动行李。女子说她们共两个人,拉萨来的。本来只想去小转。路上碰到了这一大家子,就跟着来转山了。她叫泽西,不停地鼓动我,一起走一起走,没事的。我坐在那里,左右为难。我能背得动自己的行李么?我是真想跟着藏族走啊,像毛栗说的,能体会更多人文的东西。多有趣啊。可是要真在路上背不动了可怎么办,没有向导可找了,那就要一条路走到底了,那些垭口,那些高差。我不敢想下去。端着大碗,喝了无数碗清茶。泽西又劝我:“这不是酥油茶,是清茶,清茶好喝,喝了一会儿好爬山……”爬山?天哪。这时,从下面支信塘小庙走上来十几个藏民。原来他们都是一起的,刚才去庙里行了仪式,这个庙被称为“领取转山钥匙处”。不少男子的手里都拿着好几个树上采的石榴。女子的围裙里也有。他们都很好奇地看着我,不会说汉语。泽西说了我也来转经。藏民都看着我,分给我石榴,不断劝我喝茶。
这一大家子人真够多的,男子偏多。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就在一根村口的水管下冲头发。女人们忙着倒茶,穿着玫红色上衣的女子坐在地上的样子让我想起一幅画。
阳光下我忙着拍照,真好看啊他们。如果一起走的话能拍到不少有趣的片子吧。
有个头发卷卷的男子看到我壮观的行李。他好奇地用手去提,结果发现很重,就大笑着叫起来。
泽西说,这是转了三次经的。他是领头的。
卷发背着硕大的佛珠,穿一件蓝色的旧衣服,笑容让人很放心。泽西怕我担心,一再说他们都是西藏昌都的牧民,人很好的。我很放心藏民,就像我在怒江碰到的师傅和悟空,一见到他们我就安心。但还是担心自己会背不动行李。卷发把他的饼分给我吃,他们都不会说汉语,只有泽西和她的同伴会说。那个饼象馕一样好吃。
我忽然想起自己连干粮都没准备。原想着反正要找向导,只买了四包方便面,还是HU发短信来提醒的。
泽西说没事,你能吃糌粑么,我俩带了好多呢。我点点头,想糌粑是啥呀,一定很好吃。藏人们吃喝完,各自收拾起来,准备上路了。泽西说,马上要爬山了,我们走在前面吧,这样轻松点。矛盾中,我还是无法抵挡和藏族人一起转山的诱惑。我想起那句:转经人在路上,永远是轻松愉快的。好吧,背上我的石头,出发。
(三)此时
我已记不清是谁一次又一次在我身后托起我的行李,好让爬得像牛一样喘的我稍稍省点力。我甚至怀疑自己的前世很可能是头一直负重的驴子。低着头,沉重的行李让我再也直不起腰,汗水砸在泥土里……这就是泽西所说的爬山。但这仅仅是刚开始。
穿过查理顶村,开始往山上走。土路一点点往上盘。出村子的路边有棵大树挂着木牌,围着哈达。用藏文写着一串字。藏民们围上去仔细地辨认着,泽西说他们并不识字。忽然领头的卷发往下面跑,大家呼拉一下扔下行李都跟过去。我不明白发生了啥事。泽西边往下走边回头:听说有活佛噶玛巴留在岩石上的手印和足印……我也往下跑,在路边一块青黑色的大岩石上,围着些经幡。赫然有深深的手印在上面。学着藏民们用手摸,虔诚的用额头去顶礼……我庆幸能跟着他们走。回来后看土豆介绍的那本书:《圣地卡瓦格博秘籍》,才知道这一路上可朝拜的圣迹比比皆是。不久又经过莲花生大师修行的山洞。藏民们走一段便会停下来靠着岩石壁休息。这也是我最为轻松和愉悦的时候。不卸包,就这样靠一会也会好得多。藏人们已热得拉起了外裤,露出里面厚厚的毛裤。泽西大姐和她的同伴已爬得满脸通红,她们买了两个背篓,里面重重地压着被褥和一蛇皮袋青稞粉。看上去可不轻。我估计自己的模样也好不到哪去。
又往上行,渐渐地我们已爬到半山腰处,对面山上散落着绿色的村庄和田地。藏民们开始四散在路上采摘一种松柏。我好奇的问泽西,为啥要采这种叶子呢。这不是很平常的一种松树么。泽西提着红色的袋子,戴着手套,一把把的往袋里装松叶,递过来一片说:你闻闻,只有这里的松柏叶是香的呢。而且被活佛加持过,带回去烧香或送人,是最好的礼物。我凑近,是有股特别浓烈的香气。真神奇。藏民们或爬到树上,或围在一边,采摘的速度特别快,嘻嘻哈哈的一会儿每人手里就很大一把了。可我总不得要领,只抓得满手碎叶子。有藏民来示范,喏,这样采,就是一把。拿出保护相机的防水袋来装。至今打开袋子,那香气还不散。沿着碎石小路又往上行。渐渐地路越来越陡,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爬升。我的帐篷垫子绑在包的下部,往上爬时总觉得包在往下坠。拉紧了收缩带,走一会儿就要弯着腰跳一跳,让自己背上的包滑上来些。
正午时分,虽是深秋,却觉得天气炎热,爬在山头上无遮无挡。但也懒得戴帽子。唯一的愿望就是盼着快快卸包休息。前方高高的山顶有经幡飘扬。我们在山脊上行走。澜沧江在谷底流动,两岸的山壁林立着。之字形的小道在深红色的山体上纵横。景色壮美。
我的汗流个不停。老是听到有 “嗡……”的一声。以为是自己幻听,或是身体虚弱出现的耳鸣。回头,却发现原来是念经的藏民发出的合音。他们手持念珠,低头边走边念念有词,尾音拖得很长。很佩服他们,我已爬得啥想法都没了,唯一的指望就是听到他们说休息。道很不好走,有时有深沟,背着重负的我控制不好自己的重心。忽然觉得自己浑身一轻。愣了一下。回头,满脸皱纹的藏族阿妈自己扛着大袋的青稞粉,却用力托住我行李的底部往上推。很不好意思。拉着背带尽量靠自己走。
在这之后的山道上,不时有藏人在我身后默默帮我托行李。我们爬上一个个山头,任风吹乱头发。汗水流满脸庞。我看到高高的杂草后,藏人那纯朴黝黑的笑脸和真挚的眼睛。他们坐在山脊上,乐呵呵地望着我给他们拍照。转经路上,他们从不以此为苦,反而像是去春游般快乐。他们和自然是如此融为一体,让人心生感动。
泽西大姐看我背东西吃力,说,小王,把你的东西分给他们背吧。那我怎么好意思呢,第一天就要人家背包。我万万不肯。泽西劝我,说没事的。卷发领头刚才一再和泽西说让我把东西分给他们背。我原先提在手上的那个装水瓶和杂物的塑料袋已被藏族阿妈夺走,每到一个休息的地方。她都会把里面的水瓶递过来示意我喝水。我很不好意思。藏族人唤我 “噶莫”,那是 “汉族女子”的意思。我总是对他们说谢谢。泽西告诉我,他们说,一家人不用说谢。他们看我弯着腰,吃力地往上爬。便想帮我分担。指指我的相机腰包,指指我背后的大包。我都谢绝了,还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泽西笑,他们问你是不是包里有贵重的东西。所以不肯让他们背……我们坐在山头上休息。已跨过了澜沧江,我看到从羊咱桥上来的那条路,那么遥远在远处的谷底。别了澜沧江,前路漫漫,不知何时再能回来。
翻过山开始往林子里走,依旧是上升的路。坐下来休息。阿妈把裙子里藏着的石榴分给了我。舍不得吃,放在兜里。解开衣服扣子散热,泽西帮我照了张相,看见自己累得不成人样。
两点半,越爬越高,遥远的山头似有积雪。半掩在云雾中。喘息中,看到卷发连比划带手势地对我做了个睡觉的动作,又指指前面那个坡地。笑了。泽西翻译:老大说,今天是第一天爬,大家别太累了。就到前面住下了。算起来,今天才爬了四个小时。但佩服自己能坚持下来。很累。挣扎到坡地。环顾四周。这是一面斜斜向上的山坡。只有一棵大树下有块稍平整的平地。藏人边上坡边四处拣拾树枝,很快卷发和一个男孩子用石块搭起了灶,燃起了火。烧得发黑的水壶用木头架起来。右侧据说有泉眼,从山上引下来特地给转经人取水,几个男子快步下去用锅接来。大家卸包,四散成两圈,围坐在一起。
藏人煮茶,放一把盐,放点粗茶叶。用水煮开。每人面前一个搪瓷小碗,有些是木碗。冲了水之后放一大勺酥油。他们还喜欢放大块的奶渣。就着茶,每个人都会再摸出个小碗来,倒上青稞粉,用一点点茶,用力来捏糌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糌粑。在泽西同伴大姐的手里变成那么个褐色的团子,很实心的样子。泽西在小碗里放了些榨菜丝,冲了些水,就着糌粑吃。其他藏人都是用些辣椒末蘸水吃的。其他就没了。老大掏出他的那袋饼,大力地掰一块给我。然后挖很大一块酥油,在放到我碗里前,他停下来看我。我有点犹豫,泽西说,喝点酥油茶吧,会有力气的。于是我点头,看那块酥油瞬间融化在热茶里。我心里也热热的。碗里又丢进好几块奶渣。老大那一大布袋里装的全是这硬邦邦的玩意。泽西递过来捏好的糌粑,说趁热吃。咬了一口,是淡的,有种粮食的清香。配着辣椒吃挺顶饿的。我只吃了一团就再也吃不下了。时间尚早,才三点,已在吃吃喝喝了。掏出手机忽然发现还有信号。上路前,匆忙给密蜡等几个朋友发了消息,告诉他们我跟着藏族人进山了。以为密蜡一定骂我不找向导,就关了机。收到消息他让我保重。天空是亮堂堂的,几轮茶喝下来觉得身体的疲惫劲都过去了。我想起背包里有牛肉干,就拿出来分给大家。一直在吃他们的东西。很不好意思。
盘腿坐在石头边,看着云压在山顶上,似有暮色笼罩着四周的群山。这里很高,望出去,山是一层又一层的连绵不断。像海里的波浪。泽西忽然问我,小王,老大他们问你为啥要来转经……我艰难地告诉了泽西。以为自己已经平静下来,但是眼泪还是忍不住在打转。回过头去看那些山,这里虽美,但菜菜却永远都不能再看见了。还是不争气地流下泪来。泽西递来纸,她用藏语告诉老大他们。然后对我说:这样外转对你的朋友是最好的……老大提着壶给我倒水,不断劝我喝茶。泽西说:你别难过,你这样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听她话语哽咽,回过头竟看到泽西和她的同伴都在抹泪。泽西怕我还担心一个人走不出去,告诉我,卷发老大说了,一定要把你带出无人区。再往前走要三天,没有村子。放心吧,我们一起走。明天把行李分给他们一起背……心里暖暖的。和藏人相遇不能不说是种缘。昨天还在后悔自己为何不买晚点出发到羊咱的那班车,那样就不用早起了。那会是另外一种行走。
而此时,我就在这里,就和他们在一起。
(四)寻常众生
坐在黑漆漆的山口,星星在眨着眼睛。世界是如此安静。我想画画,名字就叫垭口晨曦。
我知道藏民爬山都起得早,却没想到四点多就要出发。泽西大姐和她的同伴昨晚和我挤一个帐篷。她们怕睡不下,建议横过来睡,这样宽敞点。我腿长,老伸不直,蜷缩在睡袋里,一宿没睡踏实。
迷糊中只听得刮了一夜的大风。那风声很厉,一阵紧似一阵的。把帐篷布绷得紧紧的。我开始担心三人是否会被这风吹下坡去。帐篷扎在一个陡坡上,灌木丛边。没有别的选择了。记得密指导说,选择营地应:安全,平坦,避风,近水。喝茶的大树下,是此处唯一较平坦的地方。藏民们人多,且没有露营的东西。他们睡在这里最合适。一旁有土堆,也能挡风。泽西有些害怕,我的帐篷可睡两人,便说咱们仨挤挤吧。她放下心来。但又开始担心山上会不会有落石砸在我们帐篷上。风那么大。我安慰她一定不会的。平整营地时,地上有不少高高的杂草和石块。这边是上山的坡,并没有特别大的石头。在搭帐篷这个玩意时,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我忘了怎么把地钉、内外帐的钩子挂在一块儿。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搭。买东西的时候,密蜡示范过一回。我看他轻轻松松就把两根管子,两块布倒腾成个帐篷。当下觉得倒也不难。密指导在我出发前曾提醒过,你自己得单独搭一回。这话全被我抛在脑后,不在意地答:“没事,我全部都记得呢……”可现在,怎么弄都好像不对啊,根本拉不紧。真是太丢人了。后来还是几个藏族小伙子来帮忙,最终挂了上去,地钉全部深深地插在土里,并用大石头牢牢固定了帐篷四边。大约凌晨时分,我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一阵大风,夹杂着密集的雨点砸在帐篷顶上。我们边上就挨着露宿的藏民们。昨晚在天黑前,我忙着早早地搭帐篷,整理内务。藏民们还要围着火堆喝一顿茶。比我们仨晚睡。现在下雨了,听声音还不小,睡在露天的他们可怎么办呢。我听到帐篷外的藏语声此起彼伏,一阵忙碌。泽西醒了,轻轻说,小王,我们起来吧。泽西在临睡前说今天要早起,最好比那些藏民还提前些,因为我要收拾帐篷,比他们慢。我看看表,才四点多。实在是不想起啊。从没有这么早爬过山。天一定也黑着。泽西和她的同伴很快穿好衣服,钻出了帐篷。在外面大声和老大说话。才知道原来老大昨晚就睡在我们帐篷旁边。
赶紧起来吧。穿衣服,钻出来收拾东西。天黑着呢,空气清冷。泽西和女伴很快收拾好了,和女藏民们背好行李,准备上山了。我还在手忙脚乱拆帐篷。大家打着手电来帮忙。他们速度很快,一下子就把帐篷和垫子全收好了。老大把它们放在了自己的背架上。我使劲往袋子里装睡袋,大家都好了,都在等我呢。一个小伙子过来把睡袋拿走,示意我上路。我背上包忽然发现自己还没穿好鞋。越急越是穿不进去,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穿。众人都笑起来。雨已经停了,泥土微湿。我走在中间。没有了帐篷,垫子和睡袋,大包轻了不少。我拉紧背带。一步步向上。打着手电,路崎岖不平,很费体力。很快,衣服汗湿了,沉重地喘着气。我可不敢脱外套。我知道自己着凉了就爬不动山了。忍着,就让汗淌个痛快。低头时总能闻到自己身上散发的汗味,隐约间还夹杂着一股酥油味。大喜。路边休息。大部队与走在前头的泽西她们会合了。天依旧黑着。和藏人们坐在地上。拿出背包里的奶糖和巧克力分给他们。出来前,没多背,按路上的天数准备了一点。一圈发下来,所剩无几。倒也省得我再长途背着了。藏人们双手接过,小心地剥开包装纸。我后悔没多背点。静悄悄的山里一片寂静。这样的体验何曾有过。继续上路。月亮还在头顶。在凌晨爬山,身体虽痛苦,但心里还是喜欢的,就把它当早锻炼吧。挺好。借着手电的光,我们爬上了一个垭口。这座长满了松树的山,《圣地志》中称为多拉,意为松树岭。而它的另一个含义是:翻越此山能得获得一亿遍观世音心咒即六字真言的功德。多拉意为亿山。山顶的进香台。3150M。
黑暗中,经幡纵横林立。密密的挡着前行的路。有了经幡,气氛就觉得不一样。毕竟那是沟通世俗和神界的东西。藏人称之为 “龙达”,俗称 “风马旗”。我们顺着路,拨开头顶和前方密布的经幡往前行。走在最前头的藏女忽然大声呼唤。老大跑过去看,那条下山的路异常陡峭。凭记忆,老大最终找到了正确的下山路。下去前,我们在垭口上卸包休息。喘着气,看着还没有亮起来的天空中,轻轻闪动的星辰。伟岸的松树,远处连绵的山体沉在静谧中。靠在岩石上,深深呼吸,我感觉到幸福。忽然很想画画。愿意长久地记住这一切。
下山的路有些陡,好在天色微微地开始亮起来。我也关了手电。走进林子里,庆幸不用吃力地爬坡了。转眼就进入了阿色大道。密密的树,泥土很厚,若是雨季,这样的稀泥路一定不好走。我想起同样走过外转之路的女孩——HU,我在她的博客里曾看到过这里的照片。那些在原始森林里行路的记录曾经一度让我对外转的路充满了向往。而今,当真踏上了这里的路。心里满是感叹。只有真正走过转经路的人,才会知道其中的滋味。从一月决定,到九月成行。其间的九个月都在做着准备。花时间找资料,密蜡借了两本书给我。每个休息日,带小狗来来出去溜达。他高兴地满世界乱逛,我低头一遍遍地看书。从对这条转经路一点都不了解,到慢慢知道我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一切。这条外转之路,围着神山卡瓦格博作360度顺时针朝拜绕行。迪庆藏语称外转经为“叫古”。其中大半线路在西藏的察隅境内。这中间需翻越高山六座,其中4000M以上的三座。整个外转经徒步距离约在200KM以上。累计高差数约在9000M以上。超过了我任何一次的远行。出发前有一天,坐晚上的轻轨,列车缓缓驶过夜幕下的城市。望着对面玻璃窗外,远处高楼的隐约灯光,想到自己将会跋涉在茂密的森林,宿在无边的黑暗中,忽然感觉到一种无助。悟空同志很早就想陪我一起走这段路,我谢绝了。我理解他的好心,但不需要 “陪”。虽然他是个很好的同伴。出发前常老师也说,你得找队伍啊。一个人找向导?你很有钱啊?我告诉他,其实我有一些害怕。但坚持不喜欢和叽叽喳喳的人一起走。我会嫌烦。虽然自己也有过叽叽喳喳的时候。但好像这几年越发变得沉默了。不擅和别人交往。我记得老常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我知道像我这样的肯定有点傻。我的胆子不算大,也非猛驴。不想挑战自己,也不想证明什么。只想安静地走好这次来之不易的转经路。能碰上这些好心的藏民做同伴,实在是我的运气。
早晨七点,终于在路边休息时拍下一张同伴的照片。但放大看,还是糊的。天色不够亮。我却没舍得删。他们坐在地上朝我笑。每个人的脸都是红扑扑的。除去多余的衣物。继续前行。这里山峦叠嶂,远处有村舍。翻了几个山头,八点左右,我们到达一处高山流下的溪水旁,在此休息喝茶。
从凌晨四点半爬到现在,大家都很疲惫,肚子也早就咕咕叫唤了。卸下沉重的行李,终于如释负重。溪水冰冷,在水边刷牙洗脸。泽西笑得露出雪白的牙齿说:总算舒服了。小伙子们都不怕冷,还在水里洗脚。老大他们却顾不上洗漱休息,忙碌着生火煮茶。泽西问我现在要不要吃个方便面,我摇头,就吃糌粑挺好的。
休息到九点。男人们还要喝一顿茶。我和女队先行。泽西说,早出发早休息。这是不变的道理。
上包了,这是最痛苦的时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虽稍稍恢复了体力,但身体对长时间的负重体验仍有记忆,本能地抗拒着。阿妈的包就在我旁边,是个黄色的蛇皮袋,装满了青稞粉。看她艰难地背起来,这么重的行李。就靠着自己在袋子上缝的两个把手,用塑料管套了。就这么一路背着。老阿妈一直稳稳地走在前头。她还帮我拿着那个放水瓶和杂物的袋子。这一路上,同伴的行李都是用树枝做的背架,叫作 “廓嘎”。这些自制的简易背架完全没有背负系统和牢固的背带,就这么被结结实实地捆上了十几天在山里行走所必要的被子,锅碗和青稞粉。但他们一路都飞沙走石的,完全不为沉重的行李所烦恼。我想起了怒江的同伴,师傅和悟空。当时师傅背着个军用的背包,也是非常的沉重。但他俩也默默地走了一路。
路上,我渴得冒烟,喝水时,先让阿妈喝,她却老是摇头,我以为她客气。再给别人,他们全都摇头表示不喝。后来才知道。藏族人爬山时不喝水,到水源地会煮茶喝很久。
我们女队共七人,泽西大姐和同伴走得很快。她们已在远处看不见了。我和藏女们在后面赶。还是绕着山的一侧在爬,时而上,时而下。透过茂密的灌木看远处,山底的那条小溪蜿蜒着,很清亮。藏女们手持念珠,口中念念有词。和藏民转山,心里总是很纯净。但心里还是常常会想起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无法理出头绪。一个小时后,终于在一处密密的林中看到了正坐在地上休息的泽西和她的同伴。泽西的同伴总是戴着顶宽大的遮阳帽子。双颊通红。她穿着藏裙,年纪和泽西差不多,听泽西说是她的表姐。却比泽西看起来更像藏族人。赶上她俩后,我们坐在那里不卸包休息。头顶的枝叶随风簇簇落下。调皮的藏女爬到树上去采野葡萄。递过来一大串,黑色,小小的。很甜。笑声回荡在安静的山中。
阿妈玩着葡萄叶子,冲着我的镜头做鬼脸。卓玛在专心修她的佛珠。行走时,我并无多余的力气拍摄。只有在休息时,尽可能多的想留下些回忆。远处的高山中有瀑布飞溅,心里很安然。泽西说我们继续赶路吧。
没走多久,我们来到了一处经幡密布的地方。地上,树上满是旧衣物、首饰和用彩色毛线悬挂的小石头。路边有个小石洞。我看同伴们都默默排好队朝石洞走去。泽西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这个洞叫 “中阴洞”。说是从这个小洞中钻过,表示在死亡之时,能顺利通过 “中阴”过程,达到往生净土世界之愿。旁边的树上又有红红绿绿的毛线上挂满了小石子,这是朝圣的人们表示将自己身上的所有孽障集中在这块小石子上,遗弃在这里。中阴,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指的是人死之后,亡灵抛弃前身,而又尚未转世投胎之前的状况。中阴有七七四十九天,其中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临终中阴;中期:实相中阴;末期:投生中阴。《西藏度亡经》的说法是:“亡灵进入中阴境界,就像婴儿进入人世间一样,所体验的一切都既反常而又混乱。以善相、忿怒相现身的佛会相继来到面前,救度亡灵的明光和诱惑亡灵堕入地狱的光焰也会不断闪现。在生前经过佛教修炼,洞悉死亡真相的人,到中阴境界后,能顺利通过种种考验,追随救度的智性光芒得到解脱,或得到好的果报,转生为六道中的天、人等善趣;生前如果作恶太多,或陷于贪欲不能自拔的人,进入中阴之后,便会因报应而堕入地狱,或转生恶趣。”
围绕卡瓦格博行走的旅程,也就是通过死后世界,再重新出生的过程。出现在转山路途中的 “中阴狭道”,也就是 “中阴旅行”的一种象征。转经的人都相信,能否钻过石洞或树洞,和这个人的胖瘦没有关系,而与他积累的福德和罪过的大小有关系。洞里狭窄黑暗,需要匍匐前行。心里默默念经,出来后把手上的佛珠挂在了树上。我们在路边休息。卓玛说着说着大笑起来。忽然,脚步声传来,男队赶上来了。我大为诧异。他们走得可真快啊。半小时后,全体到达约南河边。这条河从雪山上流下来,河水很大,水流湍急,寒气逼人。两旁高山耸峙,古木参天。我们又走一段,在一座木桥边休息。在河边接些水来喝,感觉很清洌。
继续行走,渐渐感觉拉着背带的手,不久就麻木了。虽然卸掉了帐篷垫子和睡袋。大背包在长时间的行走下仍是越来越重。走一小段就迫切地想要休息。我们又进了森林。这里的光线有点暗。其实才中午的时候。可能是树木过于茂密的关系吧。
那条叫 “曲格”的河发源于缅茨姆的背后,一路奔腾而来,在密林中轰鸣着。我们伴着宽阔的河水在林中跋涉。这样的森林我第一次走,感觉新鲜。路上不时有漂亮的景色,如果我独自走,不知拍照要耽误多久。
路有些泥泞,厚厚的青苔,鹅卵般的滑石在脚底一路相随。每走一步,都觉得脚底针刺般疼,一定是起泡了。就这样走着,忽然感觉到林中的寒气很重。我的外衣早就脱去,再没穿上。从早上出的汗就这么干了再湿,一遍又一遍。渐渐地落在后头,阿妈和几个藏女陪着我慢慢走。时而爬点小坡,慢慢挪着。我忽然觉得肚子很饿,极想吃方便面起来,一边走一边想。感觉饿得不得了。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诱人的香味。这两天来除了糌粑便没吃过别的,觉得肚子空空的。可能汉人的肠胃还是适应米饭啊。这可真是一种折磨。身上一阵阵发冷,脚步也不稳起来。我看到路边有块大石头,一屁股坐了下去。心想就让我休息一会会吧。昏昏然闭上眼睛,一下子就睡过去了,居然还做起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