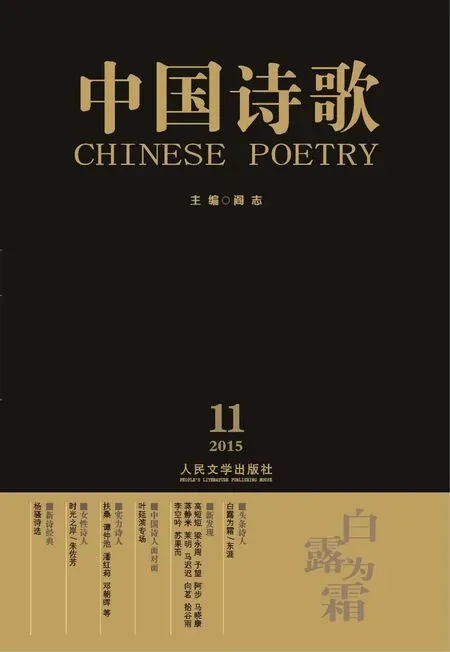诗学观点
□孙凤玲/辑
诗学观点
□孙凤玲/辑
●赵思运认为阿海跟胡正刚属于完全不同的写作路向:一个折射着古典诗学的色泽,一个着力于现代命运的勘探;一个幽禁于自我世界加以返视,一个敞亮于现世境遇加以拓展;一个经营着意象表达,一个执着于口语叙事。阿海的诗歌更偏向于古典诗歌意象群落的复活中彰显一种虚静美学的样貌。他写王维的“月光”与“竹林”,他写古诗中的“细雨”、“鸟鸣”与“桃花”,他写回不去的“宋朝”和“废庭院”。在他的作品里,充溢着浓浓的慵懒气息。阿海的诗触角大多是内倾的。他的艺术世界里“没有国仇家恨”(《古渡》)的宏观抒情。他使用最频繁的词是“梦境”、“阴影”、“睡眠”、“隐喻”。他可以沉迷于“亭子阴影里它不停长出忧郁的六边形”,“像吹破的蛛网般深深扯下去”(《陈家湾午景》)。他聚焦于王维式的幽闭宇宙。他像冬眠的生命一样,触摸着自己灵魂的悸动与燃烧,“湿漉漉的,又要承受/一些桤木,香樟,马尾松远古的记忆,尘世的他们啊/火在讨论生死,打瞌睡的有着蓝色的烛心”(《冬日虚构》)。当他诘问“为何我总要在自己的影子里看到自己”时,我分明感觉他就是那个自恋美少年纳西塞斯。
(《“技艺深沉的走钢丝者”与“讲故事的人”——片论阿海与胡正刚的诗》,《扬子江》2015年第4期)
●丹尼尔·奥罗斯科引用里尔克的话说:“人无法避免孤独,但却不必因孤独而寂寞。”独处是件好事。你仍可以以某种特别的方式接触世界,尽管有时会有些许悲伤。我认为相对于其他东西,这是有益于成长的。写作是件孤独而辛苦的事,你需要独处以完成创作。即便如此,写作生活却并不必是孤独的,也确实不应该孤独。我认为作者能走进又能走出写作的孤独与辛苦是同等重要的:要承受孤独与辛苦,但又要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把这种状态抛开。当你创作一篇小说时,你要活在其中,但你也要活在现实世界里。我即使身处现实世界,有时也想停留在小说中,停留在我的思绪里。我现在依然在纠结。或许我需要有个爱好,或者养条狗。
(《写作是一种承诺——丹尼尔·奥罗斯科谈创作》,《译林》2015年第4期)
●安石榴认为刘汉通这些以自然作为关注面的诗歌,所要表达的并非是与自然触碰的美好,而是目睹自然沦陷后内心的伤逝,以及由此而生的祈祷、相像的修复和虚设的向往。在《花园》一诗中,他借助自然事物——隐喻中的小蜜蜂说出“很少的惊喜”,似乎与我的感受形成了对应,无论如何,作为始终抱有理想色彩的诗人,都不会放弃内心的仰望,即使只能够在写作中徒劳地言说。他试图通过正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的自然事物,窥探并建筑一个维持着自然秩序、万物共生共存、所有的生命声息相通的世界。这个世界曾经存在或者应该如此存在,那些相像中的美好理应出现甚至应该超出想象。然而,在现实的世界以及真实的写作面前,诗人想要抵达的这一愿望世界并未得以出现,他更多的是说出了伤逝,常常从中陷入绝望,他自己也被那种与之俱来的缓慢的悲怆绊倒,仅仅剩下“很少的惊喜”。
(《缓慢的悲怆中“很少的惊喜”》,《作品》2015年7月号)
●安琪说,对我而言,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是,我从未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中国女诗人普遍具有的阿娃、茨娃情绪我确实一点都没有。我整个的外国诗歌阅读倾向是欧美的,时间定位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记得评论家杨远宏教授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发端于二十世纪的现代诗歌运动既是对千年传承的既定诗意的质疑、挑战和反叛,更是对一脉传承中走向定向化、精致化和既定语词、语言惯性、秩序的一种偏离、打破和哗变。跟杨远宏教授一样,我也对现代诗歌运动情有独钟,凡是那些破坏的、反理性的都天然地博得我喜爱,而那些唯美的抒情的圆满的写作则被我视为保守或传统而予以摒弃。
(《外国诗歌之于我》,《世界文学》2015年第3期)
●商震认为一首优秀诗歌,首先要保证诗人情绪状态的饱满,其次是对环境的判断坚定而明晰,进而释放出诗歌内存的强大感染力。而这种感染力,说到底,是一种入心入肺的震撼力和征服力。一首没有感染力的诗歌,无论在结构、词语、意象、修辞等方面营造得如何精妙,都不过是一张工艺精良的假币。任何一首诗都是时代的镜子,无一例外地反映当时社会的情绪状态。这首诗(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就是抗战时期的号角、匕首、投枪,是砍向日本鬼子头上的大刀。在这之前曾有人认为,诗歌无非是花前月下的伤春悲秋或浅吟低唱,直到今天还有人质疑诗歌的社会功能,我不想对这些无知的人进行诗歌教育和道德评判,只想说: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所有的重要时期和重大事件,都有诗为证。比如这首《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时代的号角》,《诗刊》2015年7月上半月刊)
●张定浩认为在诗歌领域中,早慧并不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它往往会遮蔽和纵容很多的不足,并让以后的进步变得非常的艰难。现存各种语系诗歌中最具生命力的那一部分,大多数都是诗人在成年之后的作品。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年纪可以帮助他写出更好的诗,恰恰相反,一个人活得越久,在他诗艺天平上的年龄的砝码就越显得轻微。一首好诗,通常总是某种惯用法的破坏者,但人们称赞一首少年人的诗,往往却只因为他比同龄人更快地掌握了某种惯用法。诗歌中所要求的“新”,并不是线性历史轨迹上的新,也不是站在所谓世界潮头浪尖上的新,而是一种内在的恒久生机,是时时刻刻回到源头和初心的那种喷涌不息的新鲜,也就是对当下自我种种傲慢和自负的克服。
(《“一时之花”与“年年来去之花”》,《诗刊》2015年7月下半月刊)
●张翠、和吟汐认为,对李皓而言,诗是用来生活的。生活时常像谎言一样欺骗着我们的真实,当你陷落其中,生活就成了一个被牺牲的词语,当你只是你所是,你便坚不可摧。李皓本人并不以严格意义上的诗人自居,这并非只是自谦,更多的是自省与自重。从这点看,李皓是智慧的,他懂得诗歌的秘密。因为懂得,所以珍重。李皓的诗,是他个人的说话方式,也是个人视角的观察方式。无论诗的题目还是诗的题材大多是具体的事物或具体的状态:都市生存的精神困惑,个人存在的关注质疑,人际交往的浅薄虚浮,人与人关系的冷漠封闭……他以自己理性、睿智的目光打量这个精神荒芜、生活杂乱的世界,用一种日常的、生活的、细节的、人性的、有质感的诗歌语言展开对现实客观世界的秩序化清理,从而揭开事物和生活的本相。
(《李皓:内心的大海》,《诗潮》2015年7月号)
●霍俊明说,有一点必须强调,不管邱华栋的诗歌写作受到了何种话语资源的影响,这种影响只能是选择性的,换句话说,这种资源是经过诗人的过滤和筛选的,而且经过这种淘洗和选择的过程,诗人的写作只能是作为个体的他——诗人——在语言和生存的晦暗之途上,对语言,对记忆,对经验的持久发掘、命名、发现与照亮。我对那种在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叙述中,将一个汉语诗人的写作直接对应于西方的某某大师的做法不以为然。这种对西方话语的参照,最多只能使中国出现所谓的中国的艾略特、中国的金斯堡等等,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的或最简单的就是,一个汉语诗歌写作者,他是在用母语和个人记忆在写作,这已经足够了,而这恰恰是一个诗人不可替代的创造性的内涵所在。
(《记忆在另一端静静展开——邱华栋诗歌印象或对话》,《诗林》2015年第4期)
●卢有泉认为爱情作为诗歌永恒的主题之一,在不同的诗人笔下总会得到不同的诠释、阐发。像郭虎这样一位对生活敏感而感情又极为丰富的诗人,爱情于其青春的懵懂中突然降临并演绎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初恋,而最终又无奈地选择了结束,其内心的痛苦和追悔可想而知。因此,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不仅对那段早已过去的情事精心呵护,对那个永远青春的女孩时时加以诗意的再现,而且,在他几十年的诗歌做工中,逐渐将当年的悔痛衍化为绵绵不绝的回味,并用记忆的碎片建构成一个完美的童话——关于“雪”的种种奇思妙想,这正是他的爱情诗的底色。
(《用诗歌建构爱情的童话》,《黄河》2015年4月号)
●王士强认为诗歌中的“放”与“收”是一对辩证的矛盾,诗歌需要放得开,需要陌生化,需要有张力,需要形成自己独异的世界,但同时也要收得拢,要懂得控制、留有余地,而不能漫无边际,不可过于放纵,好的诗歌,应该做到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的阅读当中我们经常遇到“放不开”与“收不拢”的状况。有的诗不能说没有“放”,已经具有一定的诗意、诗味,但是很快就“收”了回来,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本来很好的诗意生发的可能性就被浪费掉了。这是收束过紧、“负担”过重、思想上不够解放、写作上不够开放的表现。同时也还有另一个方向上的问题,那就是放得过开而不知收束、收不回来的现象。
(《放得开与收得拢》,《清明》2015年第4期)
●远洋认为译诗所费心血,与自己写诗相比,简直多几百倍。写诗往往有感而发,一挥而就;译诗得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修订,废寝忘食,日琢月磨,还得查阅大量的原文背景资料,形式和内容都力图做到忠实于原作,传达出原作的韵味,展现出作者的独特风格。说呕心沥血,一点不为过。诗歌翻译在当下中国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比如一些刊物无稿费,即使有也是低得可怜,译者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劳动被漠然视之。真正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所带来的陌生化、异质化,实际上是对陈词滥调的清理,是语言的刷新,是一次语言革命。
(《远洋访谈:我的文学素养首先来自母亲》,《诗歌月刊》2015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