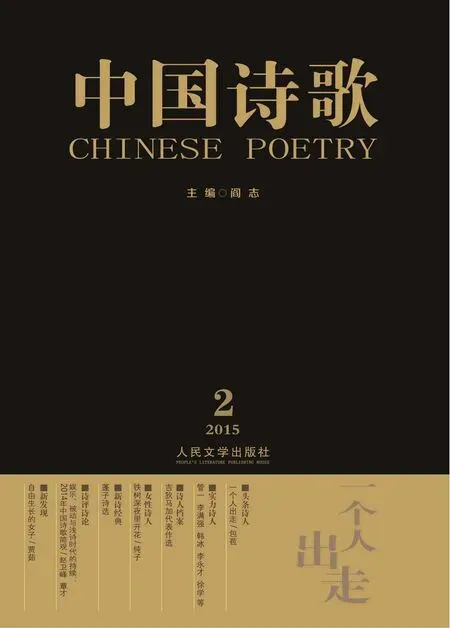铁树深夜里开花
纯子
·组诗·
铁树深夜里开花
纯子
铁树深夜里开花
铁树深夜里开花,我不知道
不会叫的鸟临死前要交出它的那对翅膀
土豆发芽,有人称为旧梦
脚后跟上长痣,是否意味着
那个尾随而来的追踪者已成为我们身体的
一部分?我不知道
天为谁亮,夜为谁而黑着
第二天能够醒来的事物在空气中
都留有幻影,比如铁树
那狐尾似的果叶都伸得很长很长了
我们当中依旧有人
准备钉子,要衰败的那一天
凸显生与死的力量。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只能对着世上所有有模有样的植物说
“来我的土里生长
用我的光和水,但要赐予我
最为隐秘的时刻”
羞怯
那些疼我的人让我感到
羞怯。我那最忠实的几份角色
女儿、母亲、妻子,我做得都不够好
那些疼我的人,他们依旧骄傲
我为很多人奔波、劳碌,我的骨架
流水不曾收留,我那娇小的
灵魂,雪地里的灯盏才被允许遇见
我活于羞怯当中,如落地的鸟儿
那些疼我的人一次次喊我的
名字,对着天空、大地,渺小的身影
我只能守着日益衰老的这副躯壳
可那迷阵似的日子,让我难以启齿
我的一分一秒都在试着躲藏
我有滚烫的心,但却少有透明的器皿
那些疼我的人总是想尽一切办法
让我活着,活像一朵含苞带露的花
大地上的摇篮
悲伤的时候,我会想起大地上的
摇篮,每一个年轻的母亲
她们因为爱,得到了耀眼的光环
大地上,只有这些可辨认的脸
深埋于婴儿的胸脯间
她们歌唱,那银河中飞翔的翅膀
我不断地梦见午夜里的神
从远方赶来,再生于冰川或烈焰
那颗幸福的心谁也无法阻挡
悲伤的时候,我会想起大地上的
利用高质量精播机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等多道工序,省时、省种,也可使用普通播种机,调距降速播深4cm左右,精量点播,粒距一致,深浅一致、株距一致,公顷保苗6-6.75万株(可按6.75-8.25万粒播种)。鲜食公顷保苗按下限计算、粒用按上限计算,保证玉米苗齐、苗匀、苗全、苗壮。
摇篮,每一双安抚中的手
虽然孤单却握着高于一切的信仰
我活在他们的时代
水尺蝽停留于静谧的湖面
棕顶树莺迷恋山崖上秋后的飞虫
大海里有成年的蓝鲸
划定自己的水域,而我
我活在他们的时代
那些从骨子里透出黑白两色的人
失声的人,那些在躯体里做梦
一伸手却只能抓住影子的人
我与他们为邻
在一个时代的空隙里
写字,我得到额外的空气
也因深渊里的呼吸而倍感焦虑
水尺蝽跳跃了一辈子
棕顶树莺死后,山崖上定会挂起
红月亮,海里的蓝鲸愈发孤独
而我,我开始听见自己
被一个时代早早淹没的声音
请在人群中带走可疑的坟墓
我要歌唱的,不是虚假的
荣耀,是生命,那不可剥夺的爱”
惊慌
惊慌,有时会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河流都干涸了,鱼还活着
鱼活在不被我们看见的深渊里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条河流
鱼活着,就从早晨游到晚上
总有锋利的钓钩,让它们尖叫
鱼的饥饿有时等同于我们的饥饿
鱼只向我们妥协,而我们
手足无措,排着长队向世界妥协
惊慌,有时还将是另一种东西
我们死了,鱼还搬动着我们的尸体
在陌生的河流,形同忠实的雇工
受困于玻璃器皿中的蟋蟀
我将安抚的对象只是一只蟋蟀
它曾经跳过人类的头顶
携着秘境,要用一大片低矮的草丛
换取人类一次小小的梦幻
到了今天,它却服从于玻璃器皿
成为一眼即可辨识的囚徒
我盯着它看,犹如盯着不幸的同类
在地球这个透明的罐子里
谁也无法停止攀爬,把别人
踩到脚下,把最高的那束光含在
嘴里。这是我想做却一直没能
放手去做的事情,因为
肉身过于单薄,而灵魂如此强大
这世间的囚徒各式各样
受困于柔弱的肢体,抑或无法割除
命运的痼疾,最终都要疯了
正如这无处可逃的蟋蟀
看上去完好无缺,实际上它活于
别处,不仅仅恐于玻璃的反光
哪怕是人类带来的一次轻微的晃动
它仍将跳跃,被阻挡,被忽视
而后,它假装死在那里
我最后给出的话语由此变得多余
在这个躁动的星球上
每一次退场,都有哀悼的形式
如果一只蟋蟀从时间中
换走了我们的形体,那么
它算是救赎呢,还是更深的罪恶
隐居者
这个世界的沉默
来自我那敞开的黑夜
光线移往这里,散步的神也在
我的指缝间流淌着
他们的时光,信不信由你
所有急于隐居的人
都已犯下和我一样的罪过
他们一次次地忏悔
一味地借用我的躯壳
日渐衰老的声音,甚至包括
那虚拟的脸孔和眼神
可你无法确认,何时或何地
我已来到万物当中
像一道口令,我被宽恕
在或明或暗的族群里
我有玫瑰的香气,却带着罂粟般的
毒,散步的神为此嚎啕大哭
他已丢失迷雾和那最亮的灯盏
某个时辰,我说出了这些
正如沉睡中的隐居者
说出了光辉的历险
老树
盛夏,老树的顶端还能看到新芽
长了百余年的树
我们当中没有几人能惊动它
它立在那儿,成为鸟的宫殿
我们一次次幻想的,那住在宫殿里的人
有雨水般的骨骼,闪电的心脏
我们摸到它的身子,一棵老树
在很多人死后它还活着
如此饥饿,胜过带血的刀子
方圆几十公里,只有一位白头发的
妇人,逢月圆之夜必来树下
她赤身裸体,亮如隔夜的月光
我存在
我存在。
我生活在这样的秩序里
天与地,男人和女人
看得见的及看不见的
我有自己的肉体、声音以及
等待捆绑的历史
我存在。
我是深夜里孤傲的王
我有自己的绳索、深渊和化石
皮肤下有疆域
血液里奔跑着子民
他们追逐,从不隐藏我的影子
我存在。
一等于万物,有限归顺于无限
在神的宴席上
我见到了另一个我
他说,给你安宁的国度
但你要学会歌唱
生命当中的这一天
这一天,我变少了
仅有的微光挂在眼瞳里
我看见天底下的虚无之物
被装进各自的小盒子
它们弹跳,却逃不过命运的手
这一天,我如此谨慎
我躲进旧衣服,怀想坏天气时
那愈发明显的变形的尺寸
我已被更改,带着补丁似的眼神
这一天,我的生命
只露出几根线头,有人扯着
有人要一刀把它们剪断
我还将努力躲藏
朝时追随群鸟,落暮独依繁星
这一天,我偷偷活着
带着肉身承受的所有偏见
钟摆即将掉落,探访者无意敲门
牢笼
时钟有它自己的行程
墙角的壁灯也是
最美好的生活比离我们最近的苦难
还要靠近我们。坦白地说
距离仅是一道尚未到来的阴影
我们终将跨越它
像乡野的公牛,越过黎明前的屏障
——迎接它的
是那瞬间迸发出光亮的世界
有一天,我们终将走出自己的屋子
寻找那可以结伴上路的人
天地广阔
即便看上去是座牢笼
向往
春天的暗流无限伸展
我乐于抛弃毁坏的躯壳,我向往
民间艺人手中复活而来的
渺小的神灵
夏日有烈焰带来意外的安宁
我和农夫端坐葡萄架下
我向往,在那瞬间闪现的甜蜜的路径
秋光中的教堂谁也不可忽视
我举着薄雾一次次
路过,我向往那在祈祷中获得恩赐的事物
它们不露痕迹,却能彼此照耀
冬雪总是说来就来
我毫无准备,我向往另一颗心
飘摇世上,依旧透彻晶莹
叶落时节离别多
秋风凉了,叶子落了,那个女子
依旧站在树下,她看飞鸟
形单影孤,她看落日
那光芒已离心尖很远很远
秋日里,每一棵树都去了远方
心爱的人哪,未曾捎来讯息
风吹过的每一张脸孔
深深注视着,那日渐战栗的女子
秋风凉了,叶子落了
飞鸟不曾停留,落日薄如夜梦
只有眼里的这一湾泪水呵
蓄着,比那悬垂的光阴还沉
心爱的人哪,请留意途中的风景
那成片的野菊总在僻静处
绽放,而那清澈的流水
请勿窥视,那里有我不安的幽思
他们说到的归途
他们曾经猜测,流水有归途
大海没有,大海是
僧侣心中的最后一道钟声
他们接着猜测,葵花地里的光芒
流落何处?被吞食
而后像那从未有过黑暗的人
他们说到扑火的飞蛾
说到命运与他者交换的
一种仪式,他们说井里的青蛙
说开花的铁树,说到结局
他们指着愈燃愈短的
那炷青香,认真地低下头来
他们说到身体里的一个
黑洞,他们朝那儿喊
“有人吗……有人吗……”
但愿
多么美好的一个日子
我爱着的事物都能得到自己的
阳光。它们不说话,它们
要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
这个世界,把我分割了无数次
秀发是黑夜中的垂柳
明眸疑似晨露,而我的臂膀
现在已被恋爱中的白鹭所借用
那被人们遗忘的浅滩
只有它们,正一次次依偎
但愿这美好的瞬间已被大地所铭记
毫无私情,没有空缺
我要赞美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云是明朗的,风有小小的念想
风要抛开所有的秩序
而后把我的感应,带给那些
拥有共同心跳的事物
壁虎向上爬,铁树深夜里开花
河湾里的银鲫自由而傲慢
还有荒岛上奔跑的山羊
它们翘首雨季,等待草色下的乳汁
但愿这美好的瞬间
都因我而存在,不容许更替
也从不被阴影所覆盖
他们代表着大地的重量
幼稚园里有很多孩子,有国旗
有两棵植物,有正被模拟的简单游戏
我所熟悉的日子在他们眼里
是光线,是等待拼接的黑夜与白昼
人世间只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欢乐都长着繁密的枝桠,而悲伤
将从指缝间穿过,那跳跃的幸福的身影
我多怀念,他们代表着大地的重量
那些可爱的孩子,他们从未有过遮蔽
读书,写字,说话,唱歌
在这小小的幼稚园里,他们
仅仅服从于自己的身体
大地仍将沉默,它只想储存光亮
而我,我能听见幼稚园里一次次敲响的
钟声,孩子们奔跑在自己的路上
太阳多温暖,哪怕有阴影正蹒跚而来
请允许我……
请允许我用一代人的安宁来照顾
这个夜晚,请允许我接受
魔力,向天际里的星光存储每一缕呼吸
请允许我偷偷剪去
窗台的枯叶,还有那噩梦里
挥之不去的尖叫
请允许我得以分身,借以分享世间的祝福
2014,我的祖国和土地
像我一样谨慎,那挂在旷野里的花束
如此孤傲,如此惊艳
请允许我代替它们返回故乡
寻找亲人们迷恋的屋脊
2014,我的身体变得躁动不安
春风紧锁,而夜里的河流看不清去向
请允许我瞬间长出翅膀
从低处飞升到高空,而世界为此弯下腰来
2014,我所看到的每一个夜晚都是
多边形的,它有庞大的肋骨
越是仔细摸索,就越发觉得我的祖国
它是那么大、那么沉
为此,请允许我在今夜伸出手来
握一抹烛光,道一声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