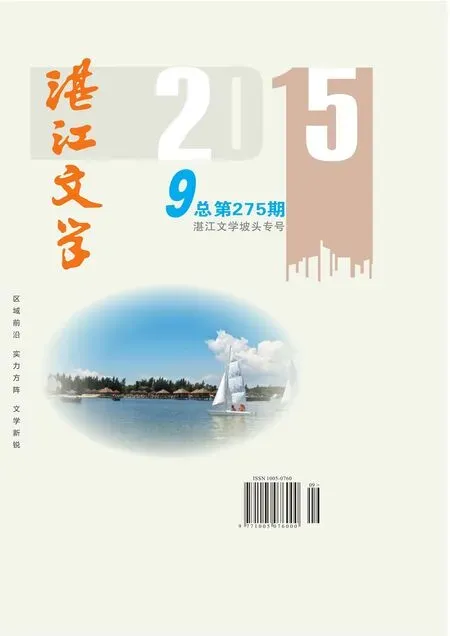牛 师
※ 陈华轩
牛 师
※ 陈华轩
我们这地方把做牛买卖的中介人叫“牛中”。可当面逢迎时又有新叫法,不叫“牛中”,称“牛师”。叫归叫,相牛这一行,真正当得起一个“师”字的能有几人?这“师”字真是一个很有斤两的字眼儿!
耕田人都说,我们这一带堪称“牛师”的,只有施乐。
施乐给人买牛百里挑一,他让买的牛准是好货。那时农村刚实行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牛成了农户家中之宝。当然一条好牛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耕田人选牛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工,二是种,要“工种两优”。就是说这牛不但要有力气,能干活,而且是条好母牛,或者将来是条好母牛。好母牛一年一仔,经济效益高。所以我们这一带很少有人养公牛,公牛容易打架,打起架来天昏地暗。为争做霸主,攻击情敌,总是打得死去活来,既误工又吓人,加上又不会产仔,谁也不愿养。所以我这里说的主要是母牛。好母牛工作效率高加上经济效益好,耕田人自然竖起两个大拇指叫好。施乐给相的牛每头都能叫耕田人竖起两个大拇指,所以耕田人信赖他,说他才是名副其实的“牛师”。
我家的牛不是牛师相来的,可是是一村人公认的好牛。它腿步有力犁地快,所以常常有人来借用。
那次二叔借我的牛犁田。说心里话,我不大愿意,可不借面子上又过不去。二叔犁田与别人不同。别人犁田是先把犁枷子校得正好,这样犁铧进土不深不浅正合适。犁起田来只要轻扶犁把,犁在泥中滑行就像船儿在水面风正帆悬般行驶,平稳而利索。耳边只听得草根、枯稻根咋咋的响,泥片飒飒的卷起,翻转,睡倒。驶牛人很悠然的跟着一步一步的踱,有些渴睡的还能朦朦胧胧的睡上半觉。可二叔不同,他驶起牛来,牛辛苦,人辛苦,犁也辛苦。他性急,脾气暴,想几下把田犁完。把犁上木枷子弄得深深的。那样犁铧吃土很深。然后把犁把扶偏,犁距就宽了。犁距宽了,田就犁完得快。本来四十个来回才能犁完的田,他要二十个来回就犁完。性急人就这样!可由于犁铧入土深,泥大块大块的立起来,翻不过身掉不下去,直抵着犁担杆。犁铧象铁锚一样越插越深,犁越拖越重,格格的响。牛绷直了脖,弓起了腰,两条前腿一颠一拐的走不稳,后腿用力的死撑,头高高地昂起,呼呼的喘着粗气,不停地打着响鼻。犁仍然一动不动。后面鞭子像雨点一样猛抽,牛死劲一撑,屎就一坨一坨的滚下来。那次二叔没把田犁完,却把木犁弄断了。木犁断了,我的牛就遭殃。二叔悻悻地卸下牛轭,捉住牛鼻圈。举起鞭子朝牛劈头盖脑一打,这样打了还不解恨,又把牛驱到一棵木麻黄树下,将牛绳圈起来抛过树杈,用力把绳往下拉,牛鼻给扯了起来,牛酸痛得绷直长脖。绳子还在继续往上升,牛只好举起前腿,最后踮起后脚,打着响鼻,眼泪沿着睫毛往下流,后蹄急急地刨着地面,很快刨出两个坑来。二叔跳起来折下一条树枝,连枝带叶举起就打。最后见牛屎滚尿撒,才骂骂咧咧的住了手。这些都是别人可怜我的牛偷偷告诉我的。那晚看着牛后腿、脊背一道道血痕,我的心难受得象堵着一团血。
让人更加惋惜的是,自那以后,我的牛就犯下了惊轭症-----每耕完地,刚卸轭,牛头突然昂起,牛眼暴突,一声响鼻,呼地冲出老远,险象横生。有一次轭还没卸下,牛带轭连犁往前蹿,我躲避不及,我的脚让犁铧撕起一块皮,鲜血直淌。
我说我的牛今番完了。这样的牛留着不是养着祸患?趁着牛的好名声还响坏名声还没有传出去,我得赶快把牛卖掉。
我对人说我想卖牛。
那天施乐带着个人看牛来了。我知道施乐相牛做中从来不欢迎“牛楔子”。所谓“牛楔子”就是指那些对牛略知一二,见有买卖交易,从旁搭讪帮腔,硬是插进场中趁机混几个中介钱的人。可是一到施乐做中,那些半桶水也轻易不敢凑热闹。施乐说人多了费用高,害了买卖双方;他从不搞“牛中”互串,在衫袖里互相捉手指玩手势暗中侃价,或者用“摸把”(中介人的暗语。“摸把”就是五个手指。暗指五十、五百或五千元)、“撇水”(中介人的暗语。由于“千”字第一笔是撇,所以多少撇水就是暗指多少千元。)之类的背语,先搞个“牛中”定价,然后支开买卖两方,两头分说,向买方把价钱要高,跟卖方把价钱说低。牛钱不是买方直接交给卖方,而是牛中这只手接钱那只手交钱,中间辗转,蒙骗双方,两头吃折,于中取利。施乐总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一是一二是二,买主卖主当面听着,愿者上钩。 更不妄说牛的“旋水”不祥,骗诱卖主,作贱牛的身价。从不因为牛身上长有“烂旋”、“孝索”、“幡竹尾”之类的怪旋怪毛而嫌弃一头好牛。不因瑕掩瑜,此所谓真识牛、爱牛者也。
见牛中是施乐,我心里先就蹿着个兔子。走近一看,买主竟是邻村张五。我的心就更加忐忑不安,“兔子不吃窝边草”,把这样的牛卖给熟人,我于心不忍,也怕惹人口非。等施乐带张五看过牛,回来试我的价,我故意把价钱吊得高高。有意让张五买不成。张五第三次还价时,我仍一口咬定,分文不少。
看看张五扳不倒我,施乐把他拉到一边,咕咕嘟嘟一阵,又带张五走过去,扳开牛嘴看看,摸了摸牛牙,说,“没错,牛还嫩着呢,刚‘四牙'”,张五把手伸进牛嘴摸摸,点点头。
施乐走到牛肚边蹲下,说“我说过了,这牛进食快。牛门齿齐粗,嘴扁,吃草准像镰割草,啃草管保不留丁点儿草茬;再看那肚仓,狮鼓一样浑圆,食量大。这种牛不挑食,鲜草干草照样能吃饱。冬天不会掉膘。养这种牛啊,工也省得多。”施乐招招手,张五蹲下来。施乐把手掌在牛奶子之间比了比,指着说:“自古说,好种出好苗,一看牛的体形便知八九。再看看,这几颗奶子如蒜葱笋一般,饱满浑圆,红润有光。奶间距离四指有余,‘福田广阔’啊,这种牛产崽后奶包大乳汁多。奶足了喂出来的牛仔粗壮,长得快。牛仔大得快也就离母快。因此母牛也就回头快(发情、怀孕快),这就是常说的‘仔牛离尾,母牛回头’。”张五微笑着点点头。
施乐站起来,张五也跟着站起来。施乐轻执牛绳,随意一撇,牛便信步前行。施乐轻“嗨”一声,牛即阔步疾走。再重喝一声,牛顿时腿急步紧起来。四蹄起落,有如龙舟赛手,运桨争先。蹄声踢踏,不啻鼓点。飞泥溅步,脚下生烟。给人一种奋进之感。施乐拉紧牛绳,走近牛,一拍牛屁股,牛一跃,一圈圈地绕着他们跑,脚下留下深深的蹄印。施乐指着蹄印,连说;“好牛,好牛!”。张五伸长了脖子。“看出门道没有?后脚印跨过前脚印。这种牛少见啊。相马人管这种马步叫“跨灶”,马是好马,牛是好牛。牛步跨距大,步幅宽,迈一步顶两步。牛蹄踮得又快,一晏耕个一亩八分地轻松着呢!刚才我那两声,牛什么反应?这种牛闻驱声而步快,见鞭影即奋蹄,让你舍不得打它。牛的眼神也有门道。这牛眼大明亮而神淳厚,像个厚道人,必定耐劳而诚实。有那么一种牛,看着身段也壮,四平八稳的,就是眼神诡异,老斜着白眼往后看。奸!你在后面喝声如雷,喊破喉咙,它就是不快。当你牛鞭一举,它就瞟见了,腰马上一陷,快走两步,躲过鞭子,又慢吞吞的走。说它怕鞭打,其实它耐打。有时鞭子突然啪的下去,猝不及防,它腰一陷,尾胯肌肉痉挛似的抖两抖,尾巴扫了扫,没事一样。依然慢吞吞,终是快不起来。真是骏马驴骡,一别天壤。”
回想施乐刚才讲的牛的四腿、脊背、屁股等体位之长处。张五都与昨天晚上看过的《相牛经》中“前尖后弓”、“龙关宽广”、“秋板壮阔”之类的话一一验证过。施乐讲的“福田广阔”牛经上虽然没有,可想想却大有道理。现在是实物在前,入眼即明,并且很多似乎早有灼见,张五顿时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快感。张五还要验证一下的是施乐讲的“跨灶”步。他要过牛绳,拉紧,照着牛屁股猛一拍,嘴里“嘿,嘿”的吆喝着牛。牛又一圈一圈地跑,张五盯着牛蹄印,两个眼珠子碌碌的转。
施乐不愧是“牛师”,牛的种种优点全让他言中了。只是牛近日落下的毛病,施乐一点也看不出来。我暗暗庆幸,在心口挂了半天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但也深感遗憾,为牛遗憾,为牛师遗憾:牛那毛病,恰如战士之临阵恐惧,医生之见血失魂,为官之利令智昏。那可是职业上的要命病根啊!
张五很得意地走近我,我知道他必有所言了。不过他没有说,而是朝地上狠狠的射了一口又黄又稠的口水。我知道他已下决心,而且心跳得厉害,要不吐出来的口水不会那么浓而冒泡。
我心里一阵发慌,不知所措。
果然不出所料,张五终于包价把牛买下。把钱交给我时,还一个劲的乐。我几次动动嘴,想让他驶牛放轭时提点神。但我即刻又打消了念头,生怕此次买卖不成,我的牛名声一传,永远卖不出去。所以我只有顺其自然,只有在心里暗暗祈祷:但愿他的好运气能改变牛的怪毛病!
可是不久有人跟我说,张五把牛卖了,并且暗地里跟人说,为那牛差点丢了性命。
我听了一阵内疚!
还有人说,施乐近来大病了一场。好起来后发狠誓:下半辈子不再为人相牛、买牛。
也许这些都是真的,因为那些专会讲“摸把”、“撇水”。最爱挑牛的“烂旋”、“孝索”、“幡竹尾”的“牛楔子”们,近日来四处游动,一个个都自立门户,自称“牛师”,为人买牛卖牛来了。
我想,相牛这一行,从此这“师”字少了好些分量了。
我对不起那位真正的牛师,是我毁了他的半世师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