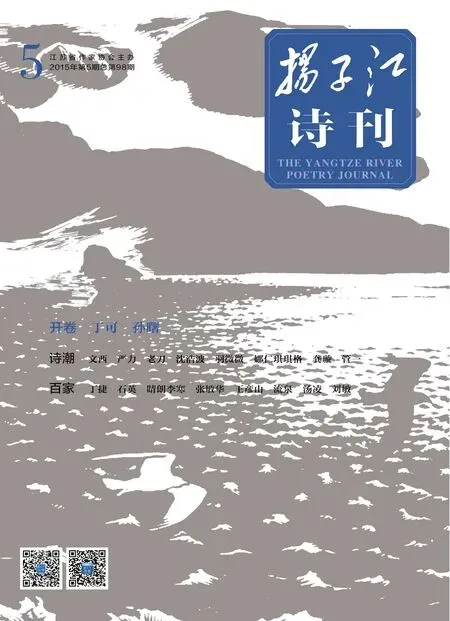湘西纪
文 西
湘西纪
文 西
一
逆流而上的人,你知道群山的源头
面黄肌瘦的巫鬼,你也有饥饿,会给
身体健壮的人送去饥饿
我们从不逃离,用火焰裹腹
然后不间断地在山顶打洞
在河口安装一只超级漏斗
以便坐在一旁观赏骨头是如何
与天体取得联系
而酒旗星的眼睛在我们准备入睡时
是怎样慢慢张开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敬畏,会下跪
当野鸡与蚌壳交欢发出尖叫的时候
当赶尸人不舍昼夜匆匆经过
你们把这些当作迷信,而我们当作天意
二
傩公傩母与我们互不相识
直到根茎穿过肚脐
肠胃里的粮食被牛羊舔食,所有人
才点头和解,用锄头深入土地
用斧头向森林求爱
每人都可以抓着一块瓦片
将它举过头顶。视力被闪电切除了
另一面回响着寂静
我们不得不为了同一个目的
重新经历一次骚动与喧嚣
最后一场雨在剔净鸟爪
植物的生长法则,像根须在地下乱爬
捕获腐骨、地龙,当仇恨当肥料
但你说话还得当心,所有的附属物
都善于把细节放大成灾难
三
獐子与麂在奔跑的时候画出漂亮的弧线
蛇、蚊子和蜘蛛,它们相拥在
枯黄的草根周围,神出鬼没
坚硬的粗纤维会自动脱落,成为石块的衣服
在一个废弃的巢穴总会聚集起温柔的物种
人们开荒,把传说安置下来
打猎,追随飘荡的白云
头顶着黑漆漆的罐子
在甲壳虫的振翅声中蹑足前行
夜里,举起松油火把
喂养黑暗
四
一到春天,泥土就开始柔软
水井满了,神就藏在倒影里
来挑水的阿哥与阿妹对上了眼
不用请客送礼,就手拉手钻进了树林
青蓝色的衣服是天,宽大的裙摆是地
天地之合传来野兽的呻吟
我听见马达在镇上压隧道,就联想到
男女之事,那个寡妇常常在门口张望
青年男子背井离乡,花影般的女孩也
日渐稀少,她们跑到远方成精
出嫁跨过火塘的女子,也想跨出门槛
大山已阻挡不了人们的视线
雾从圣书上跌进敞开的牙齿
五
无需借用超声波检测仪,你也能
听到死人常常与我们共进晚餐
还把汤匙弄得叮当作响
野兽与野菜已成为血肉的一部分
连石头下的根芽也会顽强地挣扎
一只芦笙与一只山歌交媾
一个民族的子宫不会衰老
时间不会衰老,肉体只是转化为泥土与空气
当蛀虫在视网膜上钻开裂缝
而漏进来的不只是光
六
我们在杂草与乱石中穿梭
路线比星系还要复杂
白天属我们的是一把锄头,夜里是一只电筒
一只黄蜂跟在一个人身后
像演技极好的搭档,灵魂
总会偷偷刺痛我们平淡的生命
吊脚楼里的女主人就成了
这儿最知名的相士与中医
她对一个婴儿说,他将来要死在海上
她告诉一个老人,他将寿终正寝
多孔的蜂巢在掌心转动
后来糖浆不再流了, 我们把这
称作绝经,随后在洞穴中掘好坟墓
把故事放进去,供后人祭奠
七
突如其来的风暴试图移动我们的地址
电话线吱嘎作响,企图让外界
用GPS定位系统找到我们
太多的愿望都会落空,因为你不能占有未来
虚惊过后我们与啁啾的野兔共同
赦免了自己
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赤裸着身子
与蛇一样对抗成长 ,尽管阿密妈妈
不再护佑,他的蜕皮却很顺利
后来虫蚁群体迁徙了,死人的关节
留在那里,被老鼠舐舔得发亮
没有人去收拾这副残局,但残局在我们
不在的时候已收拾妥当,又完好如初
八
今年没有落雪,这是有史以来
冬天第一次出差错
害虫没有被冻死,将在开春后蠢蠢欲动
那些麻木的面孔它们看起来
不像是恶人,也不像是善人
由于没能埋好警报线
鸟巢,田鼠洞,或是随便一个地方
你就得小心翼翼
这个时候全体居民会梦游
他们愉快地争吵,站在粮食上
比拼力气,然后继续争吵
九
石头被一阵虫鸣抬起
她在蚊帐上反复寻找一根针
她尝试把眼睛转向内部,那些老得
连猎狗都啃不动的贡品,在祭坛上沉默
它们一开始跟牙床一样柔软
她去水井打水,拿拖把清洗街道
但是开口之前先得模仿发音,然后
才能以同一种语言跟你对话
所以这么多年来她的耳朵变长了
结果是另一种听觉终于移植成功
十
酉水河畔没有生产出哲学家或诗人
连做生意的人也不使人放心
他们提着秤杆在大晴天里叫卖生命
而被电打过的鱼在网兜里苟延残喘
所以你可能会抱怨,怎么连一个
老实可靠的人都找不到
我们开始买汉人的时尚服装
把民族的色彩藏在衣柜里
也学习描眉画口红
乌鸦在树木上装腔作势叫唤
终有一天,这个地方将成为异乡
宗教也落满灰尘
这里只有探险家,并且一个老头儿说
大伙儿还宰过一头华南虎,把它钉在了河壁上
十一
在河对面的那座庵堂附近
教育局下令将狮子洞关闭了
这是尼姑们告的密,她们说早熟的
中学生在那里把衣服脱得精光
其实她们是要藏腊肉,青春很快就被风干了
我们不束缚四肢,任凭浆果裂开
一辈子还不是落土为安
把那些纠结放到风里让它们四海为家
但不放弃自己的身体,还要带走
鞋子与铁器,带走湘西的全部叮嘱
十二
尽管与你们的身体构造大同小异
但我们选择按照自己的方式
站立,坐着,躺下。平静的夜晚
陌生人请求住宿,我们答应的原因
是他上衣的第一个纽扣已经脱落
但他只能睡在天楼上
并且以我们另一面的姿势飞行
阿婆说这是规矩,谁都不敢改变
但是梦挨着梦,瓦片挨着天空
你要打扮就要坐上树枝,与花瓣为伍
不然那些小水晶坠落了,连同
我们的胎盘,牙齿,溃烂的前额,最后的头发
占卜师一直坐在群山下
目睹了这一切,包括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