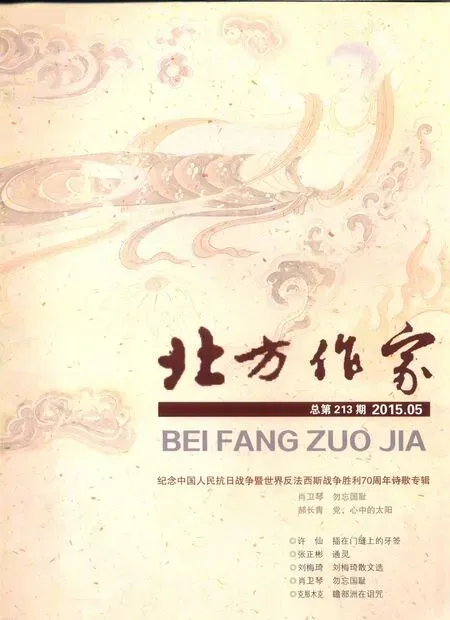插在门缝上的牙签
浙江杭州 许仙
小说
插在门缝上的牙签
浙江杭州 许仙
第四次中风的父亲被担架抬走后,我锁上他的房门。
我撕下一小块餐巾纸,蹲在门前,用牙签将它顶进门缝里。就插在距离地板十公分高的地方,把剩余部分齐门折断,捏在手里。我急忙锁上大门,下楼,爬上急救车。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迅速关上后门,急救车就呜咽起来,左一脚高右一脚低地离开杭钢南苑。
输上液的父亲直挺挺地躺着,两眼翻白。
我扶着担架,伸手想替他合上双眼。
但我最终没有这么做。我觉得这样做不吉利,好像他已经……
我发现半根牙签还在手心里,就悄悄地塞进裤袋里。
我是上完大夜班回家,发现父亲不在他床上,而是侧身倒在地板上;我帮他翻身仰天躺着,但他翻了白眼,怎么叫喊都没有反应。我打电话给哥。哥说他在上班。哥说他马上回来。哥说你叫急救车呀……但急救车来了,哥还没有到。请个假有这么难吗?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父亲送进杭钢医院,采取必要的措施后,医生就说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建议转院。我清楚他的意思,杭钢医院只是家企业职工医院,谁敢做这样的手术呀?我打电话给哥,问他在哪儿?他说他在路上。我说明情况,必须马上转“浙二”医院做手术。我问他到哪儿了?要不等他一起走?他就叫我先走,他说每分钟对父亲而言都至关重要。他说他马上赶过去,随后就到。
到了“浙二”医院。急诊室忙乱嘈杂,医生护士穿梭似地来回奔波,问这问那。父亲依旧昏迷不醒。我告诉医生,父亲二十年前患高血压;十年前因心肌梗塞第一次中风;五年前第二次中风;两年前第三次大中风,我们都以为他不行了,但他挺过来了,落下半身不遂……我话才说了一半,就被护士叫走了;她塞给我一张单子,叫我赶紧去交钱。
一切手术前的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我被叫到医生办公室。医生盯着朝窗外高举的CT片看,神色凝重。他冲我摇摇头。他说:“右脑大面积脑梗塞,左脑陈旧性血肿,右边又有新的出血点……”他说:“这个手术危险性极高。但保守疗法的话,恐怕就……”他忽然问我有兄弟姐妹吗?我说有个哥。他说给我们五分钟时间,商量一下要不要做?我打电话问哥到哪儿了?他说他在出租车上,应该快到了。我把医生的意思说了,问他做不做?他说你看呢?我说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他说那就做吧。
我在一张张单子上签名。
父亲被送入手术室。手术室的窗子突然打开,麻醉师探出头来叫我,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已经消毒好了,再给你讲一遍,病人状况很糟,中风多年,有心肌梗塞史,血压偏高,糖尿病等;这个手术需要全身麻醉,上了手术台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你需要考虑一下吗?”
我说:“做。”
手术室的窗子轻轻地关上了。
哥打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在手术室。他又问手术室在哪儿?我说了半天,他还是搞不灵清。他说你下来。我下去找他。我的天哪!他不就在楼下吗?他就不能直接上来吗?我又累又气,他当他是谁了?我没有叫他。他看看我,问爸怎么样?我生硬地质问他:“你怎么才来?”他脸一歪道:“上高架堵,下来也堵,你叫我飞过来?”他穿着绿色工作服和黄色劳保鞋,脚步笨重地跟在我身后。我们来到四楼手术室外。
他坐在走廊上靠墙的碗状塑料椅子上,拍拍双膝,问我爸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我回家时他已经倒在地上了。
我站在走廊上,两眼直盯着手术室的窗子。
一个小时后,一个白口罩单挂在左耳上的老医生出来说:“我们尽力了。”
我的脑子里瞬间贴上两个字:死了!
我回到家里,一屁股陷入客厅的沙发,胳膊肘撑着双腿,默默地盯着握在一起的双手;我低下头去,嘴里咬着并排在一起的大拇指的指甲。这一天,我想过很多次。自从父亲半瘫后,我就想,不知哪一天,它就来敲门了。但每次刚开始想,我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好像这样能够延缓它的到来。但现在,就是这一天了。怎么就是这一天了呢?
我腹中空空的,但不想吃东西,连水都不想喝;我脑袋昏沉沉的,却丝毫没有睡意。我靠在沙发上,闭上双眼,脑海里有什么东西不停地转动。父亲被送进了龙驹坞殡仪馆。他彻底太平了。他被推出来时,哥扑过去,一把揪住老医生,吓得推车的年轻医生拔腿就往里逃。老医生摘下左耳上的白口罩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我以为哥会搧他一个耳光什么的,但他没有,他连话都没有一句,就松开手,在走廊上转了个身,背对着父亲。
父亲躺在手推床上,白布蒙住了他的脸。
我还是躺到床上去吧。
我拆开握在一起的双手,按住大腿,艰难地支起身来。我走到自己房门口,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隔壁的房门。我和父亲的房间并排朝南,只隔了一堵墙。最早,父母住大房间,我们住小房间;哥结婚时,父母把大房间让给了他,他们住小房间,我睡客厅沙发。哥嫂搬出去后,他们又住大房间,我住小房间。母亲故世后,他依旧住大房间。我结婚时,他才把大房间让给我,自己住小房间。后来我离婚了,就没有再调过来。他一直盼着我能再婚,能给他生个孙子。
嫂子和我前妻,各生了个女儿,父亲就不要看这四个女人。
父亲让哥离婚。但哥对嫂子又爱又怕,他们就搬出去住了。
我离婚的部分原因也是父亲对我前妻的抱怨。
“没用的东西,”他天天骂,“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要她做什么?”“天天像只蝴蝶似的,我家只要苍蝇,不要蝴蝶。妈的,赶出去!”
父亲喜欢的是苍蝇的多子多孙。
我不恨父亲。我和前妻之间本身就矛盾重重,她有哪天是安心跟我过日子的?她和我离婚时,就没有向我要女儿的抚养费。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许我去探望女儿。我满口答应了。她骂我不是人。我说,不是人的人不是我,是那个背着老公跟别人勾搭的女人。
我走进自己房间前,先瞟了眼父亲房间。我瞟了一眼门缝,我愣住了。我单腿跪地,捡起地上的裹着半根牙签的餐巾纸。我试了试门,房门紧闭,它不可能自个儿掉的。我勃然大怒,“畜生!”我大夜班下来,饭没吃一口,眼没合一下,就赶死赶活地送父亲去医院;他们倒好,趁我不在,就跑来抢东西!我开门进去,在父亲床上翻了个遍。我知道父亲谁都提防,东西就压在他的枕头底下。但是没有。我连床垫都掀了,还是没有。
我把父亲房里翻了底朝天,就是不见那只木盒子。
我给哥打电话,我问他:“你还是人吗?”
“什么?”他假惺惺地问。
我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他又问:“什么?”
“操你妈的,”我大声吼道:“魏阳,难怪你老在路上;你咋就不敢明说呢?你在爸房里。”
哥又说:“什么?谁在爸房里?”
鬼才跟你绕弯子。
“不是你,就是嫂子!”我说,“我在外面忙死忙活,你们倒好,抢走了父亲的东西。”
我骂道:“你们还是人吗?”
“放屁!谁进父亲房间了?”哥说。
哥说:“你少来贼喊捉贼!”
我说:“哥,你就别装了,我做了记号,有人进去过,父亲的东西不见了。”
“啊……”
哥嫂是一起来的。他们就住在杭钢北苑,和杭钢南苑只隔了条半山路。他们明明有钥匙,却还来敲门,装什么吗?我打开门,说:“你们干吗不自己开门进来?”嫂子抱着冬花,她黑下脸来,咄咄逼人道:“哪来钥匙?你给的?”我也不客气道:“你就算了吧。”我说:“老爸尸骨未寒,你们就来抢……”嫂子未等我把话说完,就质问道:“你哪只贼乌珠看见我们来过了?啊?”
我戳戳自己心的位置说:“它看见了。”
我从父亲房门底下捡起东西,拿给他们看。我说:“你们没有想到吧?”我说:“出门时我插在这儿的,”我弯腰用手指敲敲那个位置,我说:“等我回家,它就掉在地上了。”哥从我手里接过东西,边琢磨着餐巾纸和半根牙签,边质问我:“你什么意思?”
我说:“就这个意思。”
哥朝我抖着他手里的东西。他与其说是抖着手里的东西,倒不如说他的双手在颤抖。他双眼血血红,怒气冲冲地问:“你怀疑我和你嫂子?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不是我怀疑你们,是事实如此。”我说。
哥继续抖着他手上的东西,问:“就凭这个?”
我说:“就凭这个。”
他说好呀,“就凭这个,你不再是我兄弟。”
嫂子说:“亲兄弟明算账。”
“既然嫂子这么说,”我说,“是该好好算算了。”
“哥应该很清楚,你有今天,是父母抛了多少本钱换来的?”我说,“你大我三岁,那三年里,你这个魏家的长子长孙,就占据了他们的心,你高中住校、一年高复班,四年大学,还有你结婚,你算过没有?父母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
“你不也读了高中,不也结了婚吗?”哥问。
我说:“我读的是什么屁高中?杭钢中学,就在家门口。”
“没有二十万,”我说,“至少也得十五六万吧?”
哥说:“那是你自己读不上去,又不是不给你读。”
……
哥是结婚生女后才失宠的。在我未出世的那三年里,他享尽了父母的宠爱;这份宠爱,一直延续到他做父亲为止。父亲对他期望很高,把光宗耀祖的重任寄托在他身上,也把家里的积蓄全抛在他身上;父母和学校老师都看好他。但他智商不高,他的埋头苦读,并不能提高他的智商,只不过在常规考试中,靠死记硬背得了高分而已;而像非常规的中考和高考,他就不行了。他没有考上重高,只考了个优高;在优高中,他自然又是好学生,但高考又不行,第一年刚上三本线;他还不自量力,非要再去读一年高复班,第二年也只是考上一般的二本。在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后,他进了钢厂,只是名上三班倒的技术员而已,和我有啥区别呀?但他好歹是我们魏家第一个大学生,至少给父母脸上贴了层薄金。不像我,普高毕业后,就进钢厂做工人。
父亲对他的失望,是他找了个同厂女工——也就是我后来的嫂子。
嫂子小个子,而且瘦,屁股尖削削的;父亲头一眼看到她,就眉头大皱。父亲认定她不是只下好蛋的母鸡。父亲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他要哥找个大屁股的女人。至少像母亲这样的。但哥是那种死读书的人,只认死理。父亲最后还是依了他,把自己住的大房间让出来做新房。但是,一年之后,嫂子生了女儿后,父亲就忍无可忍,非要哥跟嫂离婚。
嫂子到了预产期,住进杭钢医院时,母亲一天跑三趟;但她一生下女儿,母亲连个面都不露了。父亲不许她去。父亲对哥大失所望。父亲破口大骂,这个小土崽子,光宗耀祖是指望不上了,现在连传宗接代也完蛋了,那怎么行呢?父亲逼哥离婚,重新娶个大屁股女人。嫂子在月子里,哭了一场又一场;好在哥对她铁了心。说实话,我也挺同情哥嫂的,都什么年代了,生男生女有啥差别?
哥嫂不能在家里呆了。
他们到外面租了间房子,搬了出去。
在这点上,我支持他们。我叫哥嫂放心,家里有我呢。
说实话,我和哥从小就不和;但是哥嫂搬出去后,我和哥倒是比过去亲近多了。不管怎么说,哥还是挺有志气的,对爱情忠诚。虽然父亲从中作梗,但他们的小日子苦中有乐,俩人围着小宝宝,倒也是其乐融融。过了两年,厂里分给哥嫂一个小套福利房。他们有了自己的家,我替他们高兴;我帮他们装修新家,乐得忙进忙出。
我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不入调的儿子;但是,父亲把哥嫂赶走后,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当然,那也不是什么宏伟的理想,只是指望我能传承魏家的香火罢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找了个大屁股的女人,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她还不是跟嫂子一样,也生了个女儿。父亲又发作了,脸黑得跟个包公似的,我刚从医院回家,他就叫我离了。
我不离。我不做这个缺德的事情。
我说:“不是你说的吗?大屁股女人包生儿子。”
但父亲不认这个理,只认那个离。
他怎么闹我都瞒着她,我又要上班,又要去医院服侍她,累得要死要活。但是,她在医院里呆了七天,不见我母亲去一趟,就知道不对劲了。出院那天,我抱着女儿,和她一起回家。刚进门,父亲就暴跳如雷。她不比嫂子。嫂子只会关起门来哭,她才不管呢;她照样和父亲对骂,骂得不过瘾,俩人就打起来了。家里闹得天天鸡飞狗跳,永无宁日。
她大闹了三天,掸掸屁股回娘家去了。
哥摇摇手上的东西问:“你确定这东西不是风吹落的?”
我说:“绝对不可能。”
哥又问:“会不会是你前妻……”
我冷笑道:“她怎么知道爸今天会出事?家里没有人?”
嫂子说:“问你自己呀。”
嫂子说:“你跟爸住在一起,我们怎么知道东西不在你手上呢?”
“什么?”我说,“我会骗你们?”
嫂子说:“谁知道呢。”
哥的手还在抖,好像被刺了,甩不掉的痛。他说:“我想知道,爸到底丢了啥?”我顿时冷笑道:“你不知道吗?三只金戒指,十几块光头大洋,和八万多块钱的存单。”其实他和嫂子比谁都清楚。哥把东西放到桌上,问:“都不见了?”“我都找遍了,”我说,“不信,你们找吧。”
哥嫂进了父亲房间。
房间里一片狼藉,嫂子说:“你都找过了,还找个屁呀。”
我说:“你们再找找看,或许是我遗漏了。”
哥也是先从父亲床上找起,看来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可以说是沿着我找过的路线,又把父亲房间搜查了一遍,也没有新的发现。哥黑着脸,和嫂子一起退到客厅。哥再次捡起桌上的东西,又琢磨起来。他突然说:“这是你设的局吧?”
“什么意思?”我问。
哥说:“就这个意思。”
哥说:“你就想用这个玩意儿,私吞爸的东西?”
他又朝我抖抖手上的东西;好像它就是证据,铁证如山。
他反咬我一口。
这就是我哥。
我问:“要不要把我的房间也搜一遍?”
嫂子冷笑道:“就是把这套房子搜遍了,又有什么用呢?”
哥说:“爸没了,他的遗产我们各一半,这套房子你要住,也可以,按时价你出一半钱给我;当然,你不想住,我们就挂到中介去。另外,爸的那些东西,我也不想深究了,就照你刚才所说的,我们也各一半。你给钱也好,给东西也好,你自己看着办吧。”
“放屁!”我气极了。
……
自从我离婚后,父亲就说要把一切都给我,他叫我赶紧再找个女人,赶紧给他生个孙子。他当是什么了?去小菜场里买菜呀,随便你挑。再说,我也怕了,万一找个女人,还是生女儿呢?尽管父亲已经有过第二次中风,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如凶神恶煞一般。说实话,我怕他,我从小就怕他;我要顶个嘴,他手中有什么——碗啊瓶啊刀啊板啊——就毫不例外地砸到我头上。
我说我不要你的东西。
就这间破房子,值几个钱?再说,他这些年一直在闹病,家里能有什么积蓄呀?
“放屁!”父亲骂道。
他从他房里取出一只木盒子来,抓在手中,朝我摇摇;他打开盒子,取出几张银行存单,说有八九万块钱。我想不到他居然还能存下这么多钱。他又取出三只金戒指,十几块光头大洋。他说,还有房子。他说他会写一份遗书,只要我给他生个孙子,他就将一切都留给我。
我说:“你要存心给我的话,现在交给我保管吧。”
他说:“哪天我抱上孙子了,我就交给你。”
他说着,回进自己房里,关上门,把木盒子藏了起来。
父亲住的小房间,我住过二十年,我对房中的一切了如指掌;我从不担心,我会找不到这只木盒子。更何况父亲那时候已中风过两次,行动多有不便;尤其是他第三次大中风后,人已半瘫。你说他还能把东西藏到哪儿去?之前,我之所以没有找过它,是因为怕父亲发脾气;他是个没脑子的人,一发脾气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不想惹他不高兴,我也不怕拿不到它。
我没有要独吞它的意思。真的,我曾经告诉过哥,爸有这些东西。
但自从父亲半瘫之后,哥嫂就常来家里走动。
他们来一次,就被父亲骂出去一次。父亲虽然口齿不清,嘴角淌着口水,但那些恶毒的语言并没有因此而有损它的杀伤力。但凡父亲一开骂,嫂子就拉起哥走。他们愈败愈来,倒是让我起了疑心。我渐渐地明白他们的狼子野心了。
我那样子对他们,他们还这样防着我。这太伤我的心。这让我不得不想起小时候,哥要什么有什么,而我要什么没什么;我就是要支铅笔,也是哥用剩下的。至于字典什么的,都得跟哥借。而他去优高住校,读高复班,以及大学四年的费用,少说也有十五六万。他们在他身上所花的钱,足够抵得过父亲留给我的一切了。
我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他们呢?
后来,我也就留了这个心。
我说:“爸有遗书,房子和东西都是留给我的。”
嫂子说:“做梦!”
“那还说什么呢?”我说,“我们法庭上见。”
哥抖着他手上的东西,说:“报警。”
我说:“报警就报警。”
我伸手去摸裤袋里的手机,食指却被尖锐的东西刺了。
是那半根牙签。
我拔掉它时,食指上渗出一滴血来。
一滴有毒的鲜血。
许顺荣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4年生于杭州。现居杭州。在《江南》、《十月》、《北京文学》、《天涯》、《清明》、《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发表500万字。有作品入年度选本及排行榜。出版长篇小说《关于我漂亮母亲的一切》、短篇小说集《麻雀不是鸟》、小小说集《麻醉师酒吧》、《爱人树》、散文集《樱桃豌豆分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