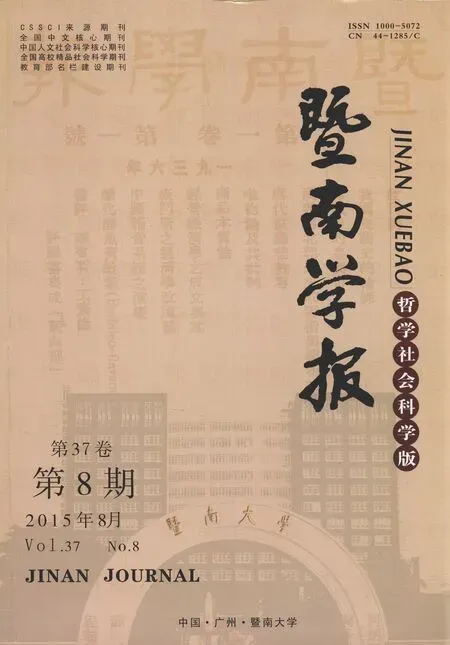诠释的策略与立场——理雅各《诗经》1871年译本研究
左 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19世纪苏格兰的新教传教士,西方著名汉学家。他倾注几十年心血,从1861年到1886年翻译并出版了“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其中,理氏《诗经》1871年译本是第一部也是至今在注释方面资料最齐备的一部《诗经》英语全译本。本文拟以该译本为中心,考察译文、译文注释与原文本意、历代解释在诗旨、礼仪制度、名物训诂等方面意义诠释的渊源与差异以及相关表达方式,以揭示理氏如何将《诗经》原文及历代解释重组和重构这样一个基础性的文本生成过程。
一、底本与资料来源
理氏1871年译本的正文体例为首列原文、次列译文、页下列注释。注释的篇幅远超译文,理氏解释说:“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丝毫不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在意;但是,可能会有第一百个读者,他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理注的主要资料来源,大致有三类:
(一)以《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为底本。1861年《中国经典》第一卷《论语·大学·中庸》出版,理雅各即认为《御制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礼记义疏》《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等经籍分别是《易》《书》《诗》《礼》《春秋》的最好版本。1871年《中国经典》第四卷《诗经》出版,理氏谈及《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我对它的评价与我在《中国经典》第三卷中对《钦定书经传说汇纂》的评价相同。”1865年,理氏曾在《中国经典》第三卷中盛赞《钦定书经传说汇纂》:“许多大学者都参与其中,该著共收录了从秦代至清代共计380家传注……览此一本,可知其他传注。这是勤奋向学、有意研究的标杆性著作——无论怎样称赞都不为过。”由此可见,理氏将《钦定诗经传说汇纂》视为最佳参考书目。另外,理氏称:“我经常参考《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礼记义疏》《钦定周礼义疏》《钦定仪礼义疏》。”说明“诸经传说汇纂”其他书目也是理氏翻译《诗经》时重要的参考文献。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是有关《诗集传》集大成性的权威资料,理氏重新按自定体例将《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另作编排,资料征引的情况不一:①全部引自《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的资料。理氏翻译《诗经》以朱熹《诗集传》为主要参考依据,在作法、诗旨和训诂上首重《诗集传》,再参考《毛传》《郑笺》和其他诸家之说。理氏大量袭用朱注,一般不再标明引自《诗集传》,力求注释文字简明。理氏译本的参考书目未列《诗集传》而特重《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所引朱注显然采自《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除朱熹外,理注所辑各家说解完全同于《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的还有李巡、王肃、杜预、陆机、葛洪、欧阳修、刘彝、王安石、苏辙、曹粹中、项安世、王质、吕祖谦、钱文子、范处义、罗原、段昌武、章甫、彭执中、李闳祖、黄震、王应麟、胡一桂、陈澔、许谦、辅广、朱公迁、李樗、刘瑾、朱善、黄佐、章潢、邓元锡、黄櫄、姚舜牧、顾起元、王志长、何楷、黄一正、朱道行、陈推、邹泉。此外,理氏译本颇采《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编者(“Theimperialeditors”“TheK‘ang-heeditors”)的按语。②部分引自《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的资料,包括《四书五经》《尔雅》《毛传》《郑笺》《毛诗注疏》《诗缉》。理注所引以上书目的资料与《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有较高契合度,但也有许多内容是《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中没有涉及的。③根据《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编译的资料,如《周南·樛木》“福履成之”,理注:“St.3.成 = 就,‘complete’.ThesongerswishthehappinessofT‘ae-sz,‘fromfirsttolast,formthesmallest thingstothegreatest’,tobecomplete.”《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释云:“《集传》:‘兴也。萦,旋。成,就也。’……〇顾氏起元曰:‘成,言自始至终,自大至小,其福无不成就。’”可见理注是在《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基础上编译而成,诸如此类,不烦枚举。粗略统计,采自《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的理注至少占总数的六成以上,据此判定《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为理氏1871年译本的底本。
(二)主要依据《毛诗注疏》进行补充。理氏译本之“参考书目”将《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列为第一种。《毛诗注疏》又名《毛诗正义》,四十卷,是唐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奉唐太宗诏所编的《五经正义》之一,该书全部保留《毛传》《郑笺》的注文,并给这些注文再做疏解,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并附有陆德明的《毛诗释文》。理注取材于《毛诗注疏》之《毛传》《郑笺》《孔疏》者尤多,陆德明的观点也有征引,在朱注基础上进一步详加解释,或补其略,或证其说,或补另说,或案断异说。凡于毛、朱义有异同,遂多左毛右朱,具体详后。
(三)辅以其他文献。理注还间有引及其他典籍,不及《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与《毛诗注疏》的什之一二。其中频率较高的有《尔雅》《说文解字》《四书五经》《韩诗外传》《诗序广义》《诗缉》《诗述闻》《诗所》《毛诗集释》等;频率较低的有《史记》《本草纲目》《毛诗六帖讲意》等。此外,理氏还述及西方汉学家的见解及翻译家的译文,皆可供参证,包括P.Lacharme,Julius Mohl,J.M.Callery,Sir John Francis Davis,A.Wylie Esq,Le Marquis D’Hervey Saint-Denys,Frederick Porter Smith,N.B.Dennys,C.J.Baron Bunsen,George Bentham等。
就理氏注释的性质而言,介于翻译与研究之间,旨在于众多解说之中择取允当的观点,故罕有发明。着重依赖者,在于收集文献要尽量全面。鉴于眼见有限,理氏1871年译本基本囿于《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及《毛诗注疏》的学术水平。清代是古文献学研究最为发达的时期,“诗经清学”发轫于康熙中期,大盛于乾嘉之际。然而,理氏1871年译本仅涉及毛奇龄、戴震、段玉裁、焦循四人,其他像被称为“清代诗经学三大名著”的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均未论及,不免令人遗憾。必须指出的是,作为最早的《诗经》英语全译本,理氏1871年译本以宗朱为本的清代官书《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为底本,参以汉学集大成的权威著作《毛诗注疏》,着眼点是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全面介绍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诗经》解释,所以具有牺牲新颖性以获取稳定性的特征。
二、诗旨:“以意逆志”与诠释合法性
对于《诗经》的意义诠释而言,题旨的解读至关重要。理氏专门在《中国经典》开篇题记中引《孟子·万章上》:“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此作为其翻译《中国经典》的宗旨。这段诗论是孟子与弟子咸丘蒙谈论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时所说,并非专门讨论解诗,但对后世文论和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氏的译文是:“...may not insist on one term so as to do violence to a sentence,nor on a sentence so as to do violence to the general scope.They must try with their thoughts tomeet that scope,and then we shall apprehend it.”也就是说,既不要拘泥于个别术语而误解句意,也不要拘泥句意而误解原作大意,努力以作者的想法去推测原作大意,这样才会领会原作。理氏明确提出:“可以说,只有作者对诗本身具有权威性,或者是他们同时代前后的可靠史料。”基于这一理念,理氏对《毛诗序》比附历史的解诗方法感到大惑不解,如《郑风·将仲子》,理氏释为:“女士恳求她的情人能让她独自安处,以免引起她父母及其他人的疑心和议论”,并指出这一解释取自朱熹;接着,下文详述《毛诗序》的“刺庄公”说,认为这是根据《左传》隐公元年的记载而附会出来的。对此,理氏评论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诗篇的运用要遵循将近200年后左氏所保存的方式,而使我们拒绝自然、简单地说明诗篇的唯一看法。”“然而,这首和其他诗篇所面临的困境在于,如何协调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字与毛公的解释。诗人们为了传达他们心中的想法,而必须使用离他们遥不可及、被指定好的语言。”在理氏看来,《毛诗序》的弊病在于其“远离原文的本意”“过度诠释”,“同样的困境发生在《毛诗序》其他诸多解释中,这使得诗义坠入谜团中,而我们被迫按照指定的答案去胡编乱造”。理氏对《毛诗序》严加分辨,参照相关史实对其附会之处逐一指出。
为了减少偏差和误读,理氏采取的诗旨诠释策略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以诗篇本意为本。鉴于历史久远,理氏已无法寻绎作者的创作初衷,只能追求诗篇客观内容所表达出的文本本意。忠实准确地传达诗的语言文字之中的客观内容,是理氏诠释诗旨的基本方法,如自称:“除了如我所述的从诗篇本身概括出的题旨外,再无别的东西”等等。第二,措辞简约而内涵丰富。最明显的例子是《郑风·扬之水》。对于这首诗,理氏认为《诗集传》《毛诗序》“这两种解释都存在理解困难,最好不要认可其中任何一种,而是将问题留给不明作者的意图”;他给出的解释是:“一方宣称忠于另一方,并抗议那些挑拨离间的人。”措辞既确知,又模糊,使得意义的客观性与开放性得到辩证统一。第三,保持客观中性的立场。一方面,理氏反对中国学者把诗歌与政教联系在一起,“诗歌的研究者和译者只能单纯地就诗论诗,无须对一些诗中的淫言秽行比另一些诗中的懿行嘉言更感到惊异”。另一方面,他又恪守译者本分,极力站在中性的立场上,抑制个人成见、好恶和民族倾向。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理氏对中国古代的妻妾制充满强烈反感,但是在注释中仍极力保持中性立场,较少掺杂自家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理氏对三百篇诗旨的诠释在突破中国经学的诗教传统上具有开拓意义。
关于《诗经》的意义诠释,并非任何解读都可以被民族文化所认同,需要经过社会、历史与信仰抉择并最终公认为权威的诠释才具有合法性定位。理氏为避免理解和解读诗旨的随意性,参阅、斟酌中国经学诸家见解,尽量择善而从之。在理氏看来,《诗集传》比《毛诗序》更自然,如《王风·君子于役》:“以上是朱熹的解释,甚至《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的编者都称许这一观点比《毛诗序》更加自然”等。理氏盛赞“朱熹在真正的批判性上远超前人,在这方面中国无人能够与之比肩”。“在我看来,大多数西方汉学家会同我一样友好地赞同朱熹的理论,就是必须就诗论诗,而不是接受那些并非从诗本身出发,将许多诗降格为荒唐谜语的解释。”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理氏解诗时主要依据朱熹的观点。可以说,理氏选择集朱学之大成的《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为底本,固然有借助其御制的特殊地位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朱熹的学术理念与其最为相近。
对于朱熹的解释,理氏并非全盘接受。在《周南》之《关雎》至《螽斯》5首诗袭用《诗集传》的“大姒”说,但《关雎》和《卷耳》篇末予以纠正,如“诗中并未提到文王和姒女士”;“我必须一并放弃大姒的观点”。事实上,大部分诗篇理氏对《诗集传》所论诗旨作了一些整饬工作。对于朱氏所定的21篇“淫诗”,理氏的说法与之类似但态度更为平实宽容。如《邶风·静女》释为:“绅士因一位女士没有赴约而深感失望,并且赞美她的礼物和美丽。”在谈到如何看待《王风·丘中有麻》时,理氏称:“我认为他(引者按:指孔子)不需要对这首诗感到恶心。”其实对《诗经》中是否存在“淫诗”,理氏与朱熹的见解迥异。孔子有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朱熹把“思无邪”看成是圣人对读者的道德要求,通过“惩创人之逸志”的作用,达到“得其性情之正”的目的。理氏理解的“思无邪”是孔子不带感情的事实陈述,“答案是圣人在介绍这首诗时,并未表现出指责时代邪恶之意,就像他记述《春秋》的那些史实一样,并不担心他的读者产生他们自己的看法”。对于朱氏无端指“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理氏并未像对《毛诗序》那样逐一辩驳,而是有意回护。例如,孔子的“郑声淫”是朱熹“淫诗说”的重要依据。理氏指出,《诗集传》中强调“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这是朱氏在解释《郑风》时反对《毛诗序》及尊《序》派解释的有力依据。也就是说,理氏看重的是朱熹借重孔子废《序》言《诗》,自成宗派的进步意义,至于“淫诗说”是否客观并未深究。
一方面,理氏发挥译者主体性,坚守自家判断,不轻易认可《毛诗序》;但另一方面对作为源语文化的权威诠释《毛诗序》仍保持充分尊重。虽然理氏解诗大抵采用朱熹的解释,但对于《毛诗序》的观点也多有所引述,甚至征引史料详加说明;即使批评《毛诗序》,语气也较为客观与克制。对此,理氏曾多次表白:“接下来会看到《毛诗序》被置于本章附录的第一部分,因为它被刊刻在中国每部自以为是的《诗经》版本中,并作为权威文献为大量学者所推崇。”“可以说,从诗篇语言来看,朱熹的解释在各个方面都是最自然的结论;然而他的观点被认为失之肤浅,而且我们发掘得越深就会发现支持毛说的越多。这里和别的地方我都努力去理解毛公和他的支持者们的研究;但是,通常来说,如果不是完全放弃个人判断的话,是不可能赞同他们的结论的。”“我们认为,《诗经》的传统解释是由毛公所作,这种解释是不容忽视的,且有史料的支撑,颇有助益。在诗篇中我们必须大力收集他们的诠释。”理氏以反《序》尊朱为主,可朱熹并不彻底废《序》,很多地方有意无意地因袭《毛诗序》。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理氏的态度比较小心谨慎,尽管《毛诗序》旧说仍无从考证,但一般不敢冒险抛弃权威解释,故姑且有限度地接受《毛诗序》说。如《大雅·云汉》《毛诗序》和《诗集传》皆认为是赞美周宣王的诗。理氏也采用此说,但补充道:“虽然第一句中提到一位天子,但宣王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诗中,所有的学者都接受《毛诗序》的说法,认为是仍叔赞美宣王——我们可以推测,这是周朝的一位大夫。”少数情况下,理氏的解释与《诗集传》《毛诗序》皆相左时也大都信而有征。如《卫风·芄兰》,理氏释为:“一个自大且有地位的青年”,这与《毛诗序》的“刺惠公”说、《诗集传》的“此诗不知所谓,不难强解”颇有不同,自称:“没有什么超出我从这两章语言中所推导出的题旨。”检阅《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便会发现黄佐、许谦已提出与理氏相同的说法,说明理氏并未脱离传统自立新说。所以,尽管理氏在恢复《诗经》本来面目上透露出一些新意,但整体上始终离不开传统诗经学话语的限制。
传统诗经学忽视“诗本义”而以解经为主流,《诗经》被解读为伦理教化文本、政治教化文本和历史文本。理氏推崇《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毛诗注疏》,但解诗中几乎不涉及对其中有关政治伦理、文化伦理的引申发挥。理氏多次表达过类似看法:“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很难从诗的字义之外发现其他什么。”另外,《诗经》之微言大义,主要不是直露激切的,而是用隐曲委婉的比兴手法来实现,此即儒家“温柔敦厚”之诗教。朱熹在《诗集传》中“分章系以赋比兴之名”,共标诗1141章,第一次对《诗经》中的章句作了全面标定。理氏仅是将《诗集传》每章所标赋、比、兴作法在篇首合项标示,至于其中寓意没有太多兴趣去分辨。如中国学者对《召南·野有死麕》的作法争论不休,而在理氏看来:“这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于比兴手法如此不以为然,很难说理氏对传统诗经学有深入研究。由于理氏1871年译本缺少对儒家义理的有效诠释,本身也就失去了经和经学的精神和生命活力。
三、训诂:“六经皆史”与诠释度
依循“以意逆志”的思路,理氏主张把《诗经》当史料来看,“《诗经》采集和保存是为了表彰德政和善行。这样做的好处是导致《诗经》为我们展现出国家政治和风俗之治乱盛衰的真实图景”。也就是说,《诗经》是保留着中国先人生活和思想信息的宝贵材料。理氏在《小雅·鼓钟》中说道:“我同意严粲的观点,经即史也;但这一观点不适于这首诗,因为其中未提到周幽王。”可见理氏赞同“六经皆史”的说法,但反对不顾诗义的恣意发挥。因此,理氏是站在史的立场审视《诗经》,称:“译者最大的困难是去确定他将要引入译文中的心境和时态。”理氏努力以体验的方式重构《诗经》产生的历史语境,把握其原初功用。强调《诗经》的史料性,故其解诗以考据训诂为根基。
理氏1871年译本关于训诂方面的注释数量最多,尤重于词义、句意的解释,兼及辨用字、明语法、显修辞、校勘文字等。理氏训诂仍以《诗集传》为主,参以《毛传》《郑笺》等。理氏大抵从《诗集传》中录出,一般不标明。遇《诗集传》与《毛传》完全歧异之处,经过比较分析,理氏基本依从朱说;同时也纠正《诗集传》的一些误释,皆必言之有据,如《大雅·文王》:“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诗集传》:“哉,语辞。”理注:“这句诗曾在《左传》和《国语》中引用,‘哉’皆为‘载’。毛公释‘哉’为‘载’,这比‘哉’的叹词的常用用法以及郑玄的‘始’更恰当。”《毛传》与《诗集传》相近之处,理氏不墨守一家,采取调和朱毛的策略,如《卫风·硕人》:“庶姜孽孽,庶士有朅。”《毛传》:“庶士,谓媵臣。”《诗集传》:“庶士,齐大夫送女者。”理注:“庶士是护送庄姜的官员,也是她从齐国来的随从。”《诗集传》存疑之处,多姑从毛说,如《邶风·静女》“彤管”等。偶有《诗集传》《毛传》皆不可取之处,转而引用别家解说。参酌西方翻译家、汉学家的释义也是理注的一大特色。如《周南·螽斯》,理氏参综“螽斯”的中西各家之说,无疑为《诗经》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理氏训诂不只编译前人的成果,因《诗经》中某些不言而喻的名物,西方人很可能无法理解,还要另辟新注。如《王风·黍离》:“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理注:“‘苍’指高远天空的蔚蓝色。‘苍天’被看作是天命的转喻,一种高居于天上的力量。”尽管理氏限于眼见较少参考明清学者的训诂成就,甚至以往汉学研究的合理见解也吸收不足,但其对所释义项,广泛地搜寻材料,每事必穷根源,所言必求依据,讲究旁参互证,反对空谈臆度,在知识层面上达到了当时西方译者所能达到的最具科学性的诠释。
由于译者视域与源语文化视域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因此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诠释度是忠实传达原词意义的重要环节。一般说来,在名物方面理氏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表达源语文化的语言信息和所隐含的文化内涵。除力求理解的客观性外,理氏还采用异化的手段,如对诗题、人名、地名、拟声词、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动植物往往采用音译法。而对于《诗经》中的重言式形容词则以注释代替翻译,如《卫风·有狐》:“有狐绥绥”译为“There is a fox,solitary and suspicious。”上述概念都是中国语言文化所独有的,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语,理氏坚持异化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诗经》作为中国经典的异域性,却也造成译文的质木无文。
理氏并非一味采用异化法而已,对于政治制度和信仰的术语则采用归化翻译法。中西政治制度和信仰的巨大差异以及系统化特性,致使此类术语翻译比一般名物翻译更加困难。政治制度概念上,为避免译文过分晦涩难懂,使西方读者保持阅读兴趣,理氏以西方的概念比附中国的概念,如将“诸侯”译为“feudal princes”;“这些诸侯国的国君分为公、侯、伯、子、男,为方便起见译作duke,marquis,earl,count or viscount,and baron,他们大部分是周王室姬氏的分支”。更重要的是,理氏在绪论中全面说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独特风貌,不致造成读者的误解。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科学且有效的翻译策略。信仰概念上,理氏把“帝”或“上帝”译为基督教的最高神“God”,并试图证明中国的宗教信仰与西方基督教信仰之间彼此暗合。如《大雅·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理释:“Illustriouswas the House of Chow,And the appointment of God came at the proper season.”又如《大雅·文王》,理注:“我将‘帝’与‘上帝’都译为‘God’。该术语中‘上’相当于定冠词。一个是希伯来语中的‘the Elohim’(引者按:希伯来文《圣经》中上帝的名字),另一个是‘the Ha-elohim’。”再如《大雅·大明》和《鲁颂·閟宫》的“上帝临女”一句,本意为“上帝亲自照临”,理氏则译为:“God iswith you”,直接以《圣经》比附《诗经》,极力夸大中西宗教信仰共同之处的存在性。对于中国人宗教观的看法,理氏主要受到法国汉学家毕瓯(M.Edouard Biot,1803—1850)的影响。他在绪论中附录毕瓯《从〈诗经〉看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文,其中指出:“《诗经》中的六首诗以不容否认的方式证明,中国人信仰一神教——上帝,最高的主。”紧接着,引《大雅·大明》《周颂·丰年》《大雅·皇矣》《商颂·玄鸟》《商颂·长发》证明商周的天子承上帝之命;引《大雅》“荡之什”,证明周朝无道,发生旱灾,周宣王称不再受到最高存在(the Supreme Being)——“上天”“天”,也就是“上帝”的眷顾。毕瓯又指出最近有许多传教士一再表示中国人并无明确的一神教信仰,理由是中国的卫道士倾向于说“天”而不是“上帝”。依据以上所引例证,毕瓯认为古代中国人更偏爱“上帝”,然后引《国语》《左传》的相关史料证明天子具有祭祀上帝的唯一合法权。毕瓯还断言:“诸神在上帝周围形成一个天上的等级系统,就像天子周围的众官。”并引《小雅·楚茨》《大雅·云汉》《大雅·卷阿》《小雅·伐木》《大雅·崧高》《周南·麟之趾》为证。关于中国是否有一神崇拜乃至神祇系统大可商榷,毕瓯以断章取义的论证方法得出结论,未免过于轻率。肩负传教使命的理氏抱定毕瓯的观点,翻译中存在过度诠释之处,将中国人信仰置于基督教诠释框架与神学信仰之下,力图借助基督教冲击、改造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从中不难见出19世纪中国典籍翻译者从传教士向职业汉学家过渡的历史印记。
综上所述,理氏1871年译本虽有失误,但是瑕不掩瑜,终不失为翔实严谨、客观中性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奠基之作,对于《诗经》的海外传播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