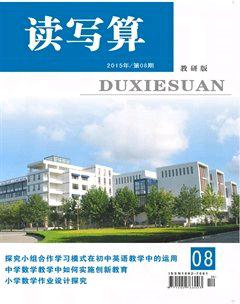“再见,语言”——从徐冰的纽约《凤凰》到戈达尔的戛纳“革命”
文‖陈亦水
2015年2月24日和25日两个晚上,徐冰在纽约的《凤凰》接连经历了两次完全不同的对话形式:“声音与影像:中国诗人对话徐冰”,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内举行小型主题研讨会;“凤凰于飞:5+5诵诗之夜”,十名中外诗人在圣约翰大教堂里朗诵诗歌。这部大型装置艺术作品,是在去年飞到纽约去的。艺术家以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读出的语言,在“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两个维度上,刺激着观看者的视觉神经。
也是在去年,戈达尔大师的《再见语言3D》,在几乎没有人能看得懂的情况下,获得了第6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面对这部“革了电影语言命”的电影,人们一时间表现出各种言说无力,于是纷纷通过历史性地回顾“戈达尔的革命一生”,从戈达尔与戛纳之间的“孽缘”为切入去获得意义。
戈达尔的银幕游戏《再见语言3D》,与徐冰的大型装置艺术《凤凰》在纽约的经历摆在一起,恰好隐现出一条关于“话语”问题的线索:今天,在语言极度匮乏的时代里,与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和社会进行对话,如何可能?
一、言说无力的悲哀
2014年5月,戈达尔和年仅25岁的加拿大青年导演泽维尔·多兰(《妈咪》),共同获得了戛纳评审团大奖。多兰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气氛十分热烈;相比之下,面对这部60年代“五月风暴”中的法国电影新浪潮旗手的作品,专业记者们竟然不知该对话。终于唯一打破尴尬的提问是:
“你今晚会把这个消息带给戈达尔吗?”
代替戈达尔出席戛纳的《再见》制片人阿兰·萨德回答:
“今晚不行,得明天,但我觉得他应该已经知道自己获奖了。”
——就这样,在如此客客气气的气氛中,戈达尔最后力作的公众对话结束了,整个过程加上翻译时间,不到一分半钟。
切换到《凤凰》,主流媒体关于它的言说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为艺术家的语言极易被读出:凤凰意象与构成凤凰意象的材料——抽象的腾飞与工业废料——观看者头顶上的悬挂与金属材料的沉重分量——也是可见的中国崛起与不可见的工业废料与它们的主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作品中所展示的实在界里“沉默的大多数”,便在某种程度上冒犯了活在符号界里的大多数。大部分的负评,都将徐冰作品中的工业废料——工人专属的“垃圾”,作为重点的攻击对象。而如果那不是工人阶级的“垃圾”,而是知识分子的眼镜、钢笔和书籍,是钞票、钱币和国旗——如果拼出的不是巨鸟,而是咬了一口的苹果,或者两个英文字母背靠背,符号界的公民会感觉好点么?
2015年2月24日和25日两个晚上,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圣约翰大教堂举行的诗人/歌对话活动,就变成比《凤凰》本身更有意思的“话语事件”。
无需详述对话徐冰的五位中国诗人,仅仅罗列北岛、翟永明、西川、欧阳江河、周瓒之名,即已将时间坐标,点在了那个语言极度饱满、言说能力无限强大的中国年代。第二天参与朗诵的西方诗人们,稍留心名单——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 l es Ber nst ein)、玛丽莲·尼尔森(Mar i l yn Nel son)、蔚雅风(Af aa M. Weaver)、白萱华(Mei-mei Berssenbr ugge)与埃尔·乔瑞斯(Pierr e Jor i s)——既有与中国诗人同时期的“语言哲学革命”领军人物,又有对中国诗人影响深远的诗歌翻译家——组织者或有意或无意地,令诗人/歌对话的形式,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匮乏。
但是,如果超越语言的言说方式生效了的话,那么更暴露了语言匮乏时代里,人们言说无力的悲哀。
二、曾经的言说饱满
1968年,戈达尔与“维尔托夫们”在第21届戛纳电影节上,聚在法国巴黎电影电影宫反对放映绍拉的作品,女主演杰拉丁·卓别林突然冲上台前,戈达尔误以为她要阻止“革命”,于是愤怒地将她推倒,场面陷入混乱……实际上杰拉丁是想把幕布扯下来,戈达尔则完全错误理解了她的肢体语言。
——任何言语都是有缺陷的、被限制的。无论是言语还是肢体,无论是银幕还是工业废料,这都并不妨碍当事人与那个年代的饱满:1968年,法国电影人掀起了“护朗运动”,西班牙电影人集体反抗弗朗哥政权,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人在现实中回应“布拉格之春”,纷纷在戛纳相遇,戈达尔、特吕弗、波兰斯基、阿伦雷奈等携上千民众,联手拒绝戛纳电影节的无视现实与冷漠政治,最终戴高乐执政时期下的第2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在“五月风暴”的革命声中取消。
电影的话语意义,永远溢于银幕以外。任何艺术的意义若仅局限于媒介,那么某种程度上,也就几乎丧失了意义。
在所有跨域话语实践中,语言的言说方式,都是极为重要的参照。纽约《凤凰》诗人/歌对话的两次文化事件主持人、哥大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刘禾教授在很多地方都有提到,诗人们迷人的语言,需要搁置在整个文化与历史语境下,去考察话语的有效性:北岛移居海外后虽名声大噪,仍一边“煮着咖啡”,一边写下“我对着镜子说中文”的诗句(乡音,1990);当初徐志摩站在剑桥大学建筑群里,写下了“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再别康桥,1928)的名篇,却无视同一时空内,英国社会的思想巨变与剑桥的一场又一场学生运动(The Nesbit Code, 2013)。将北岛和徐志摩的话语言说对比便可发现,北岛在说“中文”,徐志摩则不折不扣地在讲着“英文”。
——那么曾几何时,全中国人都在说“英文”了?
三、讲“英文”的全球时代
参考《凤凰》原本两个月的制作周期,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资金不足,而从2008年拖到2010才完成——这恰巧是极具坐标意义的年份:2008,世界金融危机正式在全球扩散的第一年,北京承办奥运会、向世界正式言说自己;2010,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难道不是在这个时间前后,中国大众文化“讲起了英文”了吗?
从未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时代里,话语的言说方式,如此高度统一。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话语在《凤凰》那里,被言说为工人阶级与中国崛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对话。《凤凰》所讲的“中文”,不仅是传统中文(凤凰的意象),还是社会主义使用的中文(工人阶级的主体)。她在白天和黑夜,呈现出两幅不同的样子:在白天,人们很容易认出凤凰的身体,是工业生产与城镇化进程中的废料——工人的专属品;而晚上,当装饰的灯光亮起,匆匆一瞥则很难看清其内在组成——唯有两只宏伟腾飞的凤凰。
如果当初进驻CBD玻璃城的命运兑现了,那么白天和黑夜的《凤凰》与资本消费中心之间,会产生怎样的话语效果呢?已有20世纪80年代诗作如是穿越言说:
——“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它的白天在事物的核心闪耀/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就像鸟在纯光中坚持了阴影/以黑暗方式收回光芒,然后奉献。”(玻璃工厂,欧阳江河,1987)
在24日晚的论坛中,哥大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约翰·雷奇曼教授敏感地发现,在座的中国艺术家诗人们,都拥有跨域创作的经验,例如北岛从美国到香港,徐冰来到纽约搞创作然后返回中国。徐冰的回答说,艺术深度在于艺术家如何处理与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自己正是目睹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国际化大都市的崛起,才有了《凤凰》,纽约则不会给他这种创作的需要。
——他恰好“来了”,“看见”,然后“说出”。
四、语言的字谜
今天,戛纳电影节需要戈达尔,因为她要在所有人都讲“英文”的时代里,宣布自己也接受这个讲“法文”的老男人,好看起来和讲美式“英语”的奥斯卡金人牛仔的区别更大些——尽管这个男人在1968年有过那样的行径。当然,戛纳也很现实地把同一个奖项,颁给了那个潜力无限的加拿大男孩。
虽然戈达尔曾以“回避电影节和死亡”为由不再出席戛纳,后者还是把奖项塞到大师怀里。戈达尔的拒绝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戛纳始终不懂他。不过要看懂《再见语言3D》,观看者必须至少具备以下三个素质:1.看3D版;2.懂法语;3.懂戈达尔。做到前两点不算太难,第三点,则成为只有戈达尔自己才能解开的语言的字谜。
其实,并非戛纳释怀了戈达尔与自己的那份“孽缘”,也不是评审团猜出了戈达尔的字谜,而是因为无人能获得戈达尔的话语意义。比如在2010年,戛纳就不可能让包含了阿兰·巴丢的广场演说情节、接过20世纪60年代反战接力棒的朋克教母现身的电影《电影社会主义》得奖——事实上这部作品都没有入围主竞赛单元。戛纳将这样的戈达尔放入“一种关注”之列,正如戈达尔在影片结尾赫然标明的态度:不予置评。
今天,戛纳把评审团大奖颁给了这样的戈达尔:由陌生演员和一条狗主演的、景深被无害的日常生活与大自然景观所填满的《再见语言3D》——戈达尔与戛纳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得以善终。
——请问,对于主流文化而言,还有什么,比接受一个失去对话可能的艺术品,更安全的吗?
一个所有可以随心所欲言说自己母语的乌托邦理想,如今编织进所有人都在说“英文”的世界现实之中。所以人们如何热烈欢迎3D电影《阿凡达》,也可以如何将反3D语言的《再见》,推向一个失去所有对话现实的神圣位置孤立起来——毕竟这已不再是戈达尔们闹革命的60年代,而是一个语言匮乏的时代。
五、“神啊,语言!”
戈达尔因此在语言的字谜游戏里,玩儿得很开心。法语标题“Adieu Au Langage”里,“Adieu”意思虽是“再见,告别”,但大师的哏在于,如果将“adieu”拆成“a”和“dieu”来看,“dieu”的意思是“God”(神),那么语言就变得复杂起来:1.字面意思是“神”;2.人们通常说“再见”时使用;3.人们表示吃惊时,也会用在短语“Mon dieu!”中,相当于“Oh my god!”。
如果我们笨拙地将三组意思连接起来,那么,“再见语言”的意思其实就转喻成了带有震惊语气的:“神啊,语言!”——“(a)dieu”从此成为一个神圣的迷。当人们终于肯承认自己看不懂,《再见语言3D》就被捧上了神坛宝座,“教皇”亦十分配合地闭口不言,默然接受着来自八方、语言匮乏的人们的朝拜。Mon dieu!
2月25日晚,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举行的中外十名诗人与《凤凰》的对话活动,使得作品在超越语言的言说中,意外地获得了新的话语意义。
组织者尽力地克服着言语的天生缺陷,比如配发每位听众一本英文翻译,因为大部分诗人们用母语朗诵。中外诗人亦相当尽责地,纷纷告别并超越着语言:比如北岛通过略带羞涩的表达,一如既往地一点点释放他内敛的狂热;圣约翰的驻校诗人玛丽莲·尼尔森,通过描述人们的痛苦,去想象某种新生的可能;西川放弃宣读印刷在翻译手册上的诗作,而选择现场用英语朗诵《开花》,在重感冒下拖着重重的鼻音,使得频频出现的“bloom/blooming”远远超过了其它词汇与语言结构;著名的语言派诗人(L=A=N=G=U=A=G=E)查尔斯·伯恩斯坦,自然不会放过如此“告别语言”的机会,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言说;再比如欧阳江河用川普天生的言语力道,言说徐冰如何掏空了“词的仓库”,让“黄金和废弃物一起飞翔”——中外诗人们运用新生、飞翔等一系列主题意象,似乎不约而同地试图建构某种新的可能,其话语意义,都是极其饱满、不曾有过的。
——难道我们只剩下超越语言的方式,来解决话语匮乏的问题了吗?
六、“再见,语言”
面对主流文化的语言匮乏,艺术家们的共同直觉是:再见,语言。
如果匮乏的语言不再能够有效地产生对话,如果层出不穷的新词汇、新技术,继续暴力地统治着人们的话语言说方式并无人反抗,那么也只好向语言告别。那么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戈达尔式的回答,需要沉默的“教皇”脚下的信徒们,自己某一天的顿悟才能获得。徐冰的《凤凰》,则将问题强有力地抛在了与读者的积极对话过程,但遗憾的是,主流话语因为语言之匮乏,人们同样对此言说无力。
这既是在圣约翰大教堂诗朗诵的无比“神性”之处,也暴露了时代的话语匮乏:技术革新与越来越发达大脑,逐渐被单向度的“英语”语言所统一起来。非英语世界的人们,不仅几乎丧失了母语,更缺乏对母语的言说能力。于是在语言匮乏时代里,任何所谓崇高或低俗、神奇或腐朽的作品都可以抛出,人们却对此言说无力,甚至拒绝解读它们的异质声音——也忘了这些所谓的异质声音,在那些特定的年份里,曾是何等地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