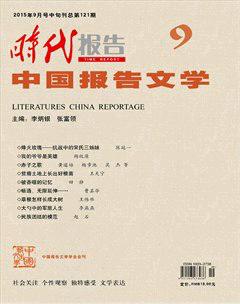被吞噬的记忆
田静


1
一个人,一生能写多少日记,又能忍受剜眼剖心之痛,毁掉多少日记?
在文学馆的展柜里,第一眼看到那个奇怪的小本儿,这个问题便开始对我纠缠不休。
小本儿是展开的,巴掌大小。
右侧,一张黑白照片,清晰可辨,赫然在目。卜兰夫,三十五岁,第二分所长,屈指可数的几个字,像镌刻着久远历史的碑文,证明着照片主人的身份。机关名称,宁晋县公署警察所;办理时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一日。
左侧,是详细的“手牒须知”。
所有信息,都清晰地透露出:这个在当时叫作“手牒”普通小本儿,俨然一个人的身份证。它的主人是宁晋县伪公署警察所第二分所所长卜兰夫,办理时间是1943年6月1日。
展柜里,它与徐光耀的书同在!
我疑惑地合上它,黑色的封皮,只字皆无。正因为如此,疑惑和好奇在我内心的碰撞就愈发激烈。
这个奇怪的小本儿,不起眼的外表下,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泛黄的纸上,“秉公守法”四个大字,沁入纸心,力透纸背。
翻到第七页,我才恍然大悟。
这一页,徐光耀写下了1944年1月1日的日记。
一页页泛黄的纸张,藕断丝连、不屈不挠地在线上挂着,每翻过一页,便抖落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翻到最后一页,整个小本儿完整地记录了徐光耀1944年1月1日到31日的那段经历。
卜兰夫的“手牒”办理时间是1943年6月1日,徐光耀却写下了1944年1月1日的日记。看来,卜兰夫的“手牒”还没捂热,就易了主。
这个奇怪的小本儿,历经南征北战、硝烟弥漫而得以幸存。望着它,我感触颇多:历史是无限放大,又是无限凝缩的,必定有一段历史凝结在这个奇怪的小本儿上。
1938年,13岁的徐光耀远离家乡河北雄县的段岗村,开始了四海为家的军旅生涯。
他的运气不错,一入部队,参加的就是正正规规的八路军。这支部队是由老红军改编的120师359旅特务营。之后,特务营脱离了120师建制,改属冀中军区,又相继与“冀中民军”合编为“民抗”,与“挺进支队”合编为警备旅。1939年冬,警备旅被调往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修的碉堡群。大获全胜后,警备旅又回到赞皇、井陉一带参加百团大战。警备旅此后便在冀中6分区(后改11分区)安家了。从那时到抗战胜利,徐光耀一直活动在石家庄至衡水段铁路两侧,跟那里的人民一起,共同渡过了一段血与火的残酷岁月。
小本儿成为徐光耀的战利品,是在1943年下半年的一次战斗中,战场就在石家庄至衡水段铁路的两侧。
参军二十余年的时间内,徐光耀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00多次炮火连天的战斗,在徐光耀的血液里流淌,就像爬满他脸上的皱纹,历历在目,清晰而深刻。
100多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不计其数,唯独这个小本儿,令他印象深刻。
缴获的战利品,其它东西,徐光耀毫不犹豫地交了公,甚至于今天想来,到底都有些什么东西,亦在他的记忆中烟消云散了。唯独这个小本儿,让他如获至宝,那一张张的空白页,让他垂涎三尺。战争年代,纸张实在太匮乏了,装订如此整齐、精致的小本儿,比获得二斤猪肉的概率都小,难度都大。徐光耀后来回忆,当年写日记最难的就是找纸和笔,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很多日记本,都是一张张纸订起来的。
思量再三,几经犹豫,他还是留下了这个小本儿,写下了1944年1月1日到31日的日记。
面对这个厚不盈寸、巴掌大小的黑色小本儿,我清晰地感到了它的重量与沧桑,厚重与沉静。那微微翘起的页脚,似乎急切地想要诉说一段神秘的传奇。
作为远离战争和灾难的青年一代,却意外地从战争中获益,且受益匪浅。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精神食粮,它们或者成为了文字落在纸上,或者凝固成影像,被一遍遍地演绎。神奇的是,较之于这些鲜活的启示,那些摆在文博类展馆内、侥幸从战火中逃生而幸存下来的物证,却偏生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致。我总是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它们,只有透过它们,才能更加真实地触摸到些许与那个年代相关的记忆。
在这本日记的一开始,徐光耀写道:从今天开始写日记,恰和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起写的日记相对照,那是我比较好的第二年,那次的日记也坚持得最为长久。回忆我孩提幼稚的日记,每天还在写买花生花了几毛呢,我亲爱的王司令员还曾耻笑过我这一点呢,那是第一次写日记……
由此得知,徐光耀的第一本日记是写在1940年,那一年是他所处环境稍好的第二年。
1938年,参军的第三天,他就随部队开始了长途跋涉。有一天,行军九十多里,最后十里,实在走不动了,他就抓着马尾巴,让马拖着走。可拖着也走不动了,就挤掉旁人,骑上了马。骑着马是舒服了,可到了目的地,下不来了,腿木木的胀得厉害,动弹不得,只好由人抱了下来。
1939年春天,梨花开放的时节,他被调到“民抗”锄奸科,当上了文书。
情况稍有好转,对文学的热爱和向往,就一下子重新蹦了出来。
说起写日记的初衷,徐光耀直言:从小就想搞写作,但那时对文学的理解比较朦胧,文化水平也不高,就想办法加强创作功底,写日记一方面记下自己的行动,一方面可以练笔,让自己的文字更加流畅。
从1940年开始,徐光耀救命的行军包中便多了一样他视如生命般珍爱的东西——日记本。它们换着颜色和大小、变着节奏和内容,却保留着初心,让徐光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找到了快乐和精神上自我倾诉的“舞台”。岁月在硝烟弥漫中萧然而去,唯独日记伴随他走过了形格势禁的日子……一直走到了今天。
他的日记,一写,就写了70余年。几百册,千万字,堪称活生生的史料,生命中的汤镬炼骨,写作中的哭笑癫痴、呕心沥血都从笔尖游走而出。
他挤占着每天临睡前的那一点点时间,有时伴着炮火轰鸣,一个字一个字,写下了战斗、生活中随时跳出来的人物、事件和场面。
一本本薄薄的小册子,全用牛皮纸包着封皮,每本都标明着起始时间、截止日期以及写作地点等。
这是徐光耀现存的第一本日记,却不是他写下的第一本日记。
2
1939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徐光耀在部队做了六年多锄奸工作。一开始当文书,凡送锄奸科的犯人,“第一审”都经他的手,都是他亲眼所见。
1940年7月,他被提拔为技术书记,并被选送去参加冀中军区举办的锄奸干部培训班,而此时的冀中军区早已转移到北岳山区。
月光笼罩,山峦起伏。他们一行人悄无声息地猫行在山间羊肠小道,欲北过正太线,进入北岳山区。半夜行至娘子关,临近石太线时,却突然惊动了日军的巡逻队,只得无功而返。又一个漆黑的夜晚,依然没有突破。
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曲线救国,改走东边,过平汉线。寂静的深夜,他们屏住呼吸,猫腰跳过铁路,一头扎进稠密的庄稼地里,躲过了日军的巡逻队。在敌占区,他们在敌人炮楼之间的缝隙中绕来绕去,有时刚要吃一口老百姓做好的热饭,忽地听到枪声,不得不仓皇而走。徐光耀的小说《望日莲》便由此段经历脱胎而来。
3个月后,培训结束,他和战友几经辗转返回部队。不久,他便被调到冀中警备旅第六分区锄奸科当干事。
六年多时间,他亲见了太多的血腥、背叛与死亡,他的日记中必定也有工作的影子。
1940年的第一本日记因此罹难的念头刚一兴起,马上就又被推翻了。
这期间写下的日记,消失的仅仅是1940年的第一本,其它日记都高枕无忧。
后来得知,那本日记中确实记载了很多当年绝对不可以曝光的事,比如他们怎样奉命去挖地道,怎样夜间运土、如何保密等等。
然而,1944年的日记可以确证:1940年的日记里,更多的是他孩提时幼稚的记忆,比如花一角钱买花生吃,比如和其他小八路拌嘴。13岁的徐光耀,一个月就一元钱,拿出一角钱买零食吃,要下很大的决心。现在看来不值一提,可当时他觉得都是“大事”。
他写下那些日记,无非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
这种执着,让我想起了在展厅内看到的另外一样东西:诗人钱丹辉的手稿本。
几张纸装订而成的简陋小本儿上,密密麻麻爬满了字。因年代久远,更因字迹过于纤细,我很难用肉眼看清楚,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我曾试图用放大镜放大,也只能看清很少的一部分。最终,我放弃了去看清上面的字,因为我已经实实在在看清了一位老诗人对文学的热爱,对创作的执着。在战争年代,在纸张极其匮乏的年代,他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写下了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
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无异于光明正大地“登堂入室”。当我揣着疑惑,数次“登堂入室”之后,终于发现:1940年的那本日记在战火中丢失了。徐光耀很多儿时幼稚美好的记忆也都被战火吞噬了。
那是他写下的第一本日记,也是他无奈毁掉的第一本日记。
旧的疑惑解开了,追寻中,我却无奈地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从1957年到文革结束,很多时间段的日记都是缺失的。
3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徐光耀这位经历了硝烟洗礼的战士,在今年迎来了他90岁的生辰。
一位老作家,几乎走过了一个世纪。他用手中的笔,记录了70余年的酸甜苦辣而从未间断。这些日记,已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记忆。它既是一个人的生命史,也是一个时代的投影。它属于一个人,更属于现当代史。
我试图通过现存的日记,寻找那一部分缺失的记忆,寻找日记被毁的初衷,甚至那曾经爬满纸面的横竖撇捺。
翻开一本日记,当年参军的豪情与哭笑不得一跃而出。
为了参军,徐光耀软磨硬泡,连哭了七天,把父亲的狠心磨软了,最终如愿以偿。
参军的第二天,发的军装又肥又大,可以装下两个他,引得大家嘻嘻哈哈围着他乱转。
……
又翻开一本日记,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场景历历在目。
1938年冬,日军第一次进犯肃宁城,他所在的特务团驻扎于此。战斗从清晨开始,由于大雾弥漫,部队遭到了重创。可撤退时,又幸而大雾茫茫,敌人的飞机在天上漫无目的的盘旋,像一只只无头苍蝇。炮弹四野乱落,第一次参加战斗的他就领略到了挨炮弹的滋味。也是这场真刀真枪的战斗,让他真正懂得:枪声一响,人命关天。
……
再翻开一本日记,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残酷与激烈鲜活起来。
当时,他正在冀中一支县游击队里工作,活动在石德路南的宁晋一带。环境越残酷,斗争越激烈,出现的英雄事迹也就越多,王家堡战斗、护驾池伏击、双井村突围、朱家庄喋血……
战火间隙,大家围坐地洞里闲谈,常常说:抗战胜利后,再想想今天的斗争,不定多么有意思哩!
偶尔也有人说:如果有人把这些编成书,实在太好了。
可在当时,那些都是多么遥远的奢望,一个闪念也就过了……
人们随口而说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就在当年的那个闪念里,镌刻在徐光耀的一本本日记里。
翻开日记,那些战友就活生生地立在字里行间。那些事件和场面,时常零零星星地跳到眼前来,感动他。
1946年,冀中发起过一次“抗战八年写作运动”,号召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写写在八年抗战中最感动的事迹。他想念着战友们,写下了《斗争中成长壮大》,写一支游击队在大扫荡中,如何由失败、退却,经过整顿和斗争又成长起来走向胜利的。
1947年,他有机会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去学习了八个月,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朦朦胧胧觉得:表现五一大扫荡那段斗争的责任,不一定非指望别人不可,他也应该担负一下。
他所受的感动越来越强烈,日记也就越写越多。
他兴奋地把这些随时跳出来的人物、事件、场面,都捉住塞进日记里。
《平原烈火》就诞生在这些日记里。
慢慢地,原本互无关联的事件,也逐渐联系起来,原本分散片断的人物,也有的合并了,一些独立单个的场面,也连接扩大起来。逐渐的,人物由模糊趋于明确。周铁汉由一个名叫侯松波的战斗英雄作模特儿,加上程等的材料,钱万里由宁晋县大队副的模样作原型,再换上另一位参谋长的“深嵌在眼窝里的黑眼睛”等等,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形象便逐渐鲜明起来……
1949年7月,徐光耀所在的部队转入和平练兵环境,他也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安静,于是动了笔。故事的梗概就大致按“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发展顺序进行了扩充。书中的人物,凡是当干部的和侦查员、通讯员们,几乎都有一个真实的人做模特儿。
怀着对先烈的缅怀,那些与他最亲密、最熟悉的逝者,都在他的心里复活了,那些黄泉白骨,又重新幻化出往日的音容笑貌,《平原烈火》中有很多篇页就是那些战斗英雄们,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
每当翻开那些日记,硝烟弥漫的战场便在眼前重现;每当翻开那些日记,战友们便从字里行间立了起来。
没有找到被毁日记的线索,我却有了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发现:原来《平原烈火》和“嘎子”就诞生在这些日记里。
4
关于“嘎子”的原型,徐光耀始终坚持说过两句话:凡是在白洋淀或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寇作过英勇奋战并有一定贡献的人,都可在“张嘎”身上找见自己的影子;“张嘎”是个艺术创造的产儿,是集众人之特长的典型形象。
徐光耀13岁参军,与“嘎子”同庚。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多读者都以为他便是那个电影里调皮捣蛋、坏水横溢的“嘎子”。
对此,徐光耀却一口否定,说自己小时候是个很老实、刻板、听话、循规蹈矩的孩子,于是很羡慕“嘎子”的性格,但自己又变不成“嘎子”,于是就很喜欢和“嘎子”性格的孩子交朋友,在身边的十三四岁的小八路和乡亲家孩子里挑挑拣拣地找“嘎子”,他的脑海里就慢慢地积累了很多的“嘎人嘎事”。
如果非要追究“嘎子”的来历,就要说到《平原烈火》里的“瞪眼虎”。
“瞪眼虎”实有其人,原是赵县大队的一个小侦查员,他还有个伙伴外号叫“希特勒”,创造了很多诡异的故事。“瞪眼虎”倒挎马枪、斜翘帽沿的逼人野气和泼辣风姿,就来自那个小侦查员,事迹则源于很多如“希特勒”一般的小战士。“瞪眼虎”由于出场晚,为避免与主角争戏,刚开了个头儿,还没展示才智本领,就随大流谢幕了。
他一直感到遗憾。当创作“嘎子”的念头一萌生,“瞪眼虎”就第一个跳了出来。
这些嘎人嘎事,都在徐光耀的日记里。从这个角度而言,“嘎子”就诞生在日记里。
徐光耀塑造了“嘎子”,“嘎子”同时也赋予了他新生。
1957年的一天,徐光耀被正式“点名”了,让他准备在第二天的会上,检查交代。
徐光耀说:这一日,真是我生命史上下地狱的一天啊!
那一夜,他通宵未眠,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明白”是因为明确告诉他,他有“言论”,之前也被“点”过两次名。
“糊涂”就彻底糊涂了:我13岁当兵,当年入党,20年没有离开过党的怀抱,怎么,我要“反党”?即使做梦也做不成这样的噩梦!把党反倒,哪还有我的站脚之地?莫非我要自己打倒自己?再说,我给“丁陈”干了什么了?如此彻底地翻检,又有什么上得“纲线”的东西?老天发疯了……
“明白”和“糊涂”捉对儿厮杀,通宵达旦。
他一生有过无数次的思想斗争,唯有这次最为痛苦、激烈。坚持写了70余年的日记,他记得很多日子,甚至记得13岁时花一角钱买花生的事情……
可他却唯独忘记了这令他最痛苦的一天。
被“点名”之后,他开始了一个相当长的挨斗过程:历史、现行、亲朋战友、祖宗三代、无不层层搜剥,翻检净尽。开了数不清的会,写了几大摞“检查”,最后“斗透”、“斗熟”,“挂”了起来。
自从被“挂起来”后,他便无工作,无任务,无会可开,无文件可学,大门不能出,亲友不能访,精力闲置,四顾无靠,日日枯坐愁城,简直度日如年。
自从13岁参军以来,日日奔波,整日闲着的日子几乎没有。何况当时30出头的他,恰是风华正茂的少校,哪里受得了如此的清清净净。
煎熬了半年,他便猛然变得暴躁乖张,迥异寻常,仿佛成了一颗炸弹,不知几时便会“崩”的一声,炸成粉尘。
有一天,他刚满周岁的小女儿,蹒跚着跑到他的跟前,央求抱她玩耍,他却突然怒火丛生,大吼一声,把女儿吓跑了。当看着女儿跌跌撞撞狼狈奔逃的背影时,他的心却陡地一沉,把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这是怎么了?
想到精神分裂的可能,他真的害怕了。假如真的成了和疯子一样的废物,真比死掉还要坏上万分!
生死关头,他记起了《心理学》上的两句话。大意是说,在精神分裂出现苗头时,必须自我控制,而控制之法可以归纳为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反复掂量过后,他觉得最切实的“集中精力”,莫过于写作。可这个念头刚一兴起,他又犹豫了,想想自己的现状,生活下去都难,还要写作,岂非异想天开!
他试着读书,完全读不下去;试着看影戏,人在心不在;试着遛大街、逛商店,完全没心情……
又憋了两天,忽然茅塞顿开:如此闲暇,如此安静,有大块光阴,绝无人干扰,以往求之不得的条件,而今全到眼前,谁阻挡你写作了?你不写,只怪自己太脆弱、没出息罢了!
想通了这一点,他如醍醐灌顶一般,精神也为之一振。
写作的念头一起,《平原烈火》里13岁的“瞪眼虎”,那个他一直惦念的野气逼人、调皮泼辣的小英雄,便马上跳到他的眼前。
“瞪眼虎”一出来,后面又跟来往日英豪、少小伙伴,一队人马。此时,那些往日积累的嘎人嘎事也一并跳了出来。
为了给这跳跃的一群人一个优美轻快的环境,他又特地把故事背景选在了风光旖旎的白洋淀。就这样,徐光耀于1958年1月23日,开始了《小兵张嘎》的写作。
为了节省体力,一开始,他选择写电影剧本,认为剧本只讲究对话,故事架子一搭起来,叙述性文字能看懂就行,相对省力。可剧本写到一半,就遇到了无法突破的“拦路虎”,写到嘎子被关禁闭、受教育时,思路嘎然而止。思量再三,他把剧本搁置,重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小说。
小说写得很快,他也跟换了个人一样。得意时,甚至手舞足蹈,向着想象的敌人“冲锋”,完全忘了自己是个“待决之囚”。
创作的顺利程度出乎他的意料,一个月内,即完成。经过一番嘎人嘎事的塑造,顽皮可爱、侠义智慧的小英雄嘎子活脱脱地站在了人们面前,为革命战争文学增添了一个独特的不朽典型。随后,电影剧本也按照小说的路子,痛斩“拦路虎”,又半个月后,剧本也顺利完成了。
“嘎子”稳稳当当站在了纸面上,徐光耀的“集中精力”法取得了实效,他摩拳擦掌,兴致勃勃地准备再写一部长篇。不巧,“军法判决书”下来了,他彻底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双开除”后,立即发往保定农场劳动改造。另一长篇,只能作罢。
直到1961年,《小兵张嘎》小说才得以发表,说起来还有件轶闻。
1961年,《河北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张庆田到保定组稿,对徐光耀说,你给我们写一篇小说吧。徐光耀说,我给你稿子敢发吗?张说,你只要敢给,我就敢发。徐光耀这才把《小兵张嘎》的手稿交给了张庆田。
按常规,一篇三四万字的中篇小说,应该分两期刊出。尽管此时,徐光耀已经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摘帽右派的稿子能不能发,上级还没有明确规定,编辑部怕发出一半,上边万一卡住不让再发怎么办?最后决定,干脆把两期合成一期,用出合刊的方式一次发出。《小兵张嘎》就发表在了《河北文学》1961年的第11期和12期合刊上。没想到,一经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62年又发行了单行本。
单行本一发,徐光耀的胆子大了起来,他把电影本子也拿了出来,寄给了曾给他当过创作组长的崔嵬,电影《小兵张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63年拍摄完成。
小说《小兵张嘎》发行至今已逾百万册,曾被译成英、德、泰、阿拉伯、印地、蒙、朝、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影片自发行以来,几乎每年都放映,尤其每年的“六一”前后,总能见到“嘎子”的面孔,这个小英雄的形象已深入千家万户。1980年,在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评奖会上,小说和电影双获一等奖。
一个作家最大的愿望和最高的荣誉就是作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历久而常新。
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徐光耀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许多老作家在完成了对革命战争的回忆和书写后,基本上就停笔了。他却依然精进不止,把此前作品的时代主题、革命战争主题,真正转移到以人为本的主题上来。
在一处农民废弃的小屋里,他自己担水、烧火、做饭,远离闹市,潜心完成了晚年最重要的写作。2000年1月,他用《昨夜西风凋碧树》做了一次坦诚的、明心见性的倾诉。这部作品作为一份历史的证言,成为当代思想史的一份珍贵记忆,在文学价值之外,更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而这一作品,依然可以在他的日记中找到创作的根源。
5
近些年,徐光耀很少写日记了,书法却日臻成熟。
深厚的文学底蕴,给他的书法作品注入了精、气、神。他的书法作品书写的大多是他的原创,浑然天成而毫无雕琢之气,既含雅韵,又存豪情。刚劲有力、朴实大气,于笔墨之间透出性情的刚直清正,与其行文的质朴刚硬相得益彰。
2015年3月份,我随电视台的摄像去拍摄纪录片。刚叩开门时,阿姨一边示意我们进屋,一边做出“噤声”的动作。我们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迈进屋里。
徐光耀正在客厅的一角挥毫泼墨,神情专注。全部声响都凝于笔尖的游走,止于宣纸的墨迹。直到盖下最后一枚章,他才长舒一口气,热情地招呼我们:“你们来啦,我担心一会儿架着摄像机会紧张,一紧张,手就抖,会写不好,所以就先写一幅练练手,一会儿再拍写字的镜头,就不那么紧张了。”
说完,呵呵地笑着。
凝滞的空气,一下子舒缓流动开来。年已九旬的徐光耀,竟愈发幽默起来。他大大方方地诉说着自己面对镜头时可能会出现的紧张情绪,丝毫不叫人轻视,反倒心生敬意。
摄像师架好机器设备,拍摄他写字的场景。他站在摄像机前,神态自若,并未出现之前担心的紧张状态,一行字刚写完,他就开心地说:“果然有用,这幅字比刚才那幅还好,这摄像机架着,你们在一边儿看着,嘿,我还来精神了!”
果然,余下的一气呵成,笔力苍劲。认真观察了一会儿,他又信心十足地说:“嗯,这幅真的要比上一幅还好些。”
我们都笑了。
他的书法,遒劲有力、刚健质朴,完全看不出书写之人已有九十高龄。
谈到练习书法的初衷,他坦言,本是为了修身养性和强身健体。如同写日记一般日日坚持,时至今日,仍要每天坚持练字一个小时。多年下来,身体居然健朗了许多。
只要天气晴朗,他每天都会固定地抽出一些时间,走出屋子,去楼下的公园里散散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这位九十岁的老人,腰板挺直、步态稳健。
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地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他一个人坐在屋里,面对着那一大摞日记本,内心深处进行了怎样的痛苦交战。但是,多年过去了,2015年初春的那个上午,老人戴着墨镜,拄着拐杖,在阳光沐浴下悠然而行的身姿,让我坚信他对很多事情已然释怀。
老人的背影,让我想起了马蒂斯的一张照片。当更多的人把马蒂斯和毕加索同称为现代艺术的源头时,我却更加心仪于八十三岁的他,坐在画室的轮椅上,光着脚,专心剪剪纸的专注与安详,感动于他对生活不倦的喜悦和爱,感动于他迷恋创造的那片童贞。
又想起徐光耀在1944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吹口琴,学会东渡黄河舞谱子……
我的眼前瞬间就闪出那样一幅画面:月光清寒,轰鸣的炮声似有若无,19岁的少年坐在营地前,一曲激昂的旋律缓缓流动,火光映红了遥远的天边,少年的眼睛清亮如水……
时光荏苒,望着面前堆叠如山的日记本,那双满含纠结痛苦的眼睛,却明亮如昔。
望着那一摞早期的日记,他的心里还是较为放心的。
那一摞日记里,记录着他参军的激情和斗志,记录着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惨烈绝伦,记录着战士们用鲜血创造的壮烈事迹……
他在心里默默地合计着:这些日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缓缓的,他的目光又扫过另外一大摞日记本。
那里面记着解放战争,记着建国后到1957年上半年之前,供应充足,物价稳定,各条战线欣欣向荣,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党的号令四海风……记着朝鲜战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吐气扬眉……这些大概也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可看着另一摞日记,他开始感觉到了强烈的不安。
那些日记里,有“鸣放”的始末;有“鸣放”后期,他被通知去给陈沂部长提意见,居然有些兴奋当面给部长提意见的机会实在是难得,于是实实在在列了好几条;当然,还有他忘记的被“点名”的时间,被“点名”后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会议……
他越琢磨,越觉得那些日记是“有问题”的。“文革”期间,他只得忍着剜眼剖心之痛,把那一大摞“有问题”的日记偷偷销毁了。
最简单,最原始,也最彻底的方式:付之一炬。
被吞噬的,不仅仅是日记。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