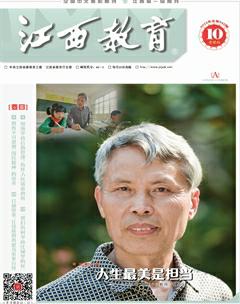邂逅
王淦生
2002年初夏,高考刚刚结束。我所供职的学校为了犒劳没日没夜地“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高三老师,为我们组织了一趟“三峡告别游”——让我们最后看一眼传说中的长江三峡的原貌。
在长江南岸,我看到了一座被毁弃的小城——云阳。这是一座需要整体搬迁的县城。一座风光旖旎的江滨小城,已变成断垣残壁。其实不光是县城,一些著名的文化遗存——如始建于蜀汉末年、有1700余年历史的张飞庙,亦要整体搬迁到30公里之外。
当然,更为搬迁纠结的应当还是那些库区的移民。一个小小的云阳县,需要搬迁的就达数十万人。而在这当中,相当一部分人需要远离故土,背井离乡,到其他省份另谋生路。譬如我所在的苏北盐城,位于地旷人稀的海滨滩涂的乡镇,就接纳了近万名三峡移民。
我没有接触过三峡移民,但是我能想象出他们背井离乡的痛楚。当他们离开故园的那一瞬,一定会经受一种一棵树被连根拔起的剧痛——虽然树根被拔出了泥土,但那丝丝缕缕的根须依然留存在土中。而他们必须斩断自己与故土除了情感之外的一丝一缕的联系,背起行囊,投向一片陌生的土地。前程是明是暗,未来是祸是福,一切就像是一场赌局。
十多年过去了,关于“三峡移民”的话题已愈来愈少,各种媒体上也已很少见到与此相关的新闻。“没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但愿没有新闻的背后,是他们生活的安好。
数日之前,我平生第一次邂逅了一位三峡移民——准确地说,应当是“移民二代”。她是今年中考期间与我分在同一考场监考的一位稚气未脱的年轻老师。小姑娘文静,严谨,敬业,字与人一样清秀。在不多的交流中,我得知她是最早的一批三峡移民,老家在云阳,来江苏时刚小学毕业。她在乡镇读完初中,然后考上了重点高中和师范大学。她的就业之路不算平顺,在江苏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相对饱和的地方,想成为一名有“正式编制”的教师颇为不易,所以她只能先在一所县城的普通高中代课,然后参加市教育系统的招聘考试。去年终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夺得一个紧俏的指标,目前在市郊的一所普通中学里任职。
女孩柔弱的外表下掩藏着的是一颗不屈的心。正是这样的一颗心让她在没有任何背景、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下凭借自己的努力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我想,这或许也就是百万三峡移民共同拥有的一种精神和气质吧。
他们的梦,被裁成两段——一段遗落在那片遥远得再也回不去的故土上,随着时间渐行渐远;一段播种在脚下这片新鲜的泥土里,坚实而令人憧憬。祝福他们:一切如愿!(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