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存 :铸丹心开日月
张晶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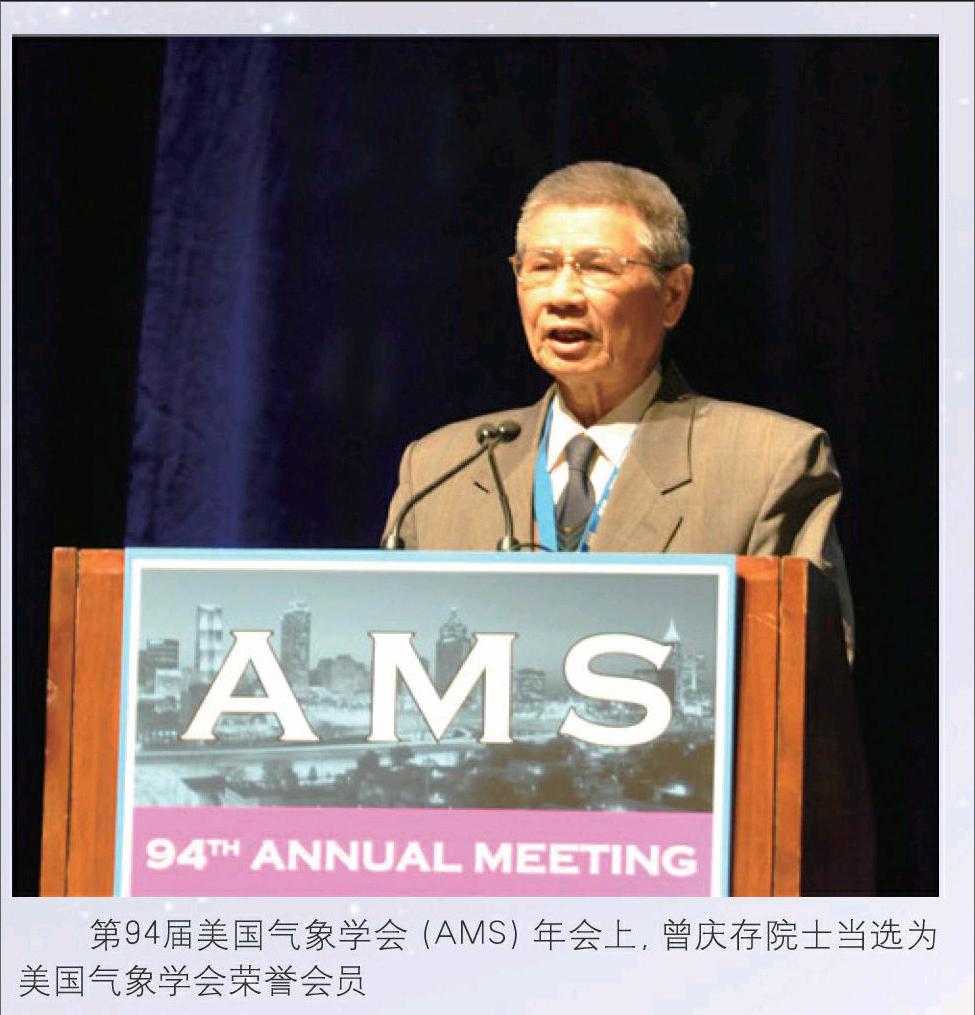


曾庆存院士当选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对于中国气象学界来说,这是一份来自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出生于1935年的曾庆存先生今年已是79岁高龄,龄近耄耋,虽偶有疾恙,但腰杆仍直,思维仍敏捷,依然孜孜不倦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2014年岁初,各大科技网站纷纷刊载消息—“曾庆存院士当选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对于这位45岁便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同时也是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气象学家来说,多一个头衔或许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对于中国气象学界来说,这是一份来自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记者有幸在大气物理所铁塔分部的安静园区采访到曾先生,敲门进入时他正伏案为学生修改文章。背阴的办公室里光线并不是很好,简朴办公桌上的日光灯发出淡淡的白光,到处摞着的资料默默述说着主人多年来的故事。
“堂堂七尺之躯,有骨头,有血肉,有气息,喜怒哀乐、成功与挫败、苦难与甘甜,人皆有之,我也一样,老百姓一个。”这是曾庆存的自描,掷地有声,亦文采斐然。
智启于父
谈到自己的启蒙老师,曾先生毫无疑问地说是自己的父亲。幼年家贫,但曾父却始终勤勤恳恳,与邻为善,曾母也是温良恭俭,悉心照顾着曾家兄弟姐妹。一日,曾父去往城里挑肥,偶遇小学校长。校长见曾父虽为农民,举止投足之间却透露着一股文雅之气,遂上前交谈。
“谈话中校长了解到父亲有两个适龄读书的儿子,便嘱咐父亲一定要让孩子读书。”曾先生说,“其实父亲自己也非常向往课堂,无奈没有机会。”听了校长的话之后,曾父下决心一定要让兄弟俩读书。自此,曾庆存便跟在哥哥身后,日日往返于田野学堂,因为知道机会来之不易,兄弟俩都倍加珍惜。
一边劳动,一边读书,本来觉得能考上中学便是幸运之事的曾庆存,从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在大学深造,并且将科研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事业。1952年,响应政府号召,他报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顺利考取之后被分配到了气象学专业,从此他便展开了自己的科研人生。
在他的故乡广东阳江,乡亲们都说:“曾庆存即使不做气象学家,也会成为一名文学家。”
放牧于田,少年曾庆存会唱山歌来解闷,开始读书之后,他开始正式了解中国的古典诗歌。放学归家,曾氏兄弟复习功课,曾父也在旁共同学习,吟诗诵词,抑或在地上练习写“大字”。土地上的活计十分繁忙,除了愉快的晚间时光,另外一个全家可以在一起享受诗词之乐的时间便是连日阴雨之时。
观屋外雨景,曾父吟出一句“久雨疑天漏”,曾庆存接道“长风似宇空”。“父亲虽不无赞赏地说有几分少年英气,却嫌对得欠工整。”曾先生说。后父子联手,成诗一首:“久雨疑天漏,长风似宇空。丹心开日月,风雨不愁穷。”曾父极为喜欢这首诗,83岁高龄时,亲笔将这首诗题于纸上,这也是曾庆存最为珍惜的一件纪念品。
被问到为何会喜欢上诗歌时,曾庆存回答说是因为博大的中华文化和秀美的祖国山川。他爱学问,不管是科学还是诗歌,甚至开玩笑说,“若要我从政,也许会是一个贤明公正的好官”。
史公之励
1957年底,曾庆存被选拔赴苏联深造,师从气象学大师基别尔。基别尔建议他从事应用原始方程作数值天气预告的研究,尽管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题目,曾庆存最终还是听取了老师的意见。
历经三年的时光,曾庆存细致总结了老师以前的工作,中间经历了多次失败,苦思冥想之后,在1961年他首创了“半隐式差分法”。该方法至今仍不失为一个好的研究方法。曾庆存说,自己虽然时有中断,但一直在用功研究。
在苏联曾立志要攀登上大气科学的珠穆朗玛峰的曾庆存,自评虽未登顶,但大概已经在海拔8600米处建立了一个营地,供后人休憩、前行。
1972年,曾庆存当时工作的团队收到了强制解散的命令。这让他和同事们痛心不已,工作和生活陷入了困境的他大病一场,期间又失去了自己挚爱的哥哥,这使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在给自己四姐的信里,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情况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十二级台风”似乎有吹毁一切的架势。重压之下,不少人选择放弃,他却逆风行走。
谈到当时的情况,曾庆存先让记者诵读了《史记》中他最喜欢的、支撑他熬过那段岁月的段落:“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人生在世,就得与天地共同奋斗,推动社会向前进。”曾庆存说,“当下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似乎已经偏离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大同世界的内核。面对不公,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享受工作的乐趣。”
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仍然出色完成了之前上级交给他的编写任务:出版巨著《大气红外遥测原理》和《数值天气预报的数学物理基础》。
谈到自己最喜爱的作家,曾庆存提到了三位—司马迁、毛泽东、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这之中,太史公其人其事对曾先生的人格养成影响最为巨大,其行文风格也深受《史记》影响。
遥跨千年,承史公之励。曾庆存写下这样的诗句:“家有难事任务多,千头万绪绞心窝。未成著作咬牙抵,灯冷蚊叮夜揣摩。”
科学之诗
早在31年前,曾庆存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做科研需要“勇敢、严谨、坚韧”。时至今日,他依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不敢就不能创新,错失了‘正确的萌芽;不严谨就会根据不足,为错误开了门户;不坚韧就可能达不到循此路本可达到的正确的地方。”
曾庆存将自己的科研创新扩展到了科学与文学交界的地方。确实,他不仅是研究wt的一把好手,在科学院更是因为写得一手好诗、好文章而有着“诗人院士”的美誉。他解释说,写作于自己是一种愉快的体验,同时也希望将这种愉快的体验传递给读者。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人反馈说,不管是读他的文章、诗歌,还是读他的专业论文,都有种爽快的阅读体验。
在美国气象学会(AMS)年会上,大会会刊登载了曾庆存《帝舜〈南风〉歌考》以及他写作的七言绝句《图桑之春》《京郊四季》的中英文版本。
《南风歌》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夏季风的文献,成文于公元前22~23世纪的舜帝时代。“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全诗寥寥26字,却十分生动形象地阐释了华夏子孙与东亚夏季风之间的紧密关系。
曾庆存完整地解释、追寻了这首诗歌的内容和起源,用科学知识解读了中国古典艺术;与此同时,他也反其道而行之,用诗歌展现了科学之美,《咏亿年前古树硅化石》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在这首诗中,曾庆存从硅化木的形成联想到宇宙生生不息的运动规律,咏物托情,行文大气浑厚。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甚至入选了中小学练习题,学生们从文学、科学两个层面进行鉴赏,收到了许多积极的反馈。
虽然许多人将科学和艺术看作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他却指出无论是科研还是写作,都离不开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两者的相互配合。“写诗虽是由心血来潮的灵感冲动所引起,但其意境或其形象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及其表达,则是理性思维的范畴。”在曾庆存看来,做学问也是要讲求美的,“枯燥无味的学问不是好学问。”
曾庆存爱山水,相比人世浮华,他更喜观天地浩然。早年虽行程万里,但因工作所累,多无法阅山赏水。现在职务略减,每到一地,他都尽力记下见闻,也因此拾得不少佳作。
“霏霏雨,蓝天晴,康定弯弯溜溜城。”这是曾庆存眼中的康定城。七十载铸丹心、开日月,他至今仍然保持了一颗赤子之心—“天欲白,兴犹酣,鼓难停,抒不尽,古今中外情。”
(本文转自《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