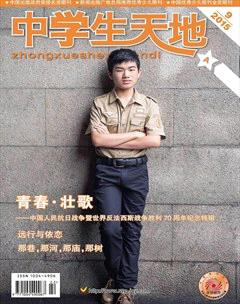日落无声
戴思杰
在熬过了连续几天的阴翳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清晨——久违了。北山路上纷杂的落叶在西湖的粼粼波光中熠熠生辉,似乎是拥有一种独立于喧嚣之外的、出淤泥而不染的静。这使我很好奇:静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孤山的西北面是一片不大的草坪。那时候,草还是绿的,常有人在这里搭起帐篷,躲开窄窄水域对岸的那些令人不安的闹。不过深秋是没有绿草的,只有一地泛黄发脆的曾经的绿草。因而,这里也是没有人的——哪怕有人,他的心也已不属于这里了。
不远处便是西泠印社。一级级石阶承载着岁月那灰绿色的厚重,在秋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那是朝圣者虔诚的脚步,抑或是取经人哒哒的马蹄声。只可惜,他们终究是过客,不是归人。
穿过一道阴冷的石拱门,流动在眼前的是和煦的阳光与沉淀于历史中的檀香。并没有想象中络绎不绝的游人,有的只是几个老人、几副眼镜与几盏淡茶。站在山边,极目远眺,山下的湖面上浮动着一层淡淡的薄雾,使人看得不甚真切,就像是深夜街边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然而只顾着埋头吃面的人注定是看不清这个世界的——毕竟,深夜吃面的人,其内心多少都是有些“近视”的。
有些时光注定是要被辜负的,但这并不是一种浪费,因为生活本就如此。阳光再好,也会有被遗忘在黑暗中的角落,这是不可避免的——否则,角落便也不是角落了。
“静”的存在,不过是为了迎合“闹”罢了。其本质无非是对空虚所做的一点拙劣的伪装。
天色渐晚,山脚边的阴翳越来越大,陈其美将军在荒草地的幕布前兀自挥舞着长鞭,像是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不用回头也知道,身后那被拉长的背影是如何的不愿承认的孑然。
但就在一片枯黄的荷叶旁,一对年轻的夫妇撑着阳伞,依偎在湖边的木质长椅上。阳光透过伞面,映衬出一种温和的橘黄,像是夜晚的路灯,或是港口的灯塔。他们保持着一种最自然的、毫无拘束的姿势,像一座雕像般在夕阳下闪烁着亘古不变的光芒。
世上的阳光本就不止一种,有的来自天边,还有的来自内心。而“静”的背后,就是这样一颗淡然而强大的心。黑夜固然是漫长的,但它只不过是白昼的另一种形式。有时候,平静的内心是比阳光更具有穿透力的。正如某位名人墓碑上所镌刻的墓志铭:纵使全世界黑暗,也不能掩盖一支蜡烛的光芒。
人世有言,日落无声。此去经年,良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