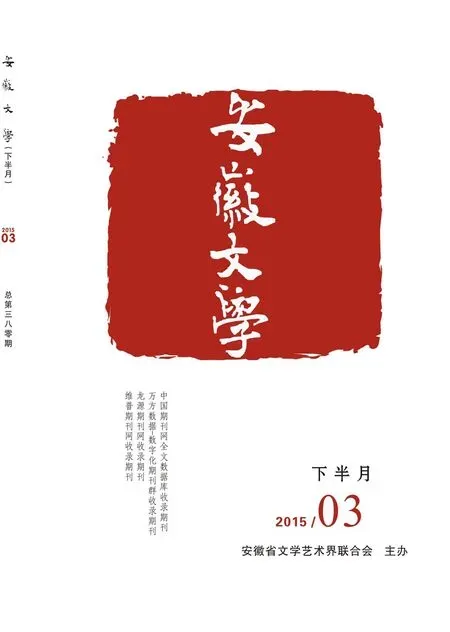《滚钩》:现实与历史的叙述二重奏
武兆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滚钩》:现实与历史的叙述二重奏
武兆雨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滚钩》以“挟尸要价”事件为核心,通过双重叙事变奏,紧贴人物生命纹理,还原成骑麻在现实语境中的生存窘境和道德挣扎,以及在历史语境和时代错动中的无力和卑微。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向度,发现了道德式微的小人物主体性的消失。
关键词:《滚钩》主体性道德缺失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江河浩渺,波涛诡谲,驾着扁舟出没于湍急凶险“风波”的是成骑麻。贴着他的生命纹理,体味他的生命温度,于是发现捞尸人成骑麻是现实与历史的交汇点。拨开道德叙事的浮藻,叙述的双重变奏将他从“风波”中“打捞”出来,还原了一个无法“回家”的老人。
一、现实语境中的挣扎
“挟尸要价”事件中对传统乡村道德伦理式微的洞见和批判漫布报章笔端,舆论争相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堆积”和“叠加”挟尸要价人的罪孽深重。《滚钩》①提供了可恶以外的另外一种“表情”,在粗粝的叙事中发现普通人在现实语境中的痛苦挣扎。
成骑麻是长江上捕鱼的渔民,主业是用滚钩钩尸的捞尸人。双重身份背后隐藏着一种讯息,多年的过度捕捞和水利工程的建设导致长江内无鱼可捞,捕鱼人因此难以为继,捞尸便成为渔民维持生计的手段。捞尸被“规范化”为一个产业,在看似合法化、实则荒诞的史壳子公司的垄断和管制下,成骑麻内心深处的道德感被冷血无情的“史壳子”所钳制,失去了个体自由。两次捞尸事件写出了成骑麻的挣扎、无奈。第一次是成骑麻发现被水浪冲到岸边的同族侄子小安,打走了啃噬尸体的狼一般的野狗,却纠结于是否向小安亲属报信。自己浮起来又漂到岸边的尸体,并未借助捞尸人丝毫的力量,但成骑麻却不敢告知小安的家人去领回尸体,他担忧的是破坏了史壳子的“规矩”而失去这收入可观的“职业”,在史壳子的霸道、冷酷之下,成骑麻无力反抗,也无法以牺牲“职业”为代价来换回那可怜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甚至,卑微可怜如他,还要同史壳子一起制造一个捞尸的假象,将同族侄儿的身上挂上滚钩,从滔滔江水中再次打捞上来,用滚钩撕烂的伤口掩盖被野狗噬咬的痕迹。更需接受小安一家的涕零感激,和家徒四壁的小安家所付的那烫手的捞尸钱。小安得了绝症,因医治不起才与妻子双双跳江自杀,留下两孤老、两幼娃,和一屁股治病留下的旧债。史壳子还是狠心要了捞小安妻子的三千元捞尸费,又收了捞小安尸体的两千元,还美曰“乡里乡亲的特价”。成骑麻收下了捞尸所分到的一千元后,深深不安袭上他的内心,浑身“像筛糠似的抖”。他无法左右史壳子制造的小安被“捞”的假象,便将五百元钱送到正在打丧鼓的小安家,偷偷塞给两个孩子各二十元钱,又为小安点了纸上了香,用自己的方式稀释愧疚和罪责。
第二次捞尸是引起轩然大波的“挟尸要价”,一个在江边野炊的女大学生意外落水,同学们手拉手组成链状下水救人,落水女同学救上来后却有三个男学生永远地沉入江底。史壳子派了三条船捞尸,可是收不到一万两千元的定金,史壳子便不发话捞尸。任那么多“学生样的男男女女的哭”和“那么大片的混乱和悲叫”,任大学的老师领导撵着史壳子急切地求情,和几十人“像被风割倒似的”齐刷刷地跪下。史壳子始终眼睛空洞得像水中爬出的饿死鬼,面无表情地不见定金便不松口。成骑麻却急得心疼,还抱有着早捞上来一刻便有可能生还的希望,可成骑麻的恻隐之心和道德感指挥不了他去捞人的行动,他必须服从于史壳子的命令。铁石心肠的史壳子在拿到一部分定金后,在成骑麻们的促成下,才发令出船下滚钩。成骑麻扯他上船时“暗使了一把劲,拧他一手”,以泄心头对史壳子冷漠无情的恨意。尸体打捞上来后,史壳子站在成骑麻身后“挟尸要价”,成骑麻在无意中被置换为了被群众口诛笔伐的对象,那个在史壳子前面挡住了沙子的老渔民,也替代史壳子成为众矢之的,被千夫所指。甚至连“滚钩”和渔具都被人烧毁,只留下一个烧黑了的空船,他无法“回家”。
平视两次捞尸事件中的成骑麻,他的“沉”和“浮、“死”和“活”都无法自主,他是被各方力量所牵制得失去了个体自由的人,真正贴近他的时候发现他多了几许可怜,少了些可恶。成骑麻的道德被以史壳子为代表的乡村恶势力所绑架,自始至终都在挣扎和纠结的成骑麻,都清醒地以乡村传统道德伦理还提示自己的他,终究落得的是一个孤家寡人落寞的身影。
二、历史语境中的错动
成骑麻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现实语境中个人生活的危机和挣扎,以历时性观照他的生命轨迹便发现在历史语境错动中的他更具复杂性和悲剧性,既包含了他无以维持生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变革中其生存资源的缺失,也包括在乡村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错动,同时还有乡村伦理的日渐式微,因而,在社会的变革、错动、断裂中,成骑麻只是一叶无力的
扁舟,浮沉、出没于时代的风波中。
成骑麻曾经历过两百多号渔船出江打鱼,捕鱼场景声势浩大、激动人心,肥美硕大的腊子和江猪子布满长江,下三层滚钩收获几万斤鱼只是稀松平常。如今大坝拦住了上游的鱼,也拦住了洄游的鱼,过度的捕捞也让长江中少了诸多活物。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中,以集聚金钱而非保证基本生存为目的的捕捞造成了渔民无鱼可捞、无法维持生计的局面,于是用来捞鱼的滚钩便派上了捞尸的用场,是生存资源的减少和消失推着成骑麻们捞尸过活。同时,成骑麻曾是村主任,是村中绝对的决策者。这曾经在集体经济时代呼风唤雨的成骑麻现在却受制于一个吸毒成瘾、无恶不作的乡村恶痞,透示着乡村权力的转移。“老村长算个卵,世界是他们的,也是他们同伙的,他们狠,你只能认”,旧的生活秩序解体,自由经济语境下产生一种包含断裂、对立的新的社会秩序,成骑麻们被抛离话语权力的中心,而受制于史壳子们乡村恶势力,成为了贫穷、孱弱、无力的底层群体。“许多年过去了,革命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正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旧的生活秩序正在解体,新的经济秩序迅速地制造出它的上流社会。”②现代化在带给一部分人文明和财富的同时,剥夺了另一部分人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权力,这种在自由主义经济逻辑中的合理分配自然失却其平衡性。另外,以捞尸为视点,透视捞尸组织的世代更迭,则可观到乡村道德的日渐式微。成骑麻的祖辈都是水牛市民间慈善组织“义善堂”的成员,专门负责捞尸葬尸而不收受分文酬金。1949年后,政府接管,同样捞尸不收钱。“文革”时期,成骑麻的父辈自发地义务捞尸葬尸。发展到成骑麻这里,这种民间义务的组织已不复存在,反而被史壳子所“合法化”为一个专门的捞尸公司,以捞尸为谋取利益的手段。在史壳子的“绑架下”,乡村伦理道德日渐丧失,“纯朴和善良,正在我的底层悄悄消失”。②事实上,成骑麻内心中的道德力量已经失去了强力,微弱得无力与史壳子的失去道德和法律双重惩戒的霸权相抗衡。他内心的恻动只是一曲愈唱愈弱的悲歌,他的挣扎和纠结只能被平视着他的人所看见,而其他人所知的,只是那个站在渔船头,手拖死尸的无情者,是被新闻的口水和民众的唾骂所淹没的“挟尸要价”的道德沦落者。
成骑麻其人,在现实语境中贫困挣扎,无法左右个体的决定和行动,放置在历史语境中,被一股股翻滚着的浪潮卷入种种风波中。贴着成骑麻的生命脉络,从一个渔人的视角审视现实、回顾历史,一种真实与虚构的咬合提供了新的理解和精神向度,原来手持滚钩的他也只是如“一粒浮游的尘埃”③般的可怜人。这并非为成骑麻开罪,只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还原了在种种错动的变局中失去个体自由的,听着《回家》乐曲却无法回家的七旬老人,如一叶小舟“出没风波里”的无奈和悲伤。
注释
①作者陈应松,刊于2014年第5期《十月》,先后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
②蔡翔.底层[J].天涯,2004(2).。
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c58050102v7n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