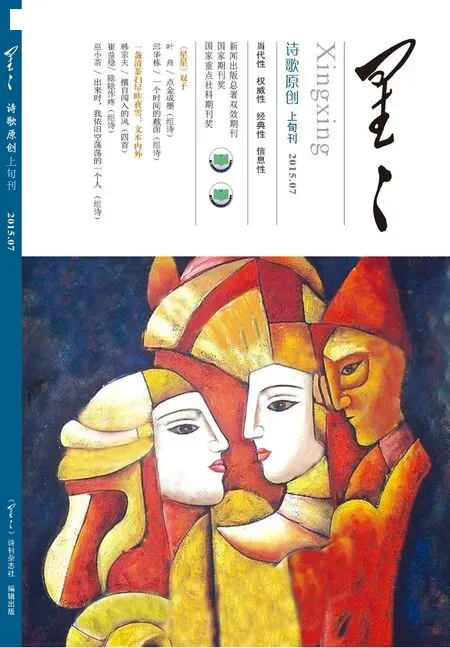猪图腾 狗兄弟
崔益稳
猪图腾 狗兄弟
崔益稳
我家三代与猪有缘。爷爷和父亲均是老家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杀猪匠,为日本鬼子和八路军都杀过猪。我刚参加工作时在肉联厂与猪打过十年交道,如今一不注意,猪常入我的文章和诗行。
在原生态的农村,猪狗几乎是朝朝暮暮不分家的兄弟。父辈杀猪卖肉时,也常干些贩狗杀狗的营生。在我童年的彩色记忆里,有关猪狗与人的真实故事生动得让人忍俊不禁,越想越回味无穷。
这里要说到两个词语:忠诚和奉献,在这两个畜牲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在当下时代高铁和物质洪流的呼啸冲击下,人类丧失的最快最多的恰恰是这两个词语。所以,我一次次将笔触伸向它们,一次次在内心将它们呼作“兄弟”。所以,故乡的荞麦、草垛、青菜之类的美物在我诗行里恣肆汪洋。
更多的人蜂拥进入城市,猪们狗们也以不同方式闯入城市。因我频频将当下人的生存状态置于城市与猪狗的背景下,不少朋友常指着街上猪狗半开玩笑讥讽我,看啊看,老崔的兄弟们来了!
狗兄弟怎么了?猪兄弟怎么了?我才不恼呢,如今这世界上能和它们平起平坐的多嘛?多少次酒酣之际。我拍案左右反问,现在有几个人保证活得比一条狗还要忠贞不二?
在记忆里那个质朴而贫穷的年代,一头猪好比一座化肥厂,是一个家庭变富的精神图腾。一只狗等于一尊守护神,对于一个村庄的长治久安何等至关重要。斗转星移,它们进入城市了,除了血液里仍流动着原始的基因,它们也以固有的神态延续其独有的生活方式。我在郊外一座现代化的养猪场看到,被称作太湖品系的杂交猪,被铁栅栏箍在不足一平方米的铁框内,从生到死不能转身,不能越雷池一步。可它们依然那么憨厚与从容 ,以一口一口的粗料变为一坨坨肉。这不是奉献精神,是什么?朋友送我几斤这种猪做成的腊肉,一遍遍叮嘱这是“生态猪肉”,可我品尝后发现与记忆中的土猪肉味大相径庭。嘿嘿,也许这就是当下时代的况味吧。在街头与小区间窜来窜去的狗太可怜了,相比于随时都可在乡村野田撒欢调情的祖辈,它们如今连谈情说爱的场所也没有了。
我家狗的故事更加令人唏嘘。母亲撒手人间后,与她朝夕为伴的狗送给了邻居。去年邻居因拆迁搬往集镇,将狗装入麻袋带走,准备给它安排宠物狗一样的悠闲生活。可狗坚决不从,一次次被捉走,又一次次跑回来,毅然回到它消失已久的狗窝里。看它可怜,邻居只好在我老家墙角瓦砾处,以砖头就地搭了一个简陋洞。今年回去过年,我一心找它,甚至欲抱住它一遍遍致敬:我的狗兄弟!可惜未能如愿,它或许成了一只流浪狗,或许成了别人的盘中餐。但我为它庆幸,他肯定没有客死他乡。狗尚且如此忠贞于故土,何况人呢?
猪图腾,狗兄弟,怎能不让我放眼正被城市化疯狂进攻与掠夺的故土。一排排风景如画的房子麻将牌般被推倒,清亮的小河被烂透的水草瘀塞了。最心疼不过的是,每次与乡亲们照面,听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我熟悉的名字,谁谁走了,谁谁又走了,得的多是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怪病。在城头登高远望故乡的方向,依稀可见老家四周的生命之灯一盏盏熄灭了,只剩下门前几棵老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苟延残喘。这又使我自然地联想到诗,想到那些曾经花哨、浮躁的文字游戏。我不可能改变活生生的现实,但我可以记录,可以呼喊,真实、真挚、真诚,以诗人之眼光烛照未来。
一位大诗人说,所有的诗人开始都是“最初的洞察者,诗人中的王者,真正的上帝。”但是,最初的洞察者会蒙上红尘之翳,王者变成了奴隶,上帝变成了弃儿。区区数年,很多诗人面前的猪们狗们,不过是行走与长肉的动物而已。而我要在疼痛里与它们一起行走。
在疼痛里飞翔与行走,是多么残酷的纠结。生活之恶在践踏,而我自己竭力用诗歌在拯救。每每读写滚烫的分行文字,都会想到波特莱尔那只追随海船的信天翁,它有天高海阔的胸怀,它有搏击风暴的坚强翅膀与心脏……可我总是不自觉地一下子联想到猪与狗的形象。
洗洁剂一样的时代之潮,每个人都得异化,但在异化面前得清醒,得坚守!我有足够的内心勇气声明,我要继续大声将猪狗们称兄道弟。我要用笔留住时间和人性最纯粹的部分,故我真实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