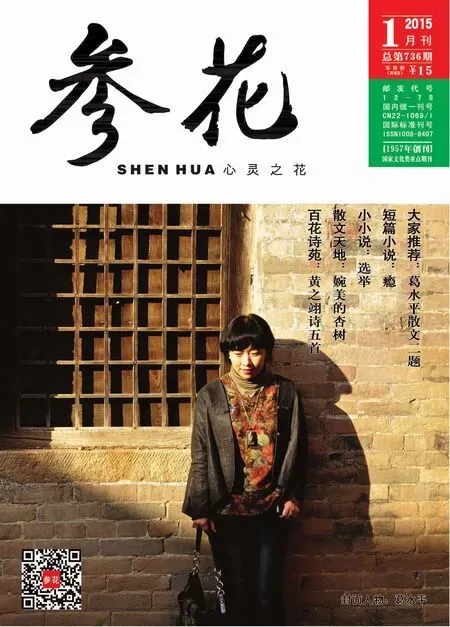城市
◎罗志伟
城市
◎罗志伟
这一场雨,把整个深圳轰然拉入了冰窖,朔风催促着行人更衣取暖。
我坐在床头。听着窗外基坑里的桩机无趣的嘶吼,如粗糙的鼓声,伴随着这个城市的节拍日夜击打,不眠不休地刺激着这个城市的更迭。我知道它的作品,是这个城市拔地而起屹立于世间的根基;是岁月沉淀后掩埋在时光里的失眠者,它如行走于战场的先遣军,却又是坚守阵地的无谓勇者。它和它的作品,骄傲而伟大。有几分荡气回肠,却又有几许凄凄寂寞。我起身望着窗外,淅沥的雨洗涤着这个城市多日的阴霾,却再也阻断不了我闻兴而起的思绪。
我在想,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一台桩机,都在社会这泥潭里摸爬打滚,亦步亦趋,带着自己的判断、尊严和信仰,带着自己对未来的承诺。窗外的雨在寒风料峭的冬季显得格外冷清,从去年七月至如今,十七个月的时光,辗转五个城市,调离六处,我很庆幸自己还在坚持,在与流年失去、容颜失色的成长中,幸好没有把青春麻醉。至少在这冷寂的冬夜,我还能诚恳地相信我的生活会如花似锦,会不时有甘霖滋润着我,对一切憧憬的浇灌。
只是一个人,在一座偌大的城市里,想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时,总有一份“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的凄凉。岁月在成长与老去中从不作妥协,却还要将距离一步一步拉开。我记得父亲在寒冷的冬夜,总爱手捧一本厚厚的书端坐在火炉旁,全神贯注地翻过一页又一页;我想起我的母亲,这会儿她应该正在父亲旁,一针一线地绣着鞋垫,那儿肯定有她最爱的儿子和未来儿媳妇的结婚垫。也许,他们正在谈论我的归期;也许,他们正在抱怨我的远去。
我已经习惯这份距离,习惯站在窗前遥望着眷念的方向,直至眼角湿润,转过头来。
窗外的雨开始放肆,发怒似的击打着玻璃窗户,将桩基的嘶吼声也渐渐掩盖,直至消失。这样的雨,或是激昂,或是愤怒,又像是为我弹奏的交响曲,在我内心激烈游走。我想这样的乐章,它只会为梦想响起。曾几何时,我总在思索假若我回到从前,我是否会抛弃让我举步维艰的理科题海,重新拾起文字,悲喜交加于苏童、余华,痴迷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村上春树。我记得那时的我,总爱走在田间小道享受稻苗的绿色;一个人穿梭在山野丛林间感受风声的孤独,因为刻在心里的追逐如云朵般悠然而真切,更如这窗外的雨水一般,透明而亮丽。
还好,还好我还记得。记得自己还年轻,还要记录,还要充实,还要写下许多自己沉醉的悲欢离合。这场雨,似乎在诉说,它是天空捎来的过客,在我耳畔轻轻告诉我,我是有多么美好的年华,多么纯真的向往。我想起我身边的那位女孩儿,那位来自遥远北方的姑娘。有时会生气地和我说,跑一辈子的路,就为了你一声的苦笑。有时也会撒娇的期待,以后啊,我们在最美的城市,在春花烂漫的午后,在明媚的春光里,撑一把油纸伞,漫步在青石街上,抓住流失于指尖的年华。
有人说,最美的青春不过是有一两个一直陪伴你的朋友和一个盗不走的爱人。如果年华渐渐远去,如果时间变得急躁,我定然依旧会用最鲜艳的纸,最亮的色彩写上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经典语录: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来特意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你年轻时更美。与那时的容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倍受摧残的面容。”
殊不知这是我最后的情书;殊不知还能挣上她最后干枯的眼泪。然后买上一张永久的火车票,踏上一辆没有终点的列车。
雨终于停下来了,灰蒙的天空像是一部黑白电影的底色,路上的行人成了最好的布景。但是我想遥远的故乡此刻应该是蓝天白云,冬阳暖照,那个养育我二十余载,充盈我期许,滋生我梦想的地方,也会像欢迎我一样欢迎我身边的姑娘。
朔风揭起夜幕的衣角,桩机谱出的乐章又开始为这座城市的前进响起节拍。时光又一次在我的梦里插上翅膀,翱翔在青春里,遍地阳光。
(责任编辑 陈天赐)
罗志伟,男,湖南娄底人,1990年6月20日出生,就职于中建三局二公司,造价工程师,好文学,擅长于散文、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