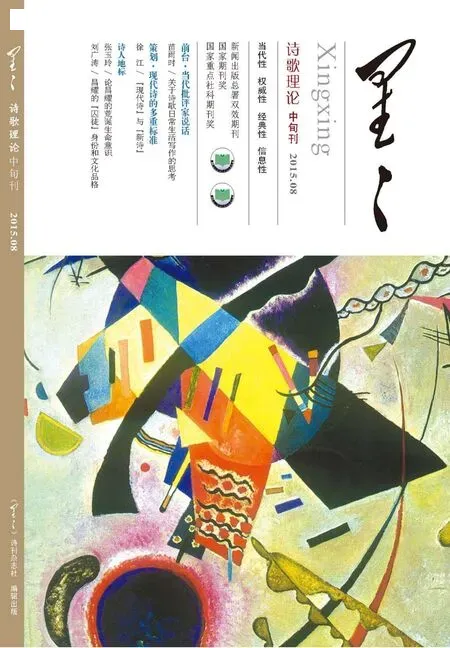论昌耀的荒诞生命意识
张玉玲
诗人地标
论昌耀的荒诞生命意识
张玉玲
一、荒诞生命意识产生的动因
昌耀的生命意识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两个字:荒诞。然而昌耀的荒诞意识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种合力的作用,在这一合力中,有这样几种力量最为关键,一是童年的创伤性记忆;二是亲人的非难与离世;三是罹难的人生经历;四是复出后的生存困境与社会现实。所以说,荒诞生命意识最后成为昌耀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与意识并非偶然。其实,从昌耀的童年起,它就已经潜伏在诗人的命运之中了。昌耀的童年是在一个高斋大院中度过的,家族很大,但遗憾的是男人都外出闯荡天下去了,留守的只有一些孤儿寡母,昌耀在这样的氛围中感受到了人生的寂寞与恐惧,他曾写过这样几段回忆文字:
然而,当我此刻回忆起这座老宅的存在,却感到几分悲凉——在它所处的那个年代就予人这种悲凉的氛围。试想,那样一座深宅大院年代久远,老主人相继过世,年青的男主人们长年浪迹江湖并不守家,只留下一两位娘子——年青的女主人留守,岂不让人有一种空空落落的寂寞。我至今还能感受到与我老宅遥遥相对的火焰岗佛寺早晚悠缓飘荡的钟声是那样的寂寞,且又是那样的深远的寂寞。
……
人各有志,或者说,人各有命,但在九九归一这一点上,虽则人生不同走向的选择显示了某种倾向性,而结局并无本质不同。此刻我在回首当年这个大家庭年青一代主人们后果的结局之后,不仅带着一种宗教情感品味那曾经有过的一幕幕而叹息:果真是苦海无边!
……
但是,我的出生并未给这个正走向新一轮裂变的传统大家庭带来何种喜气。母亲说,我出生的“民国二十五年”是九龙治水,洪水泛滥。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局动荡不宁。……灾变意识从小就渗入到我的心灵,伴我一生。[1]
从昌耀的童年回忆中,我们发现童年给昌耀留下的印象是:人生寂寞感与灾变意识。可以说,这一印象就成为后来昌耀诗歌中荒诞意识产生的最初根苗。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亲人的离世,尤其是母亲与父亲遭到逼迫并自杀身亡这一事件。而这一事件又与昌耀参军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按理说,参军应该是昌耀人生中较为荣耀的经历,但遗憾的是这段经历却又意味着骨肉永远的分离,所以,关于这段“红色记忆”,昌耀每每谈起时,总是轻描淡写:“1950年4月,38军114师政治部在当地吸收青年学生入伍,我又瞒着父亲去报考,被录取,遂成为该师文工队的一员,后来就有了我此生最为不忍的一幕——与母亲的‘话别’。每触及此都要心痛。……那年我13周岁。我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与母亲的永别。不久我随军北上,第二年又去朝鲜。”昌耀在这段文字中与其说是谈论自己的经历,不如说是谈论自己的情感。这段文字里最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昌耀提到的与母亲的“话别”。因为这次“话别”之后,昌耀便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母亲。谈到母亲,昌耀是这样表达的:“我从小深爱着我的母亲。……她于1951年因贫病去世,如若记忆无误,享年应是40岁整。”昌耀说自己的母亲是“因贫病去世”,这样的陈述并不准确,昌耀的母亲去世并不是“因贫病”而是因受不了迫害而跳楼自杀的。[2]在这里,昌耀为什么要隐瞒实情呢?而母亲的去世对昌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可以了。另外,昌耀的父亲在劳教农场沉湖自溺身亡,伯父王其梅作为驻西藏的最高领导人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昌耀的弟兄姊妹也在变故之中不得不寄居在亲戚家或被送人。这些“不幸”昌耀很少提及,包括对其母亲的“死因”在内,都会成为昌耀所不忍面对的“人生变数”。这应该是影响昌耀荒诞意识产生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命运之无理与不公。
再者是昌耀的罹难经历。诗人曾这样概括自己的人生:“1955年6月已在河北荣军中学完成两年高中学业的我报名参加大西北开发。又越两年,我以诗作《林中试笛》被打成右派,此后仅得以‘赎罪者’身份辗转于青海西部荒原从事农垦,至1979年春全国贯彻落实中央‘54号文件’精神始得解放。”[3]从这段平静的陈述中,可以看到昌耀人生的主要轨迹,那就是因诗作《林中试笛》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后至1979年春获得平反,时间长度是22年。昌耀出生于1936年6月27日,获罪时21岁,平反时43岁。这样的人生经历对昌耀会产生怎样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受呢?昌耀曾有过这样的表达:“我回味自己的一生,短短的一瞬,竟也沧海桑田。我亲眼目睹仆人变作主人,主人变作公仆,公仆变作老爷,老爷复又变作仆人的主人。我思考自己的一生,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智力不足穿透‘宇宙边缘’,惟执信私有制是罪恶的渊薮,在叫作‘左’倾的年代,周体披覆以‘右派’兽皮,在精神贬值的今日,自许为一个“坚守者”[4]从这段看似轻松的口气里,我们不妨对昌耀的心态做这样的总结:命运无常。
以上的诸多因素都会成为一种潜在的因素影响到昌耀对人生的认识,也便为荒诞意识的产生埋下了很深的“根苗”。而对昌耀“荒诞”之产生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则是“复出”后的现实人生处境。我们说,昌耀获得“解放”后所面对的并不是他所希冀的那个“美好”的世界。相反,现实世界是:大同理想被消解,物质利益越来越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诗人”的身份变得“暧昧”不清。这是昌耀平反后不久所面对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面前,诗人显然感到失望和力不从心。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曾不无感慨地这样写道:
相形之下,我就显得太萎靡了,常觉身心疲倦,虽亦想有大作为,总慨叹能量有限,力有不逮。另一方面,我又是这样一个任性惯了的人,极易意气用事,好独来独往,不善约束,加纤尘于我有时也会感到其重如磐,如此等等是我做人的致命弱点。[5]
这段文字是昌耀本人的真实写照。这样的个性昌耀说是自己“做人的致命弱点”,这自然是不错的。然而,更为不幸的是,昌耀很快就要面对自己婚姻的裂变、无家可归这一现实。而在生活中“能量有限,力有不逮”的昌耀又将如何面对这样的波折呢?昌耀是这样打算的:
但我要说的是,我决计要从这种囚闭状态走出,先拟在机关办公室谋一铺位。如可能,愿在北京或上海谋一去就、栖止,一可供寄寓的蜗壳即可。啊,这真是我的短处,涉及经纪策划一途我就觉得头脑不清,笔谈也无心,以为不如干起来再说。[6]
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昌耀在生活困境面前的局促。而后,昌耀果然在青海作协的“美术之家”谋到一铺位,前提是白天他不能使用,只能到晚上下了班后,才能进去入住。[7]这就是生活中的昌耀为自己安排的生活。其次,就是昌耀在自己出书方面屡遭“滑铁卢”。他的诗集每每要出时,却总是因种种原因而流产。这一现象令昌耀既感到愤慨又感到无奈,以至于写文章呼吁“诗人们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并为了筹措《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的出版费,而向全国16家报刊发出广告:“鄙人昌耀,为拙著事预告读者:出版难。……本书只印一千册,现已办理预约,每册收款十元,愿上钩者请速告知通信处并将书款邮汇青海省文联昌耀(邮箱810008),当然,这一举措的确是昌耀在“穷途末路”之中的笨拙反击,但此举,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昌耀的处境,令同道者颇感不平,周涛可以算作不平者的代表,他曾不无愤怒地感叹道:“一个只出版过两本诗集的大诗人。他写了四十年,只有青海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两本诗集。这还不构成一种嘲讽么,偌大的中国,无数平庸的诗集出版印行,唯有这位最重要的大诗人投书无门。”[8]而诗人在出书方面所经历的种种“坎坷”也让当事者深刻体会到作为一个诗人在物质生活中的尴尬与无奈,并且不得不为“出书”而放低姿态:
“前几天漓江出版社总编聂震宁来信称,诗刊社那辑‘诗人丛书’因逢出版社今年不景气‘无法推出’,若我明确表示将其间自己的一本抽出,他们准备单独出版(不作为“丛书”),‘咬紧牙关’为其‘力争打开销路’。他们以为下半年就可以征订,明年初出书。但我是想出版一本可以包容230首左右的长短诗作的选集,如果出版社以为牺牲过大,我可以放弃稿酬或按‘稿酬从劣’标准收取一点象征性的稿酬。那样每本书就得需十一二个印张。我不知出版社是否同意……”[9]
态度真诚而谨慎。为了能够使自己的诗集面世,昌耀把自己的要求降得很低。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昌耀的书款中就有他昔日的女友汇来的两本书款:
收到您于9月23日汇出的书款20元,以及署名Z先生(实由您汇出的)书款10元。我真有一番感慨,不过我暂不说它了,也说不完全,也说不明白,也说不准确,还是节约一下您的眼力好了。
拙著仍在征订中,目前已预售出270本,您与Z先生的‘编号本’序号则是0221、0222、0223号。……”[10]
昌耀在这小段充满了数字的信件中告诉我们,他真的为了出版书在募集经费,去征订,但当他收到远途寄来的书款20元钱时,昌耀表述是“我真有一番感慨”,这番感慨是什么,昌耀没有说,但从他接连所使用的几个“不”字,我们可以推想,他当时的心情该是多么复杂!当然,也有感情受挫后的百感交集,一个诗人已经落魄到要让昔日的女友来征订自己的诗集了!这样的一份感受我们也许永远无法体会,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出版诗集时的困难与无奈。这就是为什么周涛会用这样的言辞来评价昌耀了:“昌耀的存在是对现时文学界的嘲讽,这种嘲讽是历史对现实的嘲讽,也是神意对人为的嘲讽。”[11]除此之外,更现实的几个问题还有:无家可归、爱情追求连连受挫、癌症的茫茫威胁、物质生活的困顿、离婚后面临负担三个孩子和原配妻子的生活费。这些问题无疑将昌耀的人生逼到了更为局促的境地。在这样的境地下,昌耀当何为?我们很快在昌耀的诗歌总集中发现了这样的表达:
‘存在’何以自解?惟释以‘人生如梦’无懈可击。”“其实‘醒着’只是直面枪口,徒有几分行色的悲壮,并不能改变潜在的厄运。”[12]
生活以最现实最物质的方式揭示出它的不容质疑的存在。生活的实际与诗人的精神追求形成了相互拮抗的一对力量。他在自己的一首诗歌《生命体验》中是这样描述的:“人生有不解的苦闷。/拨弦,吟以自慰,蓝色的忧郁降至深渊,/如如豆的目光。/如一粒液态硫磺。//狐疑,如小鸡啄米/在沙面点出命运不识的文字。//无话可说。”至此,我们说,昌耀对人生的总结便是——命运荒诞。从此,荒诞意识便真正成为影响昌耀诗歌和人生最深刻的一种生命意识。
二、人生的两面:承认荒诞与直面荒诞
然而,昌耀早期却是一位“乌托邦主义”的信奉者,尤其在流放青藏高原的22年中,他不仅坚信自己的理想,更坚信自己未来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因为他坚信“历史是公正的”:“我去熟悉历史。/我自觉去查视地下的墓穴,/发现可怕的真理在每一步闪光。”(《这虔诚的红衣僧人》)这一信念是昌耀早期诗作的内在精神力量,也支撑着昌耀走过了“右派”的岁月,而昌耀早期诗作的明亮风格显然与此有密切关系。但到了1986之后,他对人生的看法却有了质的改变,他开始承认:“人生是荒诞的”。并由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可以说,“人生即荒诞”,是昌耀后半生的人生观与最深刻的生命体验,这一观念隐含着这样几层内容,即命运造成了人生的荒诞;人生无理性可言;我们生活的时代令人绝望;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只能受难。这是一个连环套,后面的内容即是这一人生观的延伸,同时也在不断的对这一人生观进行诠释。而所有的内容的核心便指向了两个字“命运”。由此,昌耀的诗歌便不断围绕着“命运”二字进行着反复而细致的体悟与执着而痛苦的追问。有评论者认为,“昌耀对生命虚无感逼至绝望性的体认,当是与艾略特、卡夫卡处在同一个层面。而他对这种虚无感的惶恐、惊骇,与之罄其生命的大力绞杀和搏斗,则很自然地使人想到鲁迅—包括鲁迅那种与青年作家相互激励的老先锋姿态。”[13]这一认识很深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昌耀的荒诞意识并不是对人类俯瞰的结果,相反,它来自于深刻的生命体验,是对人生苦难与命运的反刍之后而不得不做出的体认。荒诞意识的产生对于昌耀来说,就是命运开始遍布人类的每一言行动作之中,是命运的出场与对万物的掌控,这一体认不仅颠覆了昌耀早期对“英雄”的顶礼膜拜,也颠覆了昌耀的信仰与信念。而昌耀承认人生的荒诞,就是承认“荒诞”对人生秩序造成了威胁与挑衅。昌耀并不想走近荒诞,甚至他并不想从哲学层面来承认荒诞,来抒发荒诞,“荒诞”对于昌耀不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是一种生命体验。并且昌耀对荒诞生命意识的表达与反抗是彻底的。他没有像鲁迅那样不惜用了曲笔,在瑜儿的坟上放一个花环;也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在体认苦难与黑暗之后,不惜用一生来寻求上帝。昌耀的态度是执拗的,他承认命运的不公与人生的荒诞,并也曾为自己寻求出路,比如爱、爱情、精神家园、诗歌,但这些最终都没有成为他的“诺亚方舟”,他最后选择了“死亡”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然而,即便是“死亡”也并不能成为生命的救赎。
昌耀的荒诞意识显示出一个诗人直面人生困境时的勇气与真诚,他没有伪饰与矫情,他对人生与命运进行了执着而不懈的探究,虽然最后的结论是人在命运面前永远是一个“败北者”,“一只逃亡的鸟”,但昌耀作为大诗人所显示的直面内心世界的写作态度永远值得我们感佩:“我之愀然是为心作,声闻旷远。/舒卷的眉间,踏一串白驹蹄迹。”(《庄语》)现在,昌耀已经远去,留给我们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如何守护精神失范时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将如何面对人类的困境?诗人将“歌唱”什么?如何“歌唱”?
[1][3][4]5][6][9][10][12][13]昌耀.昌耀诗文总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747-748,743,715,881,826,837,842,655,22。
[2] [7]燎原.昌耀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4-25,387。
[8][11]周涛.最后的礁石,《读 友人书三记》,1994.11.1《新疆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