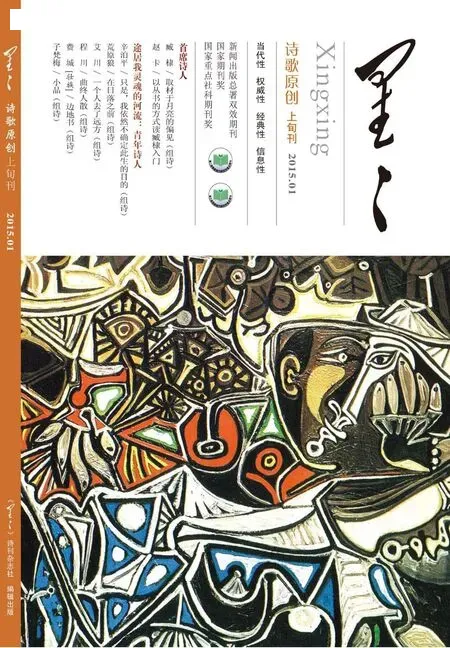取材于月亮的偏见(组诗)
臧 棣
取材于月亮的偏见(组诗)
臧 棣
柠檬入门
护工拿着换下的内衣和床单
去了盥洗间。测过体温后,
护士也走了。病房又变得
像时间的洞穴。斜对面,
你的病友依然在沉睡。
楼道里,风声多于脚步声。
你睁开迷离的眼神,搜寻着
天花板上的云朵,或苇丛。
昨天,那里也曾浮现过
被野兽踩坏的童年的篱笆。
人生的幻觉仿佛亟需一点
记忆的尊严。我把你最爱的柠檬
塞进你的手心。你的状况很糟,
喝一口水都那么费劲。
加了柠檬,水,更变得像石头——
浸泡过药液的石头。卡住的石头。
但是,柠檬的手感太特别了,
它好像能瞒过医院的逻辑,
给你带去一种隐秘的生活的形状。
至少,你的眼珠会转动得像
两尾贴近水面的小鱼。我抬起
你的手臂,帮你把手心里的柠檬
移近你干燥的嘴唇。爆炸吧。
柠檬的清香。如果你兴致稍好,
我甚至会借用一下你的柠檬,
把它抛向空中:看,一只柠檬鸟
飞回来了。你认出柠檬的时间
要多过认出儿子的时间:这悲哀
太过暧昧,几乎无法承受。
但是,我和你,就像小时候
被魔术师请上过台,相互配合着,
用这最后的柠檬表演生命中
最后的魔术。整个过程中
死亡也不过是一种道具。
半人半狮入门
古希腊人将他们的秘密情感
隐藏于半人半马,并制作出了
曲线劲美的大理石雕像。
至少有三回,我借用过那样的眼光,
世界果然另有一番景象。
说实话,有过一段时间,
我有点狐疑自己是否倾向于
过分理解人马之间的那种结合。
人身上的马,总是太逼真太漂亮;
反过来呢,马身上的人则不那么彰显,
幽暗得犹如我们在人性中
遇到一种反常的自我挑战。
医院里没有大理石雕像;
陪你走完人生之路的这些天里,
我的生活已接近我的神话。
不仅仅是死亡像吸铁石,
我的神话也源自真实的人生
从未真实过,而我却不得不面对它。
我的神话的中心,你正躺在
皱巴巴的病床上。十多天的
静脉注射后,你的躯体
坍塌成一个内部的洞穴。
大部分时间,你用昏睡原谅了
我们对生不如死的误解。
每天总会有一小段时光,
我能清晰地看到,有只小狮子
从你的身体里分离出来。
它先拍打墙壁,狠抓铁床的护栏;
安静之后,它会慢慢转向我,
抓紧我的手腕。它恳求我带你离开——
不仅是带你离开这家医院,
而且是带你逃离这个世界,
到一个没有人能找到你的地方,
那里,甚至连死神也找不到你。
你太累了,所以你需要
有一个地方比死亡更安静。
而这样的恳求似乎只存在于
母亲对儿子的神秘的信任中。
传递的过程中,我看清了
你身上的半人半狮。但更诡异的,
借助这恳求,我仿佛也认清了
我自己身上的半人半狮。
神秘的愤怒很容易找到我,
因为作为儿子,作为呼吸大师,
我却无能满足你最后的恳求。
十一月的眼泪入门
一滴已足够巨大,
足以让太平洋成为另一滴。
弥漫的浮力,甚至将生活减少到
就好像你正骑着金骆驼
穿过古老的针眼。
身边的沙漠,如同寂静的底座。
刺骨风吹过,时间的歌喉
如同宇宙的光明插座。
每个歌唱的闪电都在我们亲爱的内部
寄存过一份死亡档案。
但不管雨下得多大,它从未被模仿过。
假如秘密可用于忍受,
它显然已落下过很多次。
比如,母亲如人生的盐。
她的旁边,儿子像被砸过的一个深坑。
为月亮服务——赠康赫
你换了身衣服,就好像你最近认识的
魔术师是个女的,比男人还知道怎么欣赏
周星驰的电影。用傻笑叫停
时间的精神分裂,就好像给生活一个面子,
吃亏的,只可能是魔鬼。
而你确实表示过,仅就人生的技艺而言,
用金黄的落叶,就可兑现一笔隐蔽的财富,
其实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难;
但一旦我们显露出认真,它们又不过是
一点小意思。有意思的是,你的孤独也不过是
你的认真超过了死亡为我们划定的界限。
你向我打听如何为月亮服务。
它为我们服务了那么久,难道你感觉不到?
或者,它为你身体里的某个秘密工作了
那么长时间,且从不以我们叫不叫它蓝月亮为要挟,
你就没觉得一点歉意?好吧。
但是听起来,就好像不叫它红月亮
我们会失去你对宇宙的信任。
有时,我更想表达的是,表面上,我欠它一碗酒;
但实际上,我欠你一只整过容的青蛙;
因为不叫它金黄的月亮
你会憋死。而金黄的月亮背后
你的身体始终比世界的黄金更出色。
或者这么说吧:但凡涉及胜算的微妙,
必遭遇冒名的春秋结伙而来,
递上白条,眯缝起权力的白眼,
索要一个完美的贿赂直到它足以媲美
爱的礼物。而你已完全想不起来
那是在何种场合里,对着浩荡的纯粹,
你第一次叫它黄月亮。但听起来
就好像不喊它苦月亮,你会对不起
卧底在人海里的心针。
给秋天一个理由
我订购的铁树
在电话里说:先生,您订购的
铁树到了。请不要误会。
我绝对不可能听错,
正如你说过,我们的口号里
还缺少一个:为月亮服务。
于是,我打电话告诉你:我订购的
铁树到了。如果你不过来看,
你就是电话那一头
它开出的那朵花。
拆 迁
你付过钱,也按过手印,
也给迷人的权力穿过一条裤衩,
还用白手绢擦拭过,无底洞的后视镜;
但是一点也不奇怪,那房子并不存在。
要么就是,等记忆完全恢复时,
房子已不在原来的地方。
这一切有秋天的月亮为证。
你把前门关上时,皎洁的月亮像你的女儿,
带着从车站上失联多日前
只有卖冷饮的人见过的最后一副表情。
你把后门打开时,金黄的月亮像你的儿子,
已被大麻出卖,而耻辱并未获得新意。
取材于月亮的偏见
它不可能认不出你。
但它始终和你保持距离,
用这样的方式,它忠于你的生活——
直到你为自己那么容易就比它深刻感到羞愧。
也在只有这样的羞愧中,人的死亡
才可能获得你的真实。
于是你想,它其实也和死者保持着
同样的距离。带着发光的钩子,
油腻的吊环,诱人的钻石项链,以及
永不过时的耳坠,从新月到满月,
它在世界的黑暗中同时
也在我们的黑暗中重复自己,以至于
你很容易想到,它像试衣镜一样没有原则。
它不参与判断良心在左边还是在右边。
像皎洁一样,它有自己的局限。
但它很少出错。多数时候,
它在你认出它之前,已认出了你。
它有自己的偏心,它照耀的是你的耐心——
就如同照耀本身即它的道德。
中秋自画像
山谷的深处,好天气好到
时间的蓝肌肉从早上开始
就透明在高空中。盘旋的山鹰
无意中圈定了新的方向感。
至于云淡,它首先是一个偏僻的好词,
其次,它一直要淡到你开始习惯
我是我们的天气为止。
而我仿佛从未想过,离京城这么近,
人生竟会如此稀少,乃至稀少到
几乎可固定在山泉和山楂
以及枣树之间几条的土路上。
并且每次,上坡都比下坡要纯粹。
惊飞的伯劳,就好像有人喘着粗气
指着美丽的弧线,管它叫福楼拜。
或者,就坐在石头上,等一下
我们该如何面对什么叫纯粹。
即使按怀疑的尺度,这里的崎岖
也足以令盛大的秋天看起来
像一个安静的刀鞘。每片落叶,
都能从内部擦亮一寸锋刃。
如此,从里面,你随意抽出一把刀,
给物质削皮,很可能会将我
削到我们最透薄的那一环。
稍微一捅,那微妙的精神
便会将你中有我炸成
秋天的气息中最陌生的漂浮。
而我竟然知道,即使这只涉及
半真半假,你也不会介意。
秋天的秘密风景——赠秦三澍
黑暗中,马厩已荒废多年。
黑暗中,喜鹊搭建在榆树上的窠巢
像黑暗的时间中看不见的砝码;
而风景的倾斜要等到早上,
两条大狗飞奔着,冲向混种着
石榴和海棠的小山坡,才能初见分晓。
不仅如此,每个现场都已做过手脚,
直接对称于新与旧的炼丹炉。
哦。秘密的旋转。假如内在的火,
一直在完美我们的分寸,
或许不必等到去过冰岛,
我们就能用我们的身体收藏
一座袖珍火山。哦。蔚蓝的悬念。
无论它选择的敏感时机是否合适,
它的喷发,都适合给黎明断奶。
被秘密雕刻过的月亮
那是一种自觉,涉及
神秘的快感隐现在
中秋的月光像斧子的刃。
等待着收割,但那安静在大地的黑暗中的
收割的对象,既不是作物,
也不是我们像红高粱。
来自记忆的邀请。或者更严格,
只有向你发出过明确的邀请,
你的记忆才会触动我们的秘密;
你才有机会,越过生存的底线,
潜入我们的轮回。回溯起来,
很多细节,都像是用一个矛盾纠正
世界的寓言。当野狼和大熊
在附近交换仿佛和我们无关的
暧昧的猎物时,黑暗如砧板,
沿虚无的尺寸,占据了整个天空。
但是,作为被雕刻的伴侣,
月亮并不想吓唬你。
凭心而论,在你见过的
所有斧子中,只有它是圆的。
它以圆为宿命,热衷于神秘的团结,
并不在意我们究竟能看懂多少。
总得有人出面替我们给万有引力一个面子吧。
它只是偶尔有点像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