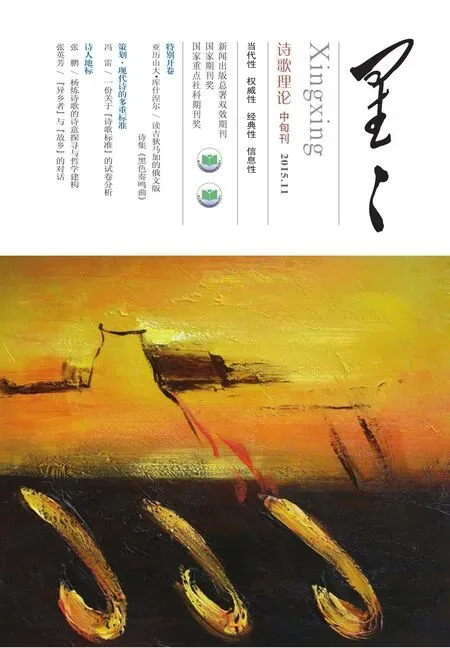张力语言:诗之回归可能
——读陈仲义教授《现代诗:语言张力论》[1]
董迎春
张力语言:诗之回归可能
——读陈仲义教授《现代诗:语言张力论》[1]
董迎春
语言本体回归,成为现代诗歌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陈仲义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耕耘“张力”这个诗语码头,统摄中西张力研究成果,精心梳理“张力的运行与诗意”结构图,“最需要做的功课,还是老老实实、不遗余力把诗语中那些细大不捐的张力好好挖掘出来,做出合理的阐释与整合”[2],为当代诗歌语言本体研究、当代诗写语言诗性回归提供了一面诗学铜镜,照出了当代研究的得失、是非,其学理性、前瞻性体现出前辈学人丰富学识与理论高度。
1943年罗伯特·潘·沃伦在同时新批评开端人物艾伦·退特的“张力”研究基础上给张力列出了具体的“清单”[3],张力在这儿既是诗学追求,也变成了语言品质。“张力,不仅活跃在语词内部,更多时候是溢出内部,带动语词与周遭世界发生关系,表现出语词陌生化与亲近化之间的‘较量’,也由此分化出现代诗语两大流向——‘去魅’与‘返魅’的博弈。”[4]在诗之所以为诗这一前提下,张力是诗性、诗意追求的过程,也是最终在文本纺织的间隙生成审美意义的文学空间。文学性的审美空间生成离不开张力,张力在语言结构中生成。“诗的意义取决于张力
多寡,诗的成功取决于在结构关系中的‘位置’。诗意的浓郁寡淡,许多时候取决于张力的强弱。当然,张力不是语言学的真空装置,它在诗中的存在,是诗语质料在历史、社会、现实与心灵的综合结晶,它隐含着诗性思维在历史与现实上的逻辑投影,最后修成诗意的正果。”[5]这个“张力”,既与中国诗学传统一脉相承,是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滋味、神韵、妙悟、意趣、意境,又深深扎实于现代诗歌的西方理论,是西方理性细读意义上的可描述的文本结构。
究其影响,陈仲义教授的《现代诗:张力语言论》给我们以下启发:
第一,“张力”命名的探索与实践,丰富了“现代诗”的理论建构。他将“张力”分为“对方性张力”、“互否性张力”、“互补性张力”,并从“远—近”、“小—大”、“时间与空间”“因—果”等多重维度展示张力生成的诗语印迹与诗学规律。“张力不止于有机二元论,更是关系主义的产物。张力是对立因素、互否因素、异质因素、互补因素构成的关系结构。”[6]这种种差异性、对比性、矛盾性、悖论性的相异关系,使诗语产生联想性、审美性的文学空间。从秩序等级将“张力诗语”分为三个“层级”:“词张力”、“句张力”、“篇张力”,它们形成不同的“样态”:弱张力、强张力、短张力、长张力、分张力、合张力、显性张力、隐性张力等[7]。这种程度上的差异性,归纳了语言抵达的审美效果,“诗歌文本的张力与审美诗意是由各种大、小、强、弱、集中、分散、有形、无形、显在、隐在的张力样态构成的。”[8]他还进一步指出张力的差异形态:“跨越式张力、蹦床式张力、断裂张力、空白张力、悬疑张力、宕开张力、虚实张力、临界张力、合成张力、散装张力、空白张力、
集合张力、节奏张力、错位张力、搭配张力、形异张力、排列张力……”[9]这些命名与区分,将暧昧模糊的语言形态精确成不同的诗语形式与思维样态,对现代诗的写作无疑提供了一种思维上的引导,进一步深化了“张力语言”的话语研究。
现代诗“意象”的经营与发展,是现代诗语的重要构件。它一方面扎根于中国传统诗学重视意境的美学形式;一方面与西方的智性诗歌写作的沟通、融汇,经历了从“浅表意象——深度意象——审智意象的变化轨迹”,“智力、理智等理性化沉淀秩序,又有直觉、智慧、领悟等感性的穿透机动”[10],“经由想象、直觉和变形的多重作用,达到出新与质感、成色与深入的状态”,这种“深度意象”与“审智意象”成为递进式的诗性捕捉与张力勘探,让传统的意象写作拓展为深度、难度的审智写作。“诗语是诗歌的‘基石’,又是诗歌内部高难的建筑与‘装潢’。”[11]吸取西学理论,通过诗语形式的剖析,厘清纠结不清的诗学问题,通过张力语言的理论建构,进一步规范与启发当代诗歌的理论研究与诗语写作。
叙事与抒情、意象与非意象化写作,同样是当代诗歌缠结不清的理论问题,意象写作自然为读者熟悉,但是非意象化的叙事作为诗学尝试的形式常为人诟病,陈仲义教授从现象学视角区分了“意象”与“语象”,并统摄于张力语言结构,“张力同时是朝向陌生化诗意开放的‘引擎’,因而有无张力是区分诗与非诗的主要界线。”[12]用“事实诗意”这一概念描绘了非意象化写作的话语特征,“所谓事实的诗意,是面对人、物、事、理的‘事实性’,保留其全部的准确、具体和充盈”[13],“多与散装性张力或‘尾张力’结缘”,它也被描述为“卧底式张力”“‘卧底’式的张力,也称隐形张力”[14],“隐形张力”我也
将其称为罗兰·巴尔特《明室》里“刺点”,它不但盘活了直接、单一的叙事话语,而且让非意象写作的叙事的“事实诗意”在“刺点”处聚焦,从而铺展成语言的“隐形张力”,使非意象的叙事诗在当代诗写中产生重要影响的直接原因,“在诗中制造‘短路’却能撞击出绚丽的辉光”,“张力的奇异之处就是让诗语短路或饱和”,“张力是通向诗意的‘引擎’”。[15]
他在考察杨黎、吕德安等作品时,指出了口语、叙事类诗歌“语感”产生的诗学价值,指出:“语感是生命体验透明的中介和外化形式,生命体验是语感的‘内在组织’,两者声应气求,具有高度和谐的同构性”[16],“口语诗彻底粉碎那些远离生命、远离生态、封闭在象牙塔毫无生气的操作,使真正的生命体悟自然地自动流淌。语感催化了的口语诗是生命与语言同构的出路,它为构建诗语的另一极做出了历史贡献”[17],“口语诗因语感、也因张力获得了疯长”[18],当然,他也强调了写作上的警惕“沙化”(雷同化、复制化),“必须责无旁贷地撑起张力那坚硬的下颌骨,控制好牙床与舌头,防止轻桃的声带肆涡震荡,把诗引向生命体验的伪劣模仿。”[19]在区分口语诗与口水诗时,标准还是指向了“张力”。
第二,绘制“张力语言论”这张诗语地图,将当代西方文论的概念与范畴有效地融注于“现代诗”的汉诗写作与形式诗学的勘探。
张力不仅是内部语言生成的结构研究,同时是外在风格、流向的拓展与延伸。“张力本来从属于语言内部的紧张关系,现在扩展为流向、风格的抵牾,这一两极性分化分流,平添了现代诗可持续生长的又一景观。”[20]异质、陌生化、纵横聚合、能指、所指、含混、戏剧性、反讽、语感,这种种剖析现代诗歌
的范畴成为汉语生成诗写张力的重要构件与基础,推动当下汉语诗歌的写作、诗语研究形式上可描述的表意研究,“张力的神奇在于把诗意引向最大化,诗意的成立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陌生化”[21],“含混成了张力说的成长基点之一”,“反词之说可以看做中国当代诗歌对于陌生化诗语的响应和学理上的发挥。反词是对可公约、可公度的熟词的突围,反词是诗语陌生化的一个鲜明表征。诗人的天职在于每时每刻必须反抗正词、熟词、陈词、便词,也就是每时每刻尝试与陌生化为伍。”[22]这些提法均是将诗语研究统一在“张力语言”这一诗意谱系,使得“张力语言”学说得以系统化、学理化。
一般而言,“张力”属于话语分析,与异质性、陌生化、变形、间离效果、语感等概念处于平等地位,此书将张力变成实践形式与诗语追求,张力也是诗性、诗意的另一种形式表达。“张力是激活现代诗语的‘起博器’,是通达优质诗语短暂却有效的入径,因而张力是衡量现代诗语品质的重要标杆与尺度。”[23]此书将此类相等的诗语范畴统摄于“张力语言论”这一理论大厦之中,建构了当代诗学更为系统化、规范化的诗学理论体系,拓展了当代诗歌语言本体回归、诗性写作的可能。张力既是生成诗意、诗性、诗思、诗美的前提与构件,它是诗的修辞与写作效果。“修辞即张力;形形色色的修辞即是张力不同程度上不等的变现”[24],“情愫、意绪、想象、智性统一‘场’上的化合反应”[25]。
此书的价值所在、前瞻所在,规避了当下诗学研究与意识形态、写作伦理的复杂纠缠关系,让诗学回归语言本体、回归诗性(文学性)的内部的形式理论研究。从现代诗的字、句、行、篇等不同角度归纳出张力生成的条件与可能,特别强调了张力是诗
意生成的效果,“诗语的发生机制来自诗意逻辑,它不同日常生活逻辑——受制于种种理性、分析、秩序的条律。诗意的逻辑是通过体验、感性、直觉经由语言中介,熔铸成非固定、非一致、非因果的‘无序’,并且强调每一次生成都是以崭新、独特、甚至一次性完成的远离因果律的‘链接’”[26],形式诗论一方面注重诗学的技术、技巧的理性细读,也强调诗语本身的特殊的诗意逻辑生成的条件与实质。
第三,“张力语言论”勘探了诗语生成的内部结构,也彰显研究者清醒而深刻的忧患意识与文化立场。
尽管此书很少从意识形态与社会批评发型对现代诗的话语分析,而是深深地扎入到语言内核与形成语言张力的形式探讨,有利于当代诗学研究摆脱意识形态批评,另辟蹊径地指向形式诗学与审美立场。时代每一区域都深深地隐藏着一种体制的厚茧与硬壳,稍不留意我们就滑入语言的圈套之中,“解放语言,清除意识形态污垢、强权政治暴力、教条主义藩萃取、乌托邦神话、非人性话语,建立普适价值的言说。”[27]这种对语言的警惕与勘探自然也指向了诗语的意识形态疏离政治、对抗异化的文化立场。诗学研究本身也意味着研究者的审美趣味与文化眼光,这里面是研究者与诗人作品的融合性的体验之思,“诗语与生命的结合,拧紧了语言与存在的本质关联”[28],生命意识的在场,诗的张力思维,诗语的纵横剖析,推进了现代诗的语言回归,审美化的张力生成的文学空间对当代诗写也产生深刻影响。
我在《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这一博士后报告中就引用“诗写”这一概念,这不单单是当代诗歌书写的名称浓缩,更是陈仲义教授数十年如一日独立研究后对当代诗歌研究的理解与签名。诗学、诗语研究本身指向张力语言的诗性回归,这
一本身折射出研究者对诗的理解与诗写精神。“现代诗的使命之一是对语言的刷新,现代诗语要逾越所谓的准确与和谐的藩蓠,这就要求诗人对被千百万人钝化了的语言世界重新审度,重新塑造。”[29]德里达讲“书写”,这成为西方话语研究中重要的概念,它指向了差异性、可能性。“话语研究并不能完全替代诗语研究。因为话语不能等同于:诗语是诗歌话语的内在部分和特殊部分;诗语是研究话语的前提和基础。”[30]古今中外的诗歌、诗人均是复数概念,指向了差异性、可能性的书写尝试。张力语言的生成正是这一特殊文体的“书写”实践。
现代诗的暧昧性、多向性、暗示性、生长性的话语特征,使得张力语言的本体性探索指向了当代诗学不断生成的可能。诗语、诗写,这些概念不仅体现出他对当代诗学的命名能力,同时也呈现形式研究中的理论归纳与思辨能力。诗语是诗艺与生命异质同构的象征体,“一级是以与生命本真同构,几近半自动言说的‘语感’;另一级是以超语义、混沌为表征的‘语义偏离’,两级动力构成现代诗语生成的基本路径。”[32]此书将其描述出生命感性呼吸的“语感”、理性的“语义偏离”的理性思维。“优质的现代诗语是来自语感与语义偏离的浑然合成,是来自所指与能指离散间的独特张力”[33],诗语研究更接近语言事实,更易挖掘文本背后所表现出来的诗意立场与审美意识。
从“张力语言”理性思维转向具体操作,此书成为当代诗学理论的“探照灯”。“含混——模糊中的歧义多义;悖论——互否与互斥的吊诡组合;反讽——基于表里内外的‘佯装’、‘歪曲’;变形——‘远取譬’畸联;戏剧性——紧张中的包孕、包容等。”[34]这些诗学范畴本身与张力同论,此书将它们统摄于张力语言这一写作的实践与诗意价值追求,汇集于张力语言生成
的诗意机制。这些技巧与方法,不仅总结出西方现代诗歌对汉诗写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让当下汉诗研究融入世界诗歌的“自我生成”与自我签名,现代诗的写作保持对古今中外诗学传统的警惕与延异,“自我生成是指避开文言诗语的同质化,也避开西洋诗语的异化,积极而自觉地在自身内部进行涅槃再生,在大量实验、探索中不断进行自我扬弃,自创新质,它们是构建现代诗语的另一重要方面军。”[35]
此书为“现代诗”的理论研究、诗写实践提供了鲜活的文本诗例与诗写思维。语言本体的诗语研究,表现出研究者前瞻性的学术视野、文化眼光,同时,这种审慎性的“张力语言”的理论勘探也折射出论者对当下诗语写作无效诗写所产生的忧患意识。当然,此书也留下许多尚待深化与辨析的命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如何始终如一地诗学立场评价相异的作品与纷繁复杂的当代诗潮,如何在这众多指涉的诗语范畴里更系统地切近、统摄于张力语言这一诗学谱系,如何在诗、非诗的语言实践甚至在诗的理解偏见中彰显出诗意精神,如何通过语言洞悉时代抵达生命与诗写的友爱在场,我想,这也是陈仲义教授《现代诗:结构张力论》留给当代诗学理论建构“言有意而意无穷”留白与注脚。
1.文中所有标注的引用,均来自陈仲义《现代诗:语言张力论》,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