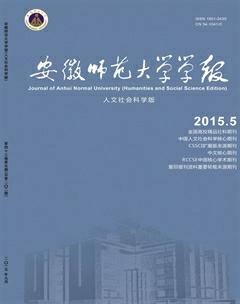刑法目的的规范论之本质
关键词: 伦理规范说;法规范适用说;强势国家主义;个体压迫
摘要: 探寻作为刑法目的理论的规范论之本质,有助于发现其深层次的弊端,并厘清其与法益理论对立的实质。伦理规范说的本质是国家伦理主义,而雅各布斯的规范适用论则在黑格尔哲学与卢曼的社会系统论的基础上,作了一个法哲学的改造,使得其理论奠基在隐藏的国家主义基础上。这两种规范论均存在站在强权的国家一边,压迫个体、忽视个体的弊病。
中图分类号: D9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5060407
“刑法究竟保护什么”的问题涉及到对刑事立法的评判以及刑事司法解释的范式之确定,同时也关系到刑法学体系的建构。客观地说,现阶段我国关于刑法目的的研究,已经普遍接受了大陆法系的法益论与规范论的话语。在此基础上,我国刑法学界一度形成了关于法益论与规范论的学术对立。
就规范论而言,从2000年至今,刑法学界开始较为系统地将雅各布斯的规范适用论思想引介至我国。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规范论在与法益论相抗衡时总体上暂处于下风。应该说,对法益论的研究已经触及到其自由主义的本质层面,①
但对于规范论的研究,则还没有达到论及思想本质的程度。有学者对周光权的规范论立场提出了批评,指出其规范违反说是给规范下了一个雅各布斯式的定义,却赋予了它日本学者式(伦理规范说)的内容。但问题是,这究竟是学者的个人立场问题还是规范论自身的问题?雅各布斯的规范论与日本学者的伦理规范说之间就是绝然对立的吗?两者究竟有无关联?这种规
范论本质层面的探究,有利于我们发现其所蕴含
的问题,厘清法益论与规范论的对立实质,进而考虑是否应固守一方或是对两者予以调和。本文在介绍这两种规范论的观点基础上,对两者的本质进行探讨,指出其所隐藏的深层问题。
作为与保护法益说相对立的刑法目的之规范论立场,大体上可分为伦理规范说与法规范适用说。刑法目的的伦理规范说认为,刑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伦理秩序。其代表人物有威尔哲尔、H迈耶(Hellmuth Mayer)与日本刑法学界的小野清一郎、大谷实、福田平等等。例如,小野
收稿日期: 20150314;修回日期: 201504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FX114);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项目“特殊群体权利保障与犯罪预防研究”
作者简介: 贾健(1983- ),男,安徽芜湖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①当前,对于法益论的探讨较之于规范论显得更为成熟,已有学者对其本质进行了探寻,如苏青《法益理论的发展源流及其启示》(《法律科学》2011年第3期);丁慧敏《刑法目的观转变简史——以德国、日本刑法的祛伦理化为视角》(《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2期)等,就从不同角度指出了法益论与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必然联系,而对于规范论的本质则研究得相对较少。
清一郎提出了反对法益保护的观点。他认为:
违法性的实质是违反国家的法秩序的精神、目
的,对这种精神、目的的具体的规范性要求的背反。违法性的实质既不能单纯用违反形式的法律规范来说明,也不能用单纯的社会有害性或社会的反常规性来说明。法在根本上是国民生活的道义、伦理,同时也是国家的政治的展开、形成,它通过国家的立法在形式上予以确定或创造。而且,这种形式的法规总是适应国民生活的条理或道义观念,以实现国家的目的。这种法是整体的秩序,违背它就是违法。
而法规范适用说的典型代表Jakobs认为,犯罪是破坏了规范,而刑法的目的就是保证这种规范的有效性,即让“弱规范”变得有效,与弱规范相对应的是绝对规范,即数学的逻辑规制和自然世界的因果法则,这些规范具有自己证明自己,自己实现自己的能力,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如果要和这些绝对规范相对抗,就是自己与自己对抗,但是对于弱规范,即不能自己证明、实现自己的规范,这种弱规范的实践取决于人的意志内容,即是否认识到有规范,是否愿意遵守规范。那么这种弱规范就需要一种外力来帮助其证实自己的存在,这种外力就是刑罚,他指出,刑法的目的是保持规范的有效性,“使弱规范稳定化”。社会规范的实践性只能依靠这种方式获得补救:破坏规范的行为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的;即使本身不是错的行为,也应当按照“错”的来看待。在刑法上是以刑罚效果的赋予来展现的。因此,刑法所力求保护的正是一种对规范同一性的适用。而之所以要使弱规范稳定化,其根本的目的是想通过维护规范达到社会的稳定。因为,规范是社会的结构,是规定人们之间那种可以被期望并且不是必须考虑其对立面的关系的内容的,涉及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涉及某个个体及其心理状态,因此,规范是一种社会事件,它的稳定就是社会的稳定。那么,这两种规范学说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两者之间又是否有关联呢?
国家主义与伦理主义:伦理规范说的本质
持伦理规范说之观点的学者中,威尔哲尔与小野清一郎无疑最具代表性。选择威尔哲尔,是因为他的学说既被作为法益学说史中由确定期向纳粹挫折期过渡的一个重要承接点,又被视为规范论的代表人物。选择小野清一郎,一是因为其理论根基既有西南德意志学派的哲学思想,也有国家主义思潮,还夹杂了东方传统佛学,二是同为伦理规范论的团腾重光、福田平等人正是其弟子,或多或少也受其影响。这里即以两者的伦理规范论的观点为样本,对其本质进行考察。
威尔哲尔的伦理规范说的本质是新黑格尔主义的绝对整体性的国家主义与伦理主义。当然,威尔哲尔还深受现象学影响,表现在其目的行为论中,其法益的内部构架也是受哈特曼的实在价值哲学影响。
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改造成某种具有非理性和经验特征的精神性存在。如,布拉德雷认为绝对经验就是知觉经验,但又并非是个人的主观经验,而是一切有限经验的整体,“宇宙的每一成分,感觉、感情、思想和意志,必定都包括在唯一的、无所不包的知觉之中”。这些都是实在的,而实在就是满足人们各种要求的东西。并且这种绝对经验是一种“和谐的全体”,是“杂多的外在性完全消失了的杂多的统一”。因此,他反对休谟经验论所主张的个体先于整体,个人自由与幸福就是道德善的观点,认为这种功利主义即使强调大多数人的幸福,也仍是原子式的个体的集合,不是超出个人之上的整体。在他看来,道德的善在本质上是超越个体的整体,个人只有投身和实现于整体之中,与整体合二为一,才有道德上善,才能实现自己的幸福和利益。在政治伦理学中,这种绝对经验的化身就是国家和社会。endprint
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威尔哲尔虽然承认有由行为规范所保护的且与个体经验相关联的法益,但仍然认为“就整体刑法而言,刑法的任务是保护基础的社会伦理心态价值”的观点了。其实,这种个别的经验法益与整体的社会伦理心态价值之间的矛盾,正是来源于新黑格尔主义个别的知觉经验对整体的绝对经验之对立与服从。另外,威尔哲尔不但强调社会伦理的绝对地位,还强调国家的绝对性和权威性,他认为:“
刑法的最重要使命,在于积极的、社会伦理性质的方面。即在现实上背反了法的心情的基本价值的立场,刑法通过对这种行为的排除与处罚,采用国家所可能使用的最强烈的方法,来显示这种不得受侵犯的积极的作用价值的效力,形成国民的社会伦理的判断,强化国民对法的忠实心情。”
这显然是受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并且就“国家用刑罚来塑造社会伦理,强化国民对法的忠实心情”这一点看,是与法规范说的观点有着某种程度上的暗合。
小野清一郎的伦理规范说的本质是西南学派的绝对国家伦理主义。正如团腾重光所说,“他将德国西南学派的文化哲学与佛教教理融为一体,以作为其刑法理论的基础。”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文化价值哲学代表人物文德尔班认为,在我们日常接触和认识到的“事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价值”世界,前者是表象的现象的世界,后者是本体的自在的世界,“事实”世界之事实命题表示两种表象的内容的相互归属关系。例如,这朵花是白的,表示的是花与白的关系,而价值命题则表示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这完全取决于主体的意志和情感。对此,文德尔班为了与相对主义划清界限,又提出特殊价值与普遍价值,前者是存在于个别人意识中的价值,后者存在于一般人的意识之中,取决于一般人的情感,是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即“应当如此”的价值,而伦理学的标准即取决于此,“众所公认的标准是一种正确的标准,个人的决定必须服从它”台湾林立博士从Jakobs的“敌人刑法”入手,认为Jakobs“只注意到‘规范被破坏、因此国家为了重建规范就必须加以反击,但是却从来没有兴趣愿意进入社会学或经验的领域探讨‘为什么有人要反抗体制?国家如何以正义化解反抗、实现自保?他这种思想的方式,正是导源于其对Kant形式主义思维方法的执著。”对此,内地有学者提出质疑并基本赞同诺依曼的观点,认为“在雅各布斯本人的著述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其基于整体秩序观和社会系统论的立场对康德先天理性法概念的异议。”认为雅各布斯正是坚守了黑格尔的主体相互生成理论,以反对康德的先天主体性哲学,这种借鉴“展示了其在现代福利国家的背景下超越自由主义法学范式的努力”。还有学者认为Jakobs的规范论的本体思想是社群主义与法实证主义,“可以看出Jakobs的规范论反对法益论,强调规范有效性维持的绝对理念,似具有浓厚的法实证主义色彩。”
上述黑格尔的刑罚学说、康德说与实证主义说的观点,看到了Jakobs刑罚绝对性的一面,虽然不能说是错的,但至少没有全面分析Jakobs规范论的思想根基。就此而言,上述对于林立先生康德说的批判,虽然不能说批判错误,但某种程度上是错位了。
至于黑格尔主体相互生成说、卢曼社会系统说,笔者基本赞同,但Jakobs对这两者均非完全“坚守”,而是有所“改造”,正是在这种“坚守”与“改造”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规范论所呈现出的社群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本质。这归根溯源,表现在Jakobs的人格体生成理论中。
Jakobs的人格体、规范与社会可谓是一体生成的。其规范的产生确是对黑格尔主奴关系论述的继承,两个个体在相互渴望承认的斗争中进行战斗,一方战胜,成为主人,另一方则成为仆人。但Jakobs指出,“仅仅用征服的事实也不能解释仆人在劳动中发现他的定义,他同样可能因对其屈从性生存感到沮丧而撤回到其动物性中去,至少是得留在单个人的个体与有害的自然做斗争时所面临的阶段上。”因此,Jakobs提出:“
主人要想维持这种承认,就必须将仆人强制地纳入主人的图示当中,并且也只有同样地赋予了屈从者一种地位,使得屈从者能够把他们的劳动理解为在为群体履行任务,这样才在主人和仆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平等的人格,否则主人仍然无异于在驱赶一匹劳作的马而已。主人是通过为屈从者制定一种设置职业阶层或者授予管辖领地式的宪法,即给每一个屈从者都制定一种职业的角色,来赋予其地位。”
由此,群体间的规范即产生——“规范是社会的结构,换句话说,是规定人们之间那种可以被期望并且不是必须考虑其对立面的关系的内容的” 黑格尔就是从“斗争”与“劳动”中获得的,而Jakobs为了维持人格的稳定,则引入了“主人强制授予宪法即社会角色”的概念,正是“角色”使得匿名社会的沟通成为可能,或者说,社会及其稳定正是由“不同职业者的角色”所构成与保障的。人们“不需要推测或者查明售货员不是诈骗犯之后才去他那里买东西,也不必忧心刑法教授会在大学课堂上宣扬纳粹。”这确是社会系统论的观点。
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为他的这种循环地赋予各罪立法正当性的方式辩护,换言之,又在反对法益论讨论除罪化的过程中,试图解释刑法设立这些罪名的合理性(这或多或少逾越了他的理论根基),例如,Jakobs反对废除亲属通奸罪认为:“
下一件要做的是允许从所提到的犯罪行为中取消对亲属通奸的禁止——理由是,这种行为缺乏一种利益侵害,但是,人们对这种理由是要摇头的,就象这一点在过去被错误地认识了的一样。但是,只要社会还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家庭,从婚姻这一面说,家庭角色与性伴侣角色的混淆就损害了一种利益,即家庭明确的结构组成。”可见,这与上文中提到的小野清一郎的“一君万民、君臣一体”之国家道义观一样,均是紧随上述纳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刑法(刑罚)目的(任务)观而作的表述。
因此,威尔哲尔与小野清一郎的社会规范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将国家和社会当做超越于个体的先验共同体,并当做刑法的保护对象,这隐藏了排除“所有非政治性权利资源和社会自由管理的制度”的危险。即国家与社会排除传统政治社会文化的自我约束内核,产生压迫个体的异化。endprint
(二)法规范适用说的问题
Jakobs意义上的人格体的自我意识虽然是在交往中从他者处获得,但是这种获得是一种单向的被施予。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格体概念在Jakobs的法哲学前思中是没有实际地位的,因为人格体概念的本质就是为了用以解释人在从蒙昧状态进入规范社会中的一种身份转化,为法律的合道德性何以可能提供一种基础性的论证。即是说,人首先成为了人格体之后才可能为规范的合道德性创设前提。简言之,规范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由人格体所赋予的,或者至少是与人格体同源的,而不是说规范赋予了人格体的地位。实际上,用Jakobs的规范发生学指导现实,极易发生对立法的盲从,即立法者成为这里的主人,例如,就安全的规范保护来说,“
立法者必须在此范围内对事先规定的目标进行集中管理,即作出规定,在什么行为方式下,某个人就扮演了杀人犯的角色,即使这个人本来持有另一种个人观点。这就是说,如果立法者作出规定,那么就要禁止醉酒开车,禁止放火烧用作住宅的建筑物,还有其他更多的对抽象危险性的全面禁止。”另外,(5)如果敌人具有通过行为从根本上破坏现实社会的基本法规范的危险,则可以动用死刑。这一方面,体现了强烈的国家主义意志。既然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主人所赋予的,那么主人当然也可以将其排除。但人格体相互生成的本意在于赋予规范理论以先验性的正当基础,正是因为设计的内核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主人也能够根据现实的行为将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随时剥夺,那么,这就破坏了人格体理论通过先验性的设定赋予规范以正当性的预设前提,等于是人格体理论自己否认了自己。如同社会伦理规范论中的超实体脱离其社会伦理原初的自我规定而滑向没有控制的纳粹共同体一样,是一种理论的异化。这制造了“人”与“非人”、“市民”与“敌人”的二元对立,“敌人”所要面对的是整个自认为是社会或国家的实体。另一方面,从上述界定敌人的几个关键词中,我们看不出明显的界限,例如,何谓超出“原则性”与“恒常性”?何谓“根本性”?实际上,这些只能从“态度”上去猜测。无论如何,对当今社会任何一种主流文化来说,如果一个理论所预设的超实体容易失去自我控制,从而滑向与个人的完全对立方向,进而压迫人,那么这个理论本身就是应该否定的。
总之,威尔哲尔与小野清一郎的社会规范说最终是滑向了纳粹,Jakobs的法规范适用说,也并非如纯粹的社会系统论一样可以通过系统内外部的协调维护整体的稳定。正因为其在规范系统运作的前阶段即人格体理论中,对黑格尔主奴哲学做了一个“小手术”,埋进了日后国家主义的强权基因。因此,其理论实际上即便是连社会系统论所具有的保守主义之稳定性也达不到,这不但如社会系统论一样应被批成是无视个人,而且还应被批具有压迫个人的潜在危险。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伦理规范说与法规范适用说虽然在理论架构上有所区别,但从背后的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两者具有实质的一致性。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周光权虽然给规范违反说是给规范下了一个雅各布斯式的定义,又赋予了它伦理规范说的内容,这不能说是犯了体系性的错误。因为即使是雅各布斯的法规范适用说,仍是与国家伦理规范暗中勾连的,两者并非绝然排斥,相反,两者的结合可以弥补各自理论的弊端。例如,法规范适用说可以减轻伦理规范说被指责为明显的国家主义的质疑呼声,而伦理规范说可以赋予法规范适用说以更强的解释能力,从这个角度看,规范论内部有必要进行相互的借鉴统合。
事实上,从规范论的知识论本质出发,有助于清晰地观察到规范论思维和法益论思维的对立实质,即法益理论立足于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站在个体一边考虑刑法保护目的立场,而规范论则站在国家、社会等超个体一边,考虑刑法的保护。从两者的思维基点来看,正如德国著名关系论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言,某些群体的人的思想一开始就在人的各种联系的自身法则上兜圈子,为了说明被他们观察到的人的各种联系的法则,便不自觉地另外设想出一个自在于个体彼岸的实体,为了说明他们的社会规律,他们还杜撰出某个“团体精神”或某个“团体有机体”作为这些规律的载体。而另外一部分人的思想则集中于人类的个体方面,他们不自觉地这样设想:对于个体之间联系的结构和法则的说明,必须在个体的“本性”或“意识”中去寻求,人们在进行思想时必须从个体、从“原子”、从社会的“最小单元”出发,以便在思想中可以根据它们——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某种事后出现的东西——彼此的关联,来建构社会。这种人类思维的对立在刑法理论中的最高体现,实际上,就是当前刑法目的理论中的法益论与规范论的对立。当然,这一结论并非显而易见,因为无论是法益理论还是规范理论均是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才逐渐显露出其依存于个体或社会的实质。某种意义上说,个体的思维与社会的思维具有对立的必然性,但个体与社会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并非是彼此处于彼岸的,由此决定了法益论与规范论必须要考虑如何融合的问题,站在任何一边得出的解释结论都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因此,二元论的规范论立场有其方向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欧阳本祺.规范违反说之批判——与周光权教授商榷[J].法学评论,2009,(6): 38.
[2]张明楷.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5-26.
[3]G·雅各布斯.罪责原则[J].许玉秀,译.刑事法杂志(台湾)(40),2: 53.
[4]G·雅各布斯.刑法保护什么:法益还是规范适用[J].王世洲,译.比较法研究,2004,(1) :102-106.
[5]全增嘏.西方哲学史:下册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01-512.
[6]Hans Welzel.Das Deutsche Strafrechtl[J]∥奈良俊夫.目的行为论与法益概念.刑法杂志,1977,21(3):292.
[7]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276.endprint
[8]乌尔弗瑞德·诺依曼.国家刑罚的法哲学问题[M]∥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冯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8.
[9]林立.由Jakobs“仇敌刑法”之概念反省刑法“规范论”传统对于抵抗国家暴力问题的局限性[J].政大法学评论(台湾),2004,(81):45.
[10]张超.先天理性的法概念抑或刑法功能主义——雅各布斯“规范论”初探兼与林立先生商榷[J].北京:北大法律评论,2008,(1):108.
[11]黄经纶.对抗“敌人刑法”——浅析的敌人刑法与德国法下客观法秩序维持之冲突性[J],刑事法杂志(台湾),2004,(5):95-96.
[12]京特·雅各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M].冯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8-29.
[13]张东辉.费希特的法权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65-266.
[14]京特·雅科布斯.行为·责任·刑法——机能性描述[M].冯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18.
[15]郑逸哲.德国刑法学者与纳粹主义[C]∥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六秩晋五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刑事法杂志社基金会,1997:788-790.
[16]韦恩·莫里林.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M].李桂兰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319.
[17]George P.Fletcher,The Grammar of Criminal Law,American,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230.
[18]冯军.死刑、犯罪人与敌人[J].中外法学,2005,(5):615.
[19]Arthur J.Jacobson.Autopotietic Law:The New Science of Niklas Luhmann[J].Michigan Law Review, 1989,26(5):1672-1677.
[20]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M].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0-21.
责任编辑:汪效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