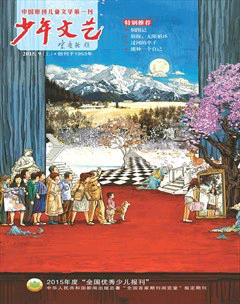橱窗
林辛格

那条纯白的舞裙挂在那儿很久了,从四月到现在,静静地,像从未沾染过灰尘。她每次背着双肩包从橱窗前走过,都要望上一眼,双眸闪闪发亮,然后匆忙离开——她害怕女老板刻薄的眼神。
她家不富有,连小康也不是。老街两排灰蒙蒙的筒子楼中的一间,便是她的家。正是傍晚,母亲和邻居大声玩笑地边嗑瓜子边打麻将,她不屑地朝家门走去。红漆的大铁门已锈迹斑斑,“咯咯吱吱”地呻吟着。
桌上摆放着中午剩下的一盘胡萝卜炒笋干,厨房里的碗堆成了小山。她一边埋怨着母亲的懒惰,一边挽起袖子开始清洗碗上残留的油渍。一个肥皂泡映着夕阳折射出五彩斑斓,她看着入了神,一袭白色仿佛又在她面前闪过。
她在学校的文艺表演上见过这种裙子,那是穿在同班的文艺委员蒋怡身上。白色的蕾丝花边轻轻摆动,顺着蒋怡随音乐摆动的舞步,灯光闪耀着裙身上的亮片,光彩照人。她在台下一个劲地叫好,心中却沉淀下了一个梦想。
她叹了一口气,地板已传来了脚步声,父亲拖着一身泥水回家,粗鲁地打开一瓶啤酒,“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大口,大声发着脾气。她小心翼翼地绕过父亲,回到自己房间。
“你是个非常有天赋的孩子。”学校的舞蹈老师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学校组织的群舞上,她表演得很好。她很开心,回家后美美地咀嚼了好一阵子,只是终究不敢面对。她不是那种活在阳光下的孩子,总是低着头,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经常在老师叫她回答问题时,哆哆嗦嗦不知所措,等待着全班的起哄。
母亲气急败坏地甩门而去,还听得到她的大声怒吼,想必又输了钱,已经不止一次了,她受够了这样的生活,像一只丑小鸭。
她在纸上画着,一条条的白裙子,如丝绸般柔软,雪一样洁白,还有闪闪发光的亮片。一天中午,一个平时调皮的女生大声嚷嚷,下周有舞蹈比赛,《天鹅湖》,她冲动地让同学帮自己报了名,在心中一遍遍默背烂熟于心的舞步。她曾在舞蹈室看老师帮同学们排练,用打杂的借口待在那儿整个下午,替同学递递水,保管保管书包,能偷偷记下一点儿就是一点儿。她很满足,她有舞蹈天赋呀!
旋转,踮脚,摆臂,她在镜子里一遍遍注视着自己的脸,又叹了一口气。没有裙子,怎么去参加比赛呢?她想去求母亲,只是怕,不敢面对。可是终究还是去了,用尽量委婉的语气。母亲骂骂咧咧,正朝着父亲大发脾气,父亲摔破了一个碗,满地白碎片。
“妈,我想参加舞蹈比赛……”她小心翼翼。
母亲半晌不说话,最终叹了一口气。她扳过女孩的脸,似乎在努力思考着。女孩知道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而舞蹈用的白裙子,实在是奢望,慢慢回头走了。母亲却叫住了她:“只用一天,对吗?”
“是的。”她说。
她不知道母亲是如何说服那个女老板的,比赛那天,她穿着白裙子来到了学校,有种满满的幸福感,推开舞蹈室的门,却一下呆住了。里面空无一人,根本没有同学说的舞台和聚光灯。后面传来女孩子的笑声。
“好傻呀,被骗了。”
“真是个白痴。”
她早该知道是个骗局,她站在那儿,只听见心里一个东西破裂的声音,好久好久。
指导老师 黄 忠 倪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