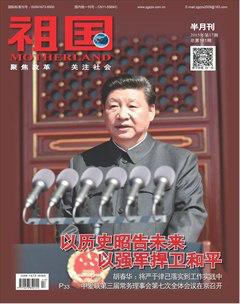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岳思平
目前,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战问题关注度极高。其中,关于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成为不可回避的最为敏感的热门话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的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说成是国民党抗战、共产党不抗战,或者说是国民党及其军队与正面战场发挥了主要作用,蒋介石是第一号的抗日民族大英雄等等。这既是历史问题,又成为现实性很强的政治问题,成为了政治安全问题。
众所周知,在如何评价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即谁抗战谁不抗战、谁抗战地位高低和作用大小之前,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答的,就是国土如何丢失的,日本是如何从沈阳柳条湖打到北平卢沟桥和上海虹桥机场的?换句话说,日本为什么在侵占东北后,进而侵入华北、华中和华南的?除了敌强我弱的根本原因外,就中国内部来说,则与国共两党两军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
全国抗战时期,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战略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抗战是比较积极的。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显而易见,即使著名的庐山谈话,蒋介石仍存在与日和谈的幻想;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予以积极的评价:“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直至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其抗战方针和政策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先后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和武汉会战等,发挥了主战场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这一战略阶段,八路军首取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以3个师的主力参加太原会战,先后取得雁北关和阳明堡等战役战斗的胜利,从而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在整个抗战期间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作战。八路军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鏖战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捷报频传。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相继进行了蒋家河口和韦岗等战役战斗,驰骋于大江南北、江淮河汉之间,连战皆捷。从而发挥了战略支队的作用,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共同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和1至3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同时,在全国抗战初期的太原会战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均参与了战役指导的重大问题。中共地下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卢沟桥抗战时的第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中共党员,第110旅长何基沣随后参加共产党,台儿庄冲锋陷阵的第2集团军骑兵连长刘兰斋和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等均是共产党员。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全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被迫转入长期战后,由以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为主,逐渐移其主力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认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军民是日军的最大威胁和心腹之患,寻歼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摧毁抗日根据地日渐形成重中之重。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敌人的文献中,也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日本陆军省决定在治安地区进行必要建设与施加军事压力相结合“逐渐形成工作重点”;“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第70页。)。如其华北方面军决心“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积极具体地开展各项工作,并且努力尽快恢复治安。”关于作战问题,要利用增兵的机会,“除计划扫清黄河以北敌军外,主要应对共军根据地进行歼灭战。”(《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362、365页。)据此,从战略相持阶段起,关内侵华日军集中58%至75%的日军和以国民党军正规投降部队为主体组成的90%至100%的伪军,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其残酷性、野蛮性和频繁性,均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略攻势”。于是,从1939年6月至1940年7月,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代号“桐工作”的诱降工作。期间,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一时间,国统区大后方人心躁动,中间派对时局悲观,亲日投降派又异常活跃起来,蒋日妥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仅仅抗击了日军有限攻势,取得了昆仑关大捷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有限的几次战役的胜利,大部分时间出现了多年的沉寂状态,基本保持了战线的相对稳定。值得称道的是,其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直接抗击日军对缅甸的进攻,支援英缅军作战,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坚决执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任务,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百团大战的胜利,打得日本帝国主义惶惶不可终日,惊呼对“对中共再认识”。华南抗日游击健儿活动在南粤五岭地区,时有斩获。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大显威风,铁道游击队、雁翎队和敌后武工队层出不穷。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为此叹服,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写道:第二次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美国新闻处纽约电,1945年7月9日。) 仅1941年和1942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就粉碎了日军1000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扫荡”达27次。实事求是地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反“扫荡”面对的日军兵力,多次达到或超过正面战场号称20余次会战中的日军规模,更不用说在此后发起的攻势作战行动,我们只是没有称会战罢了。
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在战略反攻阶段,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反攻。1943年下半年,八路军山东军区的抢占沂鲁山区、诸日莒山区战役和第129师、冀鲁豫军区发起的卫南、林南战役,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1944年,战略反攻的局部反攻普遍展开后,敌后战场的春、夏、秋、冬季反攻势头强劲。1945年上半年,八路军和新四军持续发动了春、夏季攻势作战。8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军民迅速展开全面反攻,一直持续到日本帝国主义于9月2日正式签字投降。1945年8月9日至年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方面为和平民主努力,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防止内战发生;另一方面继续与帮助国民党军队的日伪军作战,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一次作战,少则俘虏日军100余人,多则上千人。如八路军11月临城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余人,新四军12月高邮作战中俘虏日军890余人。中国抗战胜利前后,日军和伪军为什么帮助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呢,难道不令人深思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