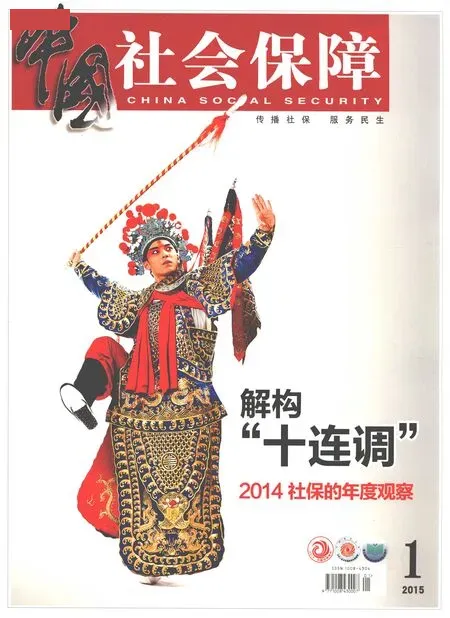“责任”与“资格”的思考
■文/周弘
“责任”与“资格”的思考
■文/周弘

周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社理事会理事、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
早年阅读有关社会保障的历史文献时,总有两个概念若隐若现,萦怀不去,一个是“资格”,另一个是“责任”。我发现,人类社会总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征问,“哪些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得到帮助?”(资格), “应该由谁来提供帮助?”(责任),相应地还有“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提供帮助?”
此后,随着更多的阅读,有关“责任”和“资格”概念的认识就连成了一条线索。无论哪个时代,社会救助的提供者都会设法界定接受帮助的资格,欧洲的达尔文教派区分“有罪贫穷”和“无罪贫穷”,认为因“懒惰”导致的贫困不应当获得救助。英国中世纪晚期出现的“次等资格”(或“更少资格”)的概念影响久远。当时的英格兰政府还提出“政府责任原则”概念,认为政府没有责任救助那些有劳动能力而行乞属于“次等资格”的穷人。“次等资格”原则认定,贫困的根源首先是个人的懒惰,贫困是“个人责任”。 “次等资格”主导下的政策是政府提供最低限度的救助。
工业化是改变个人责任概念的最主要的动因。工业化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社会生活方式的转换和社会风险的变化。农业社会中的主要社会风险,如战乱、饥荒和个人不幸遭遇等,让位于结构性失业、病患、老龄等,以及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严重失衡。个人任凭如何努力也难以抗衡结构性社会风险。社会开始呼吁互助,新的社会财富和税赋方式也使共享式的救助成为可能。“个人责任”开始让位于“社会责任”。庇古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查尔斯·布斯的“贫困线”设定,以及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工人运动最终改变了社会对于贫困责任的认定,社会服务的社会化被看成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此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轨迹尽人皆知,“社会责任”和“公民权利”成为主流观念。共享成为主要方式。没有人再敢使用带有歧视含意的“次等资格”概念。虽然各种各样的缴费或认证确定的“资格”仍然决定着各种福利项目的给付,但人们高谈的却都是“权利”。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责任”观念受到挑战,很多福利项目的设计开始向“个人责任”回归。公民的“社会权利”概念也开始为“自由权利”或“积极的公民权利”所取代,新的权利强调的是个人选择而不是集体责任。责任的内涵也从提供社会救助的责任转变为个人为自身的福利努力工作的责任。
目前,欧洲各福利国家的政府纷纷从比较全面的社会承诺中退出,而只承担有限责任。在向后工业社会、以服务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支撑“黄金时期”福利国家的大工业社会基础悄然发生变化:一是个人化,人们更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自我表达,同时一些传统的社会纽带愈加松弛,这动摇了集体应对社会风险的基础;二是全球化,在资本、人员、商品和服务超出国界流动的条件下,新的社会纽带开始出现,民族福利国家的财政基础遭到侵蚀,社会再分配体制被迫削减。
尽管社会现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仍然存在,工业化社会中的各种组织纽带仍然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因素继续支撑着“社会责任”和“社会权利”观念。与此同时,现实社会也已经出现分化,社会机制相应缓慢转型。此起彼伏的社会抗议继续使用“社会权利”的伦理概念作为理论武器,但却无法有效地阻止现实社会中社会福利削减和社会机制引入市场和个人因素的转型趋势。在观念领域里出现了“社会责任”向社会、向雇主、向个人和家庭分散化的多元现象。未来是否会有新的社会福利伦理出现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