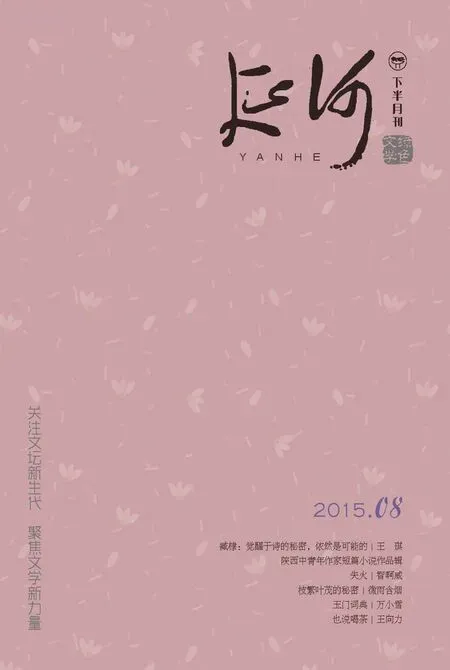失 火
智啊威
失 火
智啊威

智啊威,1991年出生于河南周口,获第四届光华诗歌奖,第一届元诗歌奖,作品发表于《天涯》《诗刊》《诗林》《诗歌月刊》《散文诗》等刊物。
刘建国家的房子在后半夜突然起火了,他裸着身子,呆若木鸡地站在救火的人群中。而他老婆金霞也裸着身子,对着大火一边嚎叫一边跳舞。由于突然起火,惊吓过度,金霞的情绪崩溃了,整个人陷入在一种癫狂的状态中。后来被几个眼疾手快赶来救火的妇女摁住,顺手扯过院中晒麦的帆布,像裹一条老泥鳅似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降伏。而神婆子王秋花赶到后,看着熊熊大火和在妇女手中挣扎的金霞,顿时神情凝重,她思索片刻后,一拍大腿,小跑着从厕所提出尿盆,大喊一声躲开,几个妇女迅疾一闪,一盆攒了几天的尿就从金霞头上浇了下去。这突然的事件不仅惊呆了那几个妇女,就连敲打着脸盆喊救火的大怪,也停止了穿梭,惊愕地看着金霞在尿水中扭曲的脸。
整个套路下来,王秋花一气呵成,然后盘腿而坐,嘴里开始念叨起听不懂的语言。金霞受了那一盆尿,竟神奇地安静了下来。金霞一安静,王秋花像被烫到了屁股似的从地上弹了起来,激动地指着金霞对围观的那几个妇女说,看!魂收住了,魂收住了!
本来金霞就看不惯王秋花的神神经经,又加上这盆尿,两个人的关系便彻底决裂了。
偶尔下地或赶集,但凡走个碰头,金霞的目光就像刀子一样在王秋花身上扫来扫去,恨不得把她大卸八块。而王秋花倒淡然的多,她目不斜视,昂首挺胸而过。
每次金霞在路上遇到王秋花,回家后阴沉个脸,像谁欠了她二百块钱似的。刘建国看到她这副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正巧中午金霞把菜炒咸了,刘建国趁机指桑骂槐。金霞一看刘建国这是要找茬,二话不说端起饭菜倒进了狗盆里。然后回头瞪着刘建国说,狗不嫌弃!刘建国顿时被气的鼻子冒烟。你个娘们儿!反了!他把筷子一摔,跳过来,啪啪,朝金霞脸上就是两个耳光。
后来,刘建国为这两个耳光后悔的肠子都青了。
刘建国凭着一股硬头劲儿打罢金霞的耳光后,等待着反扑。熟料金霞竟没有丝毫要还手的样子,她甚至连摸一下那已泛起手印的脸都没有,只是死死盯着刘建国,冷笑着甩出一句,刘建国,有种!最后那两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射出来的,刘建国不禁打了个冷颤。
金霞的屁股扭出院子时,天迅速黑了下来。
刘建国本想追出去,哄哄骗骗抱抱,这一招在跟金霞搞对象的时候常用,且屡试不爽。无论金霞生多大气,刘建国这一个流程做下来,金霞像一个大白蒸馍一样,软绵绵地就贴在了胸口上。但今非昔比,自从房子起火,刘建国两口子暂住在去广州打工的二胜家后,他的脾气就莫名其妙地变的易怒了起来。待冷静后,刘建国不禁自问,我为啥要打她呢?不就是脸难看和菜咸了点吗?多大个事儿啊?刘建国叹了口气,摇着头买酒去了。
小卖部老板刘前进,在村里辈分很高,正因为辈分高,所以口无遮拦。常拿人开蒜,落井下石。就这,你还不能恼,你一恼,他倒不高兴了:咦,咋?当长辈的还不能给你开个玩笑?一句话把人堵的死死的。
看刘建国闷闷不乐,刘前进戏谑道,建国,少喝点,喝醉了晚上咋耕地?刘前进憋着笑,撅着屁股给刘建国找酒。要搁平常,刘建国准会给刘前进磨会儿嘴皮子,但今天不行,今天他心情很差,眼看着天黑透了,金霞会去哪呢?刘建国摇摇头,拿起酒就走。
回家的路,平常五分钟,今天走了半小时。主要是心里有事,走走停停。想去找找金霞,又觉得这个时候不能服软,这个时候一软,这辈子恐怕就要被她骑到头上屙屎撒尿了!
刘建国心一狠,便反锁了大门。心想跑吧跑吧,有种晚上也别回来!
一瓶酒刚喝到一半,外面就出事了。原来是金霞的三个娘家哥提棍带棒来问罪了。在大门外边踹门边提名带姓地骂。酒意微醺的刘建国瞬间清醒了过来,吓的双腿打颤。心想完了完了,然后拍着大腿像只无头苍蝇般在堂屋里打转,转了几圈后灵机一动,窜出堂屋,翻过墙头,仓皇而逃。
也就是在从墙头上跳下去的一瞬间,刘建国听到大门被踹开的声响。
二叔锁着眉,吐了口烟,幸亏那天你躲的快,不然金霞那三个红了眼的哥,不生吞活剥了你?刘建国蹲在二叔旁边,低着头。二叔说,依我看,你还是赶快去她娘家服个软,赔礼道歉把金霞接过来算了。两口子的,哪有不吵不打的?听到这,刘建国猛地抬起头,嘴唇抖动了几下,想说什么,没说出口。“唉”了一声,头又低了下去。沉默一会儿后,二叔缓缓地说,这是能拖的事?锅被人家娘家哥揭走,被子也被抱走了,不丢人?见刘建国低着头不说话,二叔用脚轻踢了几下刘建国的脚,示意他表个态。刘建国抬起头,一脸委屈地甩着双手说,二叔!我咋觉得自己活的恁窝囊啊?
刘建国接金霞回家,可是付出了惨痛的人格代价。第一次去,吃了个闭门羹。第二次去门开了,老丈人和丈母娘不在,都串门去了。三个娘家哥轮流着把刘建国数落的没脸没皮,刘建国一个劲的低头搓手,屁没敢放一个。这个时候,刘建国十分清楚话不能乱讲,稍微讲错一句很可能就是一顿暴打。
临近中午了,刘建国想着等会儿在饭桌上给金霞认个错,说几句暖心话,这茬事儿就算翻过去了,可事儿哪有这么简单?
金霞做好饭,从厨房走进堂屋,瞥了刘建国一眼,抱着胳膊说:
“一块吃?”
“一块吃,一块吃……”刘建国一脸谄媚地点着头。
“呦,不早说,面不多了,要不我出去借瓢面?”
刘建国一听这话脸红了,谄媚的笑容尴尬地挂在脸上,竟一点一点地僵硬了起来。他咂巴砸巴嘴说,不了,不了,早上家里做的多,我回去吃,回去吃。说罢,抬腿就走。临出大门,刘建国竟鬼使神差地一回头,看到金霞正站在堂屋门口流着泪看他。刘建国顿了一下,金霞迅速背过去身,假装忙碌了起来。
这一趟下来,刘建国被气的直甩头。二叔看他大中午回来了,喊他到屋里吃瓜。刘建国觉得太狼狈了,没脸见人,但毕竟二叔是长辈的,叫去吃瓜,不去也不合适。再说了,最近一段时间,锅被金霞娘家哥揭走后,二叔没少来给自己送饭。送的次数多了,刘建国也不好意思了,摆着手说,二叔二叔,吃过了。二叔却把饭碗推到他手里说:
“咋,恁二叔的饭有毒?”
“没毒没毒。”刘建国忙不迭地说。
“既然没毒,多吃一碗饭能撑死?”
“撑不死,撑不死。”
“既然撑不死,那啥也白说啦,吃了!”
说着二叔坐了下来,在板凳上吧嗒吧嗒地开始抽烟。
刘建国边吃瓜,边讲述上午的点滴,讲到饭点儿被金霞“请”出来时,情绪瞬间激动了起来,瓜皮一摔,脖子一硬,这娘们儿,给脸不要脸!大中午的就是要饭的去了也不能不给一块馍!更何况,我还是他男人哩!
二叔又递给他一块瓜说,吃,先吃。
刘建国接过二叔递来的瓜,鼻子酸酸的。自打娘死了,爹跑后,二叔对刘建国就像对亲儿子一样。二叔是个木匠,年轻时四处跑着做木业活,自打信阳回来后,便烧了家具,从此告别木匠生涯。此后,二叔开始种地,养羊,这么多年下来攒了一些钱,在村里盖起了二层小楼,很是气派。
二叔家盖楼后,上门说媒的便多了起来,但二叔始终没同意任何人。在来说媒的队伍中,就数王秋花比较难缠,她说媒的风格是死缠烂打。但二叔不怕,二叔风趣地说,罢了罢了,俺家被子小,我一个人盖还凑合,要是突然来个女人给我抢被子,那我不是要被冻死啦?王秋花眯着小眼,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二哥,你这是没经验,这搂着女人可比搂着被子暖和的多。王秋花讲话不害臊,但二叔的耳根子倒红了。王秋花趁势揽着二叔的手臂,在自己的两个大奶间摩擦着说,要不试试?这一摩擦,二叔的脸和脖子红透了。他像被烫伤了似的抽出手臂,略带生气地说,王秋花,你这寡守的是个啥?村里谁不知道你明着在说媒做善事,暗地里是在昧着良心挣鸡蛋。把咱刘庄的好姑娘说给王庄的瘸腿子,把王庄的哑巴说给杨庄的壮小伙,图个啥?你不就是图那二十多个鸡蛋吗?
二叔一脸忧思地说,建国,看这局势,不三顾茅庐是请不回金霞这尊大神啦。刘建国嘴里塞满了瓜,腮帮子鼓鼓地说,不去了,打死也不去了,一个女人,要她干球?二叔呵呵一笑,建国啊,你还是小,这一个家啊,缺不了女人。刘建国揪住这个话题,探问道,二叔,女人要真恁好,你为啥不弄一个?
经建国这么一问,二叔沉默了。他目光呆呆地看着升腾的烟雾,陷在了回忆中。他吐口烟,缓缓地说,早年在信阳干木业活时,有一回在一家姓王的主家打组合柜,由于天阴下雨,活干完了,但雨不停没法动身,只得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王家闺女巧秀,十八岁,正是谈婚论嫁的时候。那年我二十,没对象。一来二去,两个人便熟络了起来。渐渐的,彼此就看清了对方的心意。白天在家客客气气,晚饭一结束便悄悄溜到村头的庙里约会。巧秀他爹王铁锤察觉到巧秀那段时间有点问题,但具体是哪里有问题,他也说不清。一天傍晚,巧秀刷完锅正要出门,王铁锤阴着脸,下着雨瞎跑个啥?巧秀心虚,经爹突然一问,有点慌乱。她随即调整了一下状态,故作镇定地说,巴掌大的村,还能丢了?巧秀边说边往外走,约摸着走了十来分钟,我也背着手,慢悠悠地晃了出去。出了路口,就在小雨中跑了起来。
一跨进庙门,俺俩就像两块磁铁一样吸在了一块。不说话,说啥话?说话浪费好光阴!
王铁锤踹开庙门的一霎那,也是俺俩的爱情终结的一霎那……讲到这里,几颗混浊的眼泪从二叔核桃似的脸上掉了下来。
我被巧秀她爹揍了一顿,工钱也没再敢要,连夜离开了信阳。那时候年轻,心里塞满了巧秀,容不下第二个女人,所以成家的事就一直拖。后来年龄大了,又觉得没找的必要了,找女人干啥?王大头花八千块钱从云南买回来一个媳妇,被窝还没暖热呢,人家屁股一拍,跑了。王大头像一头疯牛,满村找,骂骂咧咧地说找回来打死她!我看,也就是过个嘴瘾,人都找不到你打个球啊?这种事村里发生的还少?所以,没劲,真没劲,还是一个人过舒坦。
刘建国听的一头雾水,二叔,你意思往后我也一个人过?二叔一听这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不是我说你建国,这事也不能只怨人家金霞小气,要多想想咱咋对不住人家。你放眼看看,咱村里谁家结婚用的是瓦房?人家金霞虽不明说,但这个疙瘩可在肚子里缠着哩。
唉,刘建国又是一声叹息。
第三,在感情色彩上:东北方言中,很多中性词经重叠构词之后就变成了贬义词,都具有[-褒义]的语义色彩。如:鼓秋、蛄蛹、比划、捏咕等。
二叔沉思了一会问道:“建国,这些年,你说良心话,二叔对你咋样?”
“比亲爹还亲!”刘建国坚定地说。
“那……那你叫一声。”
刘建国猛地抬起头,脑袋有点懵。转而想想这么多年,二叔对自己的照顾,真比亲爹做的都好。可是数年来”爹”这个字在刘建国脑袋里,早已变的陌生而遥远,要突然喊出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叔看建国怔在了那里,赶紧转移话题说,那个金霞啊,抽空还要再去接一趟……
“爹。”刘建国喊了一声,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
二叔突然拘谨地站了起来,手和眼都不知放哪好了。建国看到二叔窘迫的样子,“噗嗤”一声笑了。二叔犯了一会儿愣,转而用手点着刘建国的脑袋也跟着笑了起来。
二叔坐下,突兀地说,建国,我把房子给你吧?刘建国惊愕地瞪大眼睛,头甩的像拨浪鼓。
自从刘建国家莫名其妙失火后,大怪见了刘建国就躲着走,这一切都没逃过刘建国的眼睛。有时候刘建国会故意扯着嗓子,对着大怪绕道而逃的背影喊,路又不是俺家修的,一起走嘛!大怪听了这话,反而逃的更快了。
这几天下来,办案人员一直在村里征集线索,但毫无所获。一天中午,两个办案人员在刘前进店里买了包烟,便坐下来跟刘前进搭话。刘前进撅着屁股,趴在柜台上说,简单的事你们搞复杂了。两个办案人员微笑着看着刘前进,期待着下文。刘前进说,把大怪抓起来,你就不用上刑!他鸡巴就认罪了。
两个办案人员呵呵笑了,其中一个说,要按你说的,那还要法官要警察干啥?找几个打手不久天下太平了?刘前进挠挠头,没话接了。
大怪是个残疾人,右腿天生畸形,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十分夸张。在村里,经常能看到,大怪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串顽皮的孩子,模仿着他的走姿,腿一甩一甩的,组成了村庄里一道奇异的风景。
大怪不仅腿短,舌头也短了半截,说话呜呜噜噜,不清楚。虽不清楚,但日子久了,村里人都能听懂。大怪他爹娘说他的舌头和腿一样,是天生的。但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服村里的那群妇女。他们戏称,大怪的舌头肯定是吃肉时被他自己咬掉的!大怪很不喜欢这话,反驳道,竟瞎扯!我这舌头明明是吃白蒸馍时咬掉的!新媳妇雷天鹅不知深浅,一听大怪说是吃馍时咬掉的,就乘胜追击道,又手贱,偷谁家的馍啦?
“偷你家的了!”
“哼!啥时候偷的?!”
“经常偷,都是你丈夫不在家的时候。”
“有种我男人在家时来偷,不割了你那半拉舌头!”
“咦,你家男人十天半月回来一回,一回来就抱着那俩馒头不撒手,我哪里还有机会?”
大怪说罢,妇女堆里一阵哄笑。直到这时,雷天鹅才明白过来,原来大怪把自己绕进去了。她涨红着脸,看到站在路对面的大怪伸着脖子,正对着她胸前的那两坨肉,一脸陶醉地眯着眼,噘着嘴,作吮吸状。
恁娘那腿!雷天鹅气急败坏地抄起墙头边架菜的木棍,举过头顶要去打大怪。大怪一看局势不妙,转身就逃。别看腿不方便,跑起来倒挺快!那条有问题的腿在极速跑动时,甩动的频率加快,像个奇特的螺旋桨在大怪屁股后面,推动着他在乡村的街道上绝尘而去!
大怪最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尤其是在看到刘建国那犀利的眼神,两个腿就打飘。白天在村里,人们对他指指点点,这等于村里人在集体宣布他的死期将至。大怪坐在床上,越想越怕,越怕腿抖的越厉害。都快四十的人了,连女人是啥味都没尝一口,死了可咋办?
大怪想着想着,顺手从床头拿起半瓶自己用酒精勾兑的白酒,一仰脖子干了两大口后喟叹道,咋搞的球事?我这是咋搞的球事?他边嘟囔边啪啪地拍着自己的腿,仿佛在扇自己的脸。
要隔三年前,刘建国家的这茬子事,咋弄也跟大怪扯不到一块去。那个时候的大怪,为人老实,勤快,热心肠,看到谁家有活,扑上去就干。当然是以帮助寡妇和留守妇女居多,这其中的缘由主要是可以放肆地跟人家插科打诨过嘴瘾。
“大怪,俺家的玉米还没掰完呢。”
“你家男人在,我就不给你干了!”
大怪故意把“干”字说的很重。女人明知道他又在占自己的便宜,但为了能迷糊住大怪来干活,不仅不恼,还故意顺水推舟。
“咦,你哥那小身板哪有你硬实啊!”女人挤眉弄眼地说。
大怪一听这话,舒坦!拍着瘦小的胸脯说,回去吧嫂子!等会儿我去给你干!女的说,那我等你啊。然后笑眯眯走了。
王秋花一个人,家里地里忙不过来,看着大怪这个免费劳力被东家用完被西家用,说心里话,有点眼气。可眼气归眼气,自己也使唤不动。咋使唤?像别的女人那样,让大怪用嘴摸屁股摸胸?王秋花认为自己干不出这种事。
那天,大怪正在给刘前进他嫂子干活,在毒日头下,汗流浃背。王秋花路过地头,顺口道,大怪这么下劲儿啊,改天给你寻摸个好媳妇!大怪一听王秋花要给自己找媳妇,顿时口水就流下来了。
从此以后,有事没事,大怪提捆儿青菜就往王秋花家送,看到有啥活,不等王秋花开口,就扑上去了。王秋花知道大怪的心思,深为自己当初的一句玩笑后悔。不是不愿意说媒,是不愿意给大怪说媒,不愿意给大怪说媒,也不是真的不愿意给大怪说媒,而是不敢在说媒上冒这个险。大怪人丑腿瘸不说,家里还穷的叮当响,家穷人丑年龄大,这”灾情”太严重,王秋花感到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每当大怪谈到媳妇的事,王秋花便顾左右而言他。一拖两年,大怪灰心了,从此开始破罐子破摔。村里人看见都摇头感叹,大怪恼了,彻底恼了。
大怪这一恼不当紧,王秋花家先是树苗断,然后公鸡丢,最后母狗死。
王秋花愤怒极了,她冲到大怪家时,大怪正有滋有味地吃狗肉,看到王秋花,像没看到一样。
王秋花哭嚎着从大怪家跑出来,跑到村里的,唯一的十字路口处,一屁股坐在地上:老天爷啊!大怪他欺负的人没法活啦……王秋花的哭诉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不一会儿就里三层外三层了。村长赶到后,一看到这情况,气的跺着脚骂,狗日的大怪,一个老鼠屎坏球一锅汤,恼了我法办了个七孙。村长骂大怪不是骂大怪,是在给王秋花一个体面的台阶。村长会来事儿,王秋花也不傻,趁势就站了起来,愤恨地说,村长,枪毙他!枪毙他我买一鞭炮放放!
傍晚,村长踢开大怪家门,声色俱厉地说,大怪,你再给我不老实,我就让公安局的来法办了你,我倒是要看看是你的脑袋多,还是公安局的枪子儿多!村长撂下这句话扭头就走。大怪一听到抢子儿俩字儿,吓的脸都白了。
从那以后,大怪戴上了一顶小偷的铁帽子。这对于急切盼望娶媳妇的大怪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如此,谁家丢了东西,死了家禽,必然会来大怪家转转,嘴上说来看看大怪,眼睛却在院子里东瞅西瞅的寻找蛛丝马迹。
刘建国厚着脸皮去接第三次。刘备请诸葛亮也不过用了三次而已,所以这次,他刚一出门,就已经感到胜劵在握了。
老丈人看刘建国来了,赶紧热情迎接,这热情让刘建国倍感温暖和羞愧。可礼仪性的热情过后,老丈人一张嘴就是一盆冷水让刘建国猝不及防:回家?家在哪里?不说孬好,过去还有个窝,现在连个窝都没了,你让金霞跟着你回哪?刘建国的脸一下子红了,羞愧的恨不得把头插进裤裆里去。来之前没考虑这个问题,被老丈人突然一问,倒有些茫然了。是呀,接到哪里?接到二胜家去?这能是长久之计?等过年二胜拖家带口从广州回来了,他跟金霞去哪?刘建国无言以对,低头掰弄着手指。
“回去吧建国,过去不讲了,眼下好歹得有个窝。”
凳子还没暖热,刘建国就被老丈人打发走了。
二叔听完刘建国的“三顾茅庐”后,哈哈大笑。刘建国正唉声叹气,被二叔这么一笑,有点发懵。二叔,笑啥哩?刘建国扬起一脸困惑。
要求房子还不好办?给!二叔把一串钥匙撂在了刘建国面前的茶几上。刘建国看着钥匙,愣在了那里。
“二叔,你这是干啥?”
“不干啥。”
“不干啥?”
“嗯。”
“重了。”
“不重。”
“图个啥?”
“啥不图。”
“啥不图?”
“图个死后有人埋。”
“不给,我会不埋?”
“埋,但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
“不一样。”
二叔递给刘建国一根烟,刚点上,刘建国的眼泪就掉了下来。黑暗中两个男人相对着抽烟,一句话也没再说。
二叔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四年前村里的老光棍刘能去世。刘能五十多,在一个夏夜脑溢血死了,直到尸体飘散出怪味才被人发现。同为光棍,更是感同身受。所以每当二叔想起来这茬子事儿就觉得悲凉。而更为悲凉的是,由于膝下无子女,所以刘能死后,谁来出钱火葬,成了一个大问题。有人提议说大家兑钱,但响应者寥寥。眼看着尸体的气味一天天加重,村长坐不住了,就自己掏腰包火葬了刘能。刘能的骨灰被领回来后,接下来自然是入土为安,可问题又来了,谁来把刘能入土?没有人,因此刘能的骨灰盒就被村长放在了他生前的那两间土坯房里,一搁就是大半个月。后来还是二叔召集了村里的另外几个光棍,请他们吃了顿饭,趁天黑几个人扛着铁楸,抱着骨灰盒,在河坡里把刘能埋了。
刘能的死促使二叔突然意识到生活好对付,而死后,是一个大问题。二叔打量着刘建国家的那两间破瓦房,夹杂在林立的二层小楼之前,心里便开始酝酿盖新房的想法了。
刘建国带着二叔家的钥匙和二叔写的一个无偿赠房的条子,顺利的把金霞接了回来。刘建国骑车带着金霞刚下河堤,就看到从村里冲出一群人,笑声喊声交织在一起。刘建国赶紧停下自行车,打量着奔跑的人群。仔细一瞅,大吃一惊,原来跑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竟然一丝不挂,边跑边兴奋地嚎叫。待那人跑近,刘建国惊愕的差点没跳起来,呀!是大怪!刘建国指着奔跑的大怪,回头对金霞说。
吃晚饭时,刘建国心生愧疚地说,划不来,真划不来。刘建国边吃边摇头。又想起前段时间,在刘前进的小卖部买东西时,刘前进一脸坏笑地问刘建国地耕的咋样了,好耕不?刘前进还没来得及还击,蹲在门口的大怪插嘴道,不好耕,把建国哥累坏了,后来还多亏我帮忙哩!刘前进一听这话,脸红脖子粗地呵道,靠!你给谁耕地了?大怪一看势头不对,站了起来,一脸委屈地说,你忘了么建国叔,当时婶子还夸我活干的好,肯下劲。大怪说罢,胸脯上受了刘建国一脚,趔趄着退到了坑沿,还没站稳,肚子上又受了一脚。大怪”嗷”的一声身体像个皮球似地朝坑下滚去。刘前进从屋里跑出来不见大怪,问刘建国。刘建国朝马路对面吐了口吐沫。刘前进赶紧跑到坑沿,伸头一瞧,坏了,大怪跌进了粪坑里。
大怪从粪坑里爬上来,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跟刘建国拼命,而是拖着一身屎尿,哭着离开了。刘建国怔怔地看着狼狈而去的大怪,有点愧悔。
大怪疯了,光着屁股满村跑,村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大喇叭上宣布,谁捉住狗日的大怪,奖励一百块。一听到奖钱,村里人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得追捕大怪。而大怪疯了以后,像只野兔一样,谁能抓的住?
几天了都没抓住,村长也无可奈何。他找到那两个来村破案的民警说,纵火犯疯了,要抓你们快点抓走吧,整天光着屁股满村炮,吓的女人小孩都不敢出门。其中一个民警反问,说他是纵火犯,啥证据啊?村长信誓旦旦地说,除了他没二人,前阵子刘建国因为话没说对打了他一顿,他会善罢甘休?民警递给村长一根烟说,您先回吧,等我们收集好证据,立刻就抓。
自大怪疯后,刘建国发现二叔有点不对头,总是一个人抽闷烟,饭量明显减少。半夜刘建国上厕所,见院里蹲一人,以为是贼,走进一看,原来是二叔在抽烟。
“还不睡?”
“不睡。”
“咋啦?”
“不咋。”
“心里有事?”
“没事。”
“真没事?”
“嗯。”
刘建国蹲了下来,拍着二叔的肩膀说,二叔,你要后悔,啥时候,一句话,我跟金霞立刻搬出去。二叔猛地抬起头,生气地说,你说啥混球话!刘建国摊开双手,那为啥嘛?二叔蹲下去继续抽烟,建国,你以后别再扯房子的事儿,你过的好,二叔看着舒坦。
刘建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直到清晨,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那两个办案民来到二叔家,不由分说地铐上二叔,就往门口的警车上架。金霞的碗从手里掉了下来“啪”的一声,四分五裂。建国!她大喊一声。刘建国闻声从屋里窜出来,看见二叔正被两个警察押着往外走,他顺手抄起立在墙边的铁楸,像一头发怒的狮子般拦住了去路。二叔看刘建国一副拼命的样子,欣慰地说,建国,你让开,局长请我去吃饭哩,吃罢就回。刘建国目露凶光地站着,一动不动。二叔又重复了一遍,刘建国才勉强让开。民警见路开了,押着二叔就朝外走,待走出院门时,刘建国追上几步,近乎咆哮地喊了一声:爹!二叔身子一紧,泪掉了下来。
在门口蹲着吃饭的村民,愕然地看着载有二叔的警车,迅疾地消失在清晨的薄雾中。
“姓名?”
“二叔。”
“大名!”
“刘富。”
“为啥点刘建国家的房子?”
“啥不为。”
“我再问最后一遍,为啥点刘建国家的房子?”
“为了把我的房子给他。”
“你的啥房?”
“楼房。”
“刘建国家啥房?”
“瓦房。”
“你图个啥?”
“啥不图。”
“啥不图?”
“图个死后有人埋。”
“不给房,他不埋?”
“埋,但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二叔喃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