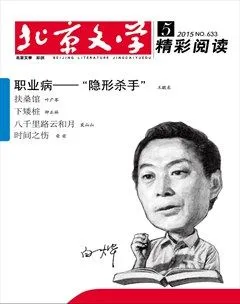母亲的字条
天下的母亲都是相同的,历经十月怀胎之苦、一朝分娩之痛,虽多数儿女会顺顺当当降临人世,但亦有因其难产夺去母亲生命的。母亲是无怨无悔的,以任劳任怨的美德,言传身教的榜样,含辛茹苦的毅力,通过甘香的乳汁一一融入儿女的血脉,铸就了儿女的骨质与品格。
天下的母亲又各有各的不同。孟母三迁为教儿而择邻,少矣;溺爱放纵儿女者,众也。我的母亲难比孟母,但她老人家每逢我的人生转折关头,都以一张普通的字条悄然为我指引。
《庄子·天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世人所崇敬的道,写在书上。书上写的不过是语言,语言有它的可贵之处。语言所可贵的是意义,意义包含着某些言外之意。意义所包含的言外之意不可以用语言表达,而世人却看重语言用来传之于书册。母亲写给我的字条不过是极其普通的语言,但字条却很可贵,可贵的是意义,因此才有了我一生的意义。
一
记得是1976年的初春,我即将高中毕业,当年毛泽东上山下乡政策虽已近尾声(到了197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彻底取消了),但我们76届高中毕业生,还是轰轰烈烈地来到北京近郊区插队落户。临走的那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递给我一个信封说道:“这些钱是给你买吃的用的,一个人在外要注意身体,多吃点营养品,农村艰苦,刚去会不适应。”母亲低声地说着,没有看我,帮我收拾着东西:“我打听过了,你们插队的那个村儿离县城不太远,不忙时跟同学一起去县城买点爱吃的东西,不要怕花钱,身体要紧,钱不够妈再给你寄。”
我接过钱,有些不知所措,又有点百感交集。我自幼是奶奶带大的,无论吃穿用都是爷爷奶奶打理,母亲一周来一次,所以我跟母亲并不太亲。这是母亲第一次给我零花钱,也是母亲第一次说出让我感动的话。因为自从母亲嫁给父亲后,她的钱就交给奶奶管理,母亲和父亲身上只留少许饭钱,所以母亲这钱肯定是平时挤出来的。我把钱又递给了母亲:“还是留着您自己用吧,我到农村是挣钱去的,到年底我会挣回不少工分呢。”
母亲没有答话,又把钱放进了我的衣袋。那一刻,母亲流泪了。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一辆大卡车把我们拉到了北京城的东面——顺义县侉子营村。由于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到农村,第一次住宿舍,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和不习惯。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想起了母亲给我的那个信封,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三百块钱,还有一张折叠着的字条。
打开字条,母亲那秀丽的字体映入眼帘:“晏彪,明天你就走了,这是你第一次离开家,妈不放心。农活对你是陌生的,农村人很朴实,也很能干,你要多向人家学习务农知识,干活时要格外小心别伤了自己。小时候,你姥爷告诫我:‘好吃的东西不要一个人独吞,要适当分给大家一些,否则小伙伴就不跟你一起玩了,别人就嫉恨你,即使有了好处也会把你挤到一边。’插队也是一样,奶奶给你带了那么多吃的,你要想着分给同屋和一起插队的同学们。如果老乡来了,人家是客人,也要请人家尝一尝。农村人生活艰苦,不像城里,他们没吃过、没见过的东西很多,如果你让他们尝了,见识了,即使他们不感激你,也不会轻意伤害你。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好,你大方,一定会有好报的。
“晏彪,18岁就是大人了,要知道社会的复杂,妈希望你平安健康。插队锻炼的时间不管长短,应该学的农家活你要认真学,学到身上的本事就是自己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用上。凡事既然做了,就一定要做好,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既然认真做事和不认真做事都必须做,为什么不认真做好呢?我相信,插队生活一定会成为你人生的一大笔财富。等你平安回来。妈妈,李秀珍。1976年3月26日。”
或许这是母亲第一次与我这样交心,字字句句都印在了心底,在我插队两年多的时间里按照母亲的话做事做人,终有收获。
我自幼进入业余体校,是东城区业余体校中长跑运动员,东城区400米纪录保持者,北京市400米前三名。在插队前,刘教练特意将我和校友范文忠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插队的事我说不好,不管怎样,我都会争取联系让你们进北京队,但你们要保持体力,每天至少要跑5000米,不然就是到了北京队也会被淘汰。”
作为业余运动员,谁不想进入专业队呢?进入北京队是我们的梦想。我和文忠最听刘教练的话,所以到农村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每天晨跑5000米,跑完规定动作后,还要做些力量练习,然后才去吃早饭上工。我们队长是个练家子,是武术世家,我们跑步回来都能够看见他在村头那棵槐树下练拳。几天后我们就熟悉了,他经常吃完晚饭到我们的房间里聊天儿,有时给我们带块红薯,有时是拿几根熟玉米。来而不往非礼也,况且母亲已经嘱咐我了,所以队长每次来,我都把带来的麦乳精给他冲一杯。那时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营养,麦乳精就算是高级补品了。队长自然没有喝过麦乳精,一尝,说好喝,特别高兴。
队长是个热情健谈的人,他给我们讲武坛趣事,也喜欢听我们讲体校见闻,我们成了好朋友。
队长人仗义,人头也熟,他见我们一心跑步,农家活也干不好,特别是割麦子时,我腰有伤,猫腰时间长了不行。开始队长帮助我,后来让我和文忠割一块地,但这样不是长久之计。麦子收割完以后,有一段空闲时间,队长就每天晚上到宿舍来为我揉腰,尽管每天我都被他揉得哭爹喊娘的,一个月后,我的腰痛病渐渐地好了。队长又开始教我养生气功,并且告诉我,练习气功对你的长跑有好处。
队长心很细,他竟然找到在顺义县体委的亲戚说,我们村里有两个体校学生,跑得很棒,能不能让他们加入咱们顺义队,参加比赛肯定能替咱们拿分。当时北京市运动会有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郊区县也经常有比赛,这样我就去了顺义队训练,既“逃离”了农村的劳动,又可以保持体力,我们从心里感谢队长。
那是1977年秋天,队部的广播员通知大家,邻村放电影《英雄儿女》。在农村要想看一场电影是非常难的,往往是一个村子放电影,七里八村的农民都来看热闹。太阳刚刚落山,我们村的老乡和知青们就兴致勃勃地向邻村走去。邻村的广场很大,已经站了许多人,电影还没有正式播放,事情发生了。这个村的知青毛子在学校时跟我们村的知青八子有矛盾,平时他打不过我们村的八子,现在我们村的人来他们村,而且他们村有几个很能打架,毛子狗仗人势,电影还没有开始放,他们就动手打了我们村的八子。由于看电影的人很多,我和几个知青来得晚,并不知道两个村的知青已经打起来了,正高高兴兴地往前排挤,想找个好位置坐下看电影,突然间毛子他们十几个人把我们给围了起来。那十几个知青每人手里都拿着木棍,有一个知青不容分说上前一棍子将我们村的阿涛的头打破了,其他人也纷纷向我们冲来。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几个掉头就往外跑,他们就挥着棍子猛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我们队长大喊一声:“谁敢打人!”他像一堵墙似的挡在我们前面,指着那十几个知青说:“还有没有王法?”这时一个知青挥着棍子上前朝他就打,队长一侧身,一掌将这个知青打倒在地,怒吼着说:“谁再上前我废了他!”
邻村知青一见我们队长会两下子,又自觉理亏,一哄而散了。我们扶着被打破头的阿涛赶快回村里卫生所包扎。这件事过后,我们仍然心有余悸,后来再不去邻村看电影了。大家都说,如果当时不是队长赶来得快,我们就惨了。
这件事虽然到现在都没敢跟母亲说过,但我心里清楚,如果不是母亲的教导,平日与队长和老乡们相处融洽,那天的后果不堪设想。
两年零八个月的插队生涯结束了,我与知青们的关系,特别是与村里老乡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乃至我回城后,队长他们还来北京看我们,而我们也经常回村去看望他们。这段插队经历虽在我人生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但在我的内心世界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至今我每天早晨还坚持天天练习养生气功,受益匪浅。正如母亲所言,插队生活是我人生的一大笔财富。
二
1978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正如母亲所预料的,在我插队两年零八个月后知青们迎来了回城潮。一天我接到通知,让我去县招工办。我来到招工办李主任办公室,李主任说,“小赵呀,村里说你表现非常好,所以通知你来,我们这儿有几家比较好的工作单位,都是带中字头的,你挑一个吧。”
我有点受宠若惊,心跳得厉害,我知道这又是队长推荐的。
招工办主任递给我一本册子,我拿起名单一看,的确都是带中国字头的大单位。在那个年代,带中国字头的单位都是好单位,有前途,能分房,是国家干部,福利待遇也很好。而我们那批插队的知青们,大多被分配到工厂、饭店和环卫、房管所工作了,分配到带中字头单位的人并不多。我一眼就相中了中国化学工业部北京化工研究院。我问李主任,化工研究院是个什么样的单位,在什么地方?李主任说,是研究单位,很不错,好像在和平里附近。我一听,正好离我们家不远,当时我们家住二环,和平里是在三环。我试想着,研究院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单位。让我没想到的是,美梦毕竟是梦,尽管我如此顺利地走进了这家化工部下属的研究单位,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大门进对了,小门却走错了!
在上世纪70年代,走后门已然成风。分配到研究院后,人事处二次分配具体工作,凡属于研究院子弟(我们一共分来15名知青,有5位是研究院的子弟),只要跟研究院有点关系的人统统分配到实验室工作,是干部编制。而剩下的像我一样的与研究院或者化工部等上级单位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用人事处人的话说,没有关系,没有字条的或者不是研究院子弟的),爱干不干,一律分配到车间当化学工。
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确定下来如此简单易行!
这个消息如当头一棒。上学的时候我是运动员,400米冠军,荣誉一大堆,是学校里的名人。即使是插队后,在队里写广播稿,到县里体工队帮忙,也属于受人尊敬的。我以前太顺利了,一直处于风风光光的状态。现在终于回城了,分配到研究单位,可悲的是他们不看能力,看“字条”,看关系,一夜之间,我仿佛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最让我感到不公平和耻辱的是,同是插队回来的知青,他们因为有关系有门路就成了干部身份,而我没有关系缺少门路成了倒班工人。我什么地方比那些人差?为什么他们能够去实验室当干部,而我却要去车间倒班?由于想不通,情绪有些激烈;又由于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处境,使我遇到了人生第一次灾难。
我迷茫了,不知所措了,我用不上班、不说话,表明我的无声抗议!
母亲与儿子的心灵是相通的,母亲也是世上最懂儿子心的人。见我几天不回家,也找不到我的踪影,知道一定有情况出现了,母亲让弟弟到祖母家(我平时住在祖母家里)给我带话,让我有时间回家一趟。
我似乎猜到了母亲会对我说什么,所以没有去看母亲。
几天以后,弟弟找到了我,将一个信封递给了我。
弟弟走了,我打开信封,果然是母亲写给我的一张字条:“晏彪,听勇彪(我弟弟)说,你对单位分配的工作不满意,说老天爷对你不公平。你想想,你有运动和艺术细胞,跑步唱歌跳舞样样行,那些不会跑步不会唱歌跳舞的人,是不是也应该怨恨老天爷不公平,没有给他们一副好嗓子,一个好身体呢?
其实老天爷是公平的,当关上你的一扇门,自然会打开你的一扇窗户,人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毛主席当年不也是受排挤吗?长征、五次围剿,毛主席都没有气馁,最终成为胜利者。我知道你不想当化学工,一是对数理化没有兴趣,二是你觉得面子不好看。你想做你喜欢做的事,妈不反对,只要不浪费青春,干什么行行都能够出状元。
听你弟弟说,你想当作家,那样可以改变你的现状,这样想是好事。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妈支持你,只要你走正道,有自己的理想,那就大胆地去追求,妈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但妈有句话一定要告诉你,当作家跟你现在的工作并不矛盾,不是当作家非要一个体面的工作。我听说许多作家都是工人出身,还有不识几个字的农民,正因为他们经历丰富才写出好文章的,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一边写作。老天爷一定是公平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的人,是值得尊敬的。既然你想当作家就要付出努力,多读书,多练习写作,别怕失败。我不懂当作家是怎么回事,也帮不上你,只有靠你自己了。凡事都要有一个过程,定下目标就要坚持走下去,一个人要想成功,他做事的风格一定是坚定不移的。半途而废、朝三暮四成不了大事,那也不是我的儿子。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妈等着在报纸看到你的文章。坚持是成功之母,切记。”
母亲的字条既给我以力量,又捅到了我的痛处,让我勇敢地面对现实,放下面子确定目标,一边坚持三班倒,一边抽空读书创作。我知道基本功是一切的基石,我作了个计划,先读古代名著,再读国外名著,有了基础后再学着创作。
读书是件既快乐又痛苦的事。快乐,是因为从书中知道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如同生在小乡村的人突然看见了茫茫大海一样。正如培根所言:阅读使人充实……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使人善辩。在阅读中,我的思想、身体和做事风格都渐渐地变化着,让我感觉到了阅读的魅力。而痛苦,是指越读书越对自己没有信心,越读书越清楚地看到自己与名家的距离有多远。当我捧读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诗句后,真有前边有景到不得之感。
人,都是在痛苦中成长的,在求知中进步的,在努力中有所收获的。我有幸经历了这三个阶段,读书,写作,投稿,失败;再读书,再写作,再投稿,再失败。我有过灰心的时候,但一想到母亲“半途而废、朝三暮四成不了大事,那也不是我的儿子”的话,又精神百倍了。我每天写下几十张字条,将名人名言和美丽的句子反复背诵。下中班回来,挑灯夜读,直至天边发亮,睡上几个小时。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读背写,写背读,参加文学讲习班,听作家们讲课,研习作家的成名作品,效唐宋八大家之语言优美精练,学朱自清、孙犁之清丽,将文言文和白话文巧妙结合,学习半文半白之文体。七年苦学,终于在1985年秋天,我的第一篇散文《幽州书屋一瞥》,发表在《北京日报》副刊上。文章渐渐地散见各大报刊,母亲为了能够第一时间读到我的文章,特意订了《北京晚报》。功夫不负有心人,写作不但改变了我的命运,也陶冶了性情。《北京工人报》终于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使我步入了新闻单位,开始了我的文学创作和编辑生涯。
三
自从进入新闻出版单位后,写作水平也突飞猛进,毕竟新闻单位的老编辑们在学识上,编辑功底上高我一筹。特别是在组织稿件时,那些名家的稿件也是我学习的营养库,这一切都让我受益。在进入新闻单位第5个年头的时候,领导委以重任,由我主持《文化周刊》工作。
一日,携妻带儿到母亲家,妻兴奋地说:“妈,人家晏彪又进步了,当主编了。”妻的话让我飘飘然,在吃饭的时候竟然会忘记了祖训,大谈阔吹起来。如何用人,怎么经营,如何抢名人稿件。由于兴奋多贪了几杯,更是狂妄自大之极:凡是不听话的换人,凡是干不好的走人,《文化周刊》在我手上一定能够办成北京第一副刊……
母亲在饭桌上是很少说话的,这次老人家却开口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当年你姥爷信奉佛教,他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师父教育徒弟的故事。一天学艺多年的大徒弟明宗要出山,说,师父,我已经学够了,可以下山独闯天下了。什么叫学够了?师父问。够,就是满了,装不下了。徒弟自信极了。那你装一碗石子来。徒弟很快装了一碗石头。装满了吗?师父问。装满了。徒弟回答很干脆。师父抓起一把细沙掺入石中,沙子一点也没有溢出来。满了吗?师父又问。这回真的满了。徒弟脸上已有愧色。师父又抓起一把石灰,轻轻撒下,还是没有溢出来。满了吗?满了。徒弟似有所悟。师父又倒了一盅水下去,仍然滴水没有溢出。满了吗?师父再问徒弟,徒弟无言以对。”
母亲的故事讲完了,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那一晚,我想了许久。天下的母亲没有不欢喜儿子进步的,但母亲在暗示我太自满了。三天后,母亲让弟弟又给我送来了一张字条。我捧着母亲的字条,久久没敢打开,我似乎猜到了母亲要说什么。
坐在办公桌前,思绪万千,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打开了字条。依然是秀丽的字体,依然是那平淡淡的语气:“……晏彪,还记得你表舅吗?他的事儿我曾经讲给你听过,当时你年龄小或许没有往心里装吧。你表舅人很能干,但他却不懂得尊重别人,属下们在他的眼里都不如他。用你表舅的话说就是与其跟他们废话不如自己干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铁钉?对于中国人而言,生命有多宝贵,面子就有多宝贵。只要你给足他面子,他就会给足你一切!可如果你伤了他的面子和自尊,他就会对你恨之入骨。你表舅当年既肯为他属下花钱治病,又帮助下属的家人找工作,应该是位好领导。可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瞧不起手下的职工,常常辱骂属下,‘你连自己的老婆都养不起还算个男人吗?’他不给属下一点情面,让人家在老婆和同事面前丢尽颜面,为自己埋下了祸根。‘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人公报私仇,往死里整你表舅。那么能干的一个人最后被一个小人打倒了,这是血的教训。千万不能瞧不起别人,更不能不给人家留情面。
“人在顺境时不要太得意,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老鹰站立的样子就好像睡着了,老虎行走时懒散无力的样子仿佛生了大病,实际上这正是它们取食吃人的高明手段。所以真正聪明的人要做到不炫耀、不显露才华,要学会示人以弱,这样的人才能干一番大事业。如果过于炫耀自我,压制了他人的表现空间,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就必然招致众人的一致嫉恨。在我们周围,才华出众却被排挤的事随处可见。大家都这么说,才华就像一把双刃剑,可以刺伤别人,也会刺伤自己,锋芒太露都会招致小人的嫉恨和陷害。你爸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16岁就当了工段长,21岁当副厂长,不大年纪管理一个厂。他太聪明,别人做不了的,他来;别人管不好的,他管;别人不愿意做的,他做。为人太正直不懂圆滑,不会溜须拍马,就是讲究技术学问。对技术不好的人,对工作中不努力的人,他从来都不客气。上级给他打招呼让他照顾老张,可他该罚还是罚。尽管他经常给老齐酒喝,请他吃饭,他家里有困难,你爸爸给他钱,但‘文化大革命’时,他还不是骂你爸喝了他的毒酒。你爸是有技术,有学问,但凭借一身硬骨头,一张死不认输的嘴,官没有升上去,房没有分到大的。他这一辈子就是不懂凡是做大事业的人,都应该修炼藏拙。有时候装一装傻,做一做糊涂人,对你的工作和人生是有好处的。我喜欢这两句话:人抬人高,人踩人低!”
人抬人高,人踩人低?表舅的故事我是知道的,父亲的事我更是耳熟能详,唯感意外的是母亲悟出了另一番道理。恰逢当时我心中有一个结,母亲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我以前的领导因为办报方针与领导相左,所以被免职贬到我的部门当编辑,这让我很尴尬。他当过我的领导,讲学历,他是厦大的高材生;论文字功底,他的古文功底非常扎实;论文学修养、稿件的鉴赏水平都高我一筹。现在我们位置互换了,倘若处理不好这种微妙的关系,声誉及人品都会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还会失了和气,丢了友谊。
母亲的告诫让我彻悟:“人抬人高,人踩人低。”《吕氏春秋·观世》中的一段话与母亲的语录异曲同工:“譬之若登山,登山者,处已高矣,左右视,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贤者之所与处,有似于此,身已贤矣,行已高矣,左右视,尚尽贤于己。”我放下身段,虚心请教,依然以主任相称。他的稿子我不审,一切由他自己决定;他的大样我不看,直接排版。我把尊严留给他,而他面对我的赤诚也给予了回馈,这便是“人抬人高”的妙处,他很快官复原职了,我们成了好朋友。
经营《文化周刊》7年后,我调到了中国作家协会,这段经历不仅是办报的成功,更多的是在办报中学会了做人。每每回忆,母亲的教诲都让我如刻心底。
母亲学历不高,只读过高小,但母亲朴素又颇具哲理的思想,如茫茫海洋中的航标灯,使我没有迷失方向。我感谢母亲不仅给我以生命,更照亮了我的人生。
感逝酸鼻,吾已过天命之年;感恩酸心,母亲已老,我还能侍奉老人家几何?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