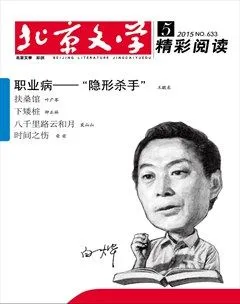记忆北京
很久以前,我在北京第三中学上学,家住在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的一个大杂院里。
听老人说,我家这一带之所以被称为“宫门口”,是因为在明朝的时候,这里曾有一个庞大的宫殿,叫“朝天宫”,是大臣们演练如何朝见天子的地方。它气势恢宏,占地面积巨大。
突然有一天,朝天宫着了一场大火,大火之后,无所遗存。远近的人们纷至沓来,在焚毁的宫殿台基上,捡起残砖破瓦和断木,搭建起一间间一排排小屋,一小片一小片的住房变成一个院子,一个个院子又连起来演化为胡同。“宫门口”三个字,取自“朝天宫的大门口”之意。
几百年过去,巍峨的宫殿从北京人的记忆中消失,只有古老的地名世代相传,却有一处院落鲜活在我记忆深处,它是我每天上下学路途中必然经过的鲁迅故居。
鲁迅故居和我家的院子近在咫尺。青灰色的砖土墙,黑漆的大门引发我强烈的好奇与无数的猜想,终于有一天,我推开了那两扇沉重的院门。随着“吱呀”一声,一代文化巨匠的一个生活片断展示在我的眼前。我平时看到的鲁迅都是他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在演讲台上慷慨陈词的伟岸和高大,而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他在卸去盔甲来到后台时,和我们常人生活无异的琐碎与平实。
鲁迅任教育部部员期间,于1924年买下了这个院落,带着他的母亲和结发妻子朱安一起搬了进来。
这是个典型的四合院,鲁迅搬进来后,也搞了一番“装修”。他在前院种下了两棵丁香树,这两棵树现在依然枝繁叶茂,年年花团锦簇。三间正房的东西两间分别是鲁迅母亲和朱安的卧室,中间的一间是厅。鲁迅把厅向后院方向扩建接出了一间,作为他自己的卧室,戏称为“老虎尾巴”。东西两侧的厢房也是他亲自设计建造的。后院原本荒废着,被鲁迅改造成了一个小花园。鲁迅在此居住期间,写出了广为世人传颂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一件小事》等两百余篇文章。
我漫步在这个在北京司空见惯的小四合院里,想象着鲁迅那拿惯了笔墨纸砚和大烟斗的双手,是如何拿得起铁锨镐头,像个邻家大哥、大叔,挥汗如雨,气喘吁吁地刨地挖坑,种树建房?朱安是鲁迅的母亲为他定下的包办婚姻的妻子,年长于鲁迅,不识字、缠足。鲁迅不爱朱安,两人长年分居两室,鲁迅视她如陌路。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1925年4月的一天,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群学生慕名来到这个小院探望鲁迅,其中有一个女子名叫许广平。
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爱火越燃越烈,朱安的心在痛苦的深渊里越坠越深。鲁迅与许广平出走南方,后鲁迅病逝于上海。再后来鲁迅的母亲去世,曾经给了朱安几许希望,又给了她无限失望的这个小院就只剩下她一个老妇人。站在朱安的卧室里,似乎还能听到她的叹息在角落里回荡。想象着她一个人在这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是每天看着丁香树上的花朵,双眼里尽是失落和茫然,我的心也不禁为她感到凄凉。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这个小院里孤独凄楚地去世了。鲁迅的几个学生把她下葬。她的墓地在当年的西直门外保福寺一带,连墓碑都没立。那片地方现在恐怕早已面目全非了吧?
北京城里到底留下了多少名人的足迹,有多少名人故居?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曾发生过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和多少被后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带着种种臆想,我又继续走在上学的路上。
走出鲁迅故居,把鲁迅的书香墨香和朱安的幽怨叹息抛在脑后,往东往北,过了宫门口三条和四条,三拐两拐就上了翠花街。沿翠花街向北,路过传说中的少帅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寓所,到富国街,我的母校北京三中就在富国街东端。
我上学下学可以穿胡同,也可以走大街。从家出来,沿阜成门内北街向南,就到了被誉为“一街看尽北京七百年”的“文物旅游一条街”——著名的阜成门内大街。这条街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美誉,是因为这条街上文物古迹甚多。我沿阜成门内大街一直向东,先路过路北边的妙应寺白塔,就是常言说的白塔寺。妙应寺白塔是元代的建筑,由尼泊尔人设计,是我国最早最大的藏式佛塔。白塔屹立在蓝天白云下,是如此的高大雄伟。尤其让我感到神奇的是塔顶的铃铛,每当从塔下走过,抬头仰视,心里总盼着刮风,心想,要是铃铛被风吹动,响几声就好了。父亲说,他小时候,白塔寺有庙会。他去赶庙会时最爱干两件事:看拉洋片和吃煎灌肠儿。白塔寺庙会是当年北京城里有名的大庙会,在老舍的《骆驼祥子》、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和鲁迅的《伤逝》里都有精彩的描述。
过了白塔寺,到达阜成门内大街和赵登禹路交会的十字路口,从这里沿赵登禹路一直往北,也可以到达富国街上的北京三中。赵登禹路是用抗日英雄赵登禹的名字命名的。卢沟桥事变后,赵登禹将军率领29军的官兵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北京南苑守卫战后的撤退途中不幸壮烈殉国。北京城里一共有三条以抗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和张自忠路。对这些抗日英雄,毛泽东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每次走在赵登禹路上,我的脑海中总会闪现出硝烟弥漫的战场,想象着这位出生在山东的英雄,带领兄弟们挥舞着大刀和日本鬼子拼杀,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就在阜成门内大街和赵登禹路交会的十字路口东边路北,还有一处古建筑,即历代帝王庙,从十字路口就能看见它“三间一启”式的屋宇式大门,粗粗的廊柱和高高的石头台阶。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昌盛于清乾隆年间,明清两代皇帝都到这里祭奠历代开业帝王和历代开国功臣。乾隆曾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使这里成为海内外华人颂扬先贤、缅怀前辈的地方。
历代帝王庙当时是北京第一五九中学的校舍,我高考时的考场就在这里,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历代帝王庙的辉煌与壮观,雕刻着精美图案的汉白玉栏杆和石阶至今还在我的记忆里熠熠发光。几年前,学校搬到别处,古建筑的风貌得以保护,这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沿赵登禹路向北到富国街,路口有一个有着朱漆大门的大院落,这里就是富国街3号,我的中学母校,北京的名校老校——北京第三中学,简称北京三中。
北京三中所在的街道以前叫祖家街,1965年更名为富国街。而祖家街这个老地名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永远定格在路口的7路公共汽车的站牌上。站牌上的“祖家街”三个字,就像一部沉默的史书,向后人讲述着如尘如雾的岁月,如云如烟的往事。
明朝有个武将,叫祖大寿,镇守明朝疆土的边关锦州。祖大寿的军队抵不过勇猛彪悍的清兵,只好向皇太极投降。满清朝廷建立后,为祖大寿加官晋爵,置办房产,就在这条街东口为他建了一套宅院。从那时起,这条街就被称为祖家街。
祖大寿的这套宅院是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三进四合院,前院后院大小房屋加起来有近20间。垂花门,雕花窗,件件精美绝伦。老影片《早春二月》和80年代的电视剧《徐悲鸿》等影视作品都曾到这里拍摄外景。祖大寿去世后,这里就改作祖家祠堂。
北京三中最早的前身是成立于雍正二年的“八旗右翼宗学”,当时校址不在祖家祠堂,而是在西单小石虎胡同的一个王府。1912年,该校改为“京师公立第三中学”,搬进了祖家祠堂。1950年学校改成“北京第三中学”。八旗右翼宗学、京师公立第三中学都是北京三中的前身。
现在的北京三中已经搬进了原四合院西侧的崭新的教学楼,四合院部分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学校里有两个由教室布置成的纪念馆,“曹雪芹纪念馆”和“老舍纪念馆”。我的母校是如何与曹雪芹和老舍有一段渊源的呢?
位于西单小石虎胡同的八旗右翼宗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所为“高干子弟”开办的贵族学校。从1740年后大约有10年的时间,这里有一位外地老师,就是后来因为文学巨著《红楼梦》而名垂青史的曹雪芹。曹家因为贪污等罪名被雍正皇帝下令抄家,曹雪芹从江南来到北京谋生,成了一名落魄的“北漂”。不过好在他有“文凭”,通过了朝廷的任教资格考试,可以到这所学校任教。这位穷困潦倒的老“北漂”,白天在学校里上班,晚上就蜗居在西单大街路西旧刑部街上的一座小庙里。
古老的北京用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博大包容的胸怀拥抱了这位“北漂”。曹雪芹的业余爱好是串胡同,是个老牌儿的“胡同串子”,没事儿的时候就到处走街串巷,寻访古迹。而恰恰是这样的生活,为他日后写作巨著《红楼梦》提供了充实的素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人考证,《红楼梦》中“葫芦僧断葫芦案”这一章回的故事发生地的原型,是东城花市斜街里的卧佛寺,贾宝玉梦游中所到的太虚幻境的原型是朝阳门的东岳庙,而荣国府的原型就是后海边的和珅府,也即后来的恭王府。
我曾特意到西单的小石虎胡同寻访。小石虎胡同就在中友百货大厦后边。当年办学的王府也在,据说是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府邸。现在府里被分割成一个个商铺,成了游人如织、熙熙攘攘的民族大世界服装市场。旧刑部街连同曹雪芹栖身的小庙,以及西单剧场等周边建筑早已被拆除而不见踪影。街上的行人有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更多的却是“北漂”。他们不仅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可以说是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北京打拼闯荡,为着心中的理想,为着美好的生活奔波劳碌,在北京这个异乡建功立业,安家落户。
在充满朝气、衣着光鲜的新“北漂”人群中,我仿佛看到脑后拖着长辫子,身穿破烂长衫的曹雪芹这位老“北漂”的身影。时光在这里轮回,空间在这里交错。虽然星移斗转,时代变迁,但是,海纳百川,包容博大,从来就是北京的人文传统之一,这种文化不以衣食住行这些外在因素的改变而改变,而是被一代代北京人世代传承,直到今日。
1913年,一位叫“舒庆春”的学生考进已经搬到祖家祠堂的京师公立第三中学。虽然这个学生学习成绩优异,可惜,因为家庭贫困,缴不起学费,又在数月后退学。舒庆春从这里退学后,又考上了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有谁会知道,这位舒庆春,就是后来成就辉煌的文学巨匠,老舍先生!
在这里,就让我高攀一下:我和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伟大的老舍先生是校友。在老舍坐过的教室里学习,在老舍走过的小路上穿行,我心中自然多了几分恭敬与宁静,在这样的历史与氛围中,我又怎能不发奋学习?
我爱读老舍的小说,从他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他的善良。老舍出生在一个大杂院里,在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接触交往中度过了贫困的童年。这段经历使得他对这些“弱势群体”有着发自内心的真切的同情。这种情感贯穿于老舍所有的作品中。我也看到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人力车夫、小商贩、娼妓等等,都在老舍的笔下栩栩如生。我走到阜成门,就会想,从这儿出城往西的模式口,是祥子捡骆驼的地方;到金鱼池一带游玩,我会想,这里原本是老舍笔下的龙须沟;到护国寺小吃店吃小吃的时候,我又会想起,老舍的出生地就在这附近的小杨家胡同,这个胡同后来成为他很多作品里故事发生地的原型,比如《四世同堂》里的小羊圈胡同。有时候,我不知是老舍把这些地方和人物搬进了他的作品,还是这些地方和人物从老舍的作品里走出来,来到人间,来到北京。我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老舍的作品里?这个感觉时常让我恍惚。老舍与北京,早已融为一体。老舍,是北京的一个符号,一面旗帜,一个象征。说起北京,谁能不谈老舍?
老舍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作为一个穷孩子苦孩子出身的老舍,如何能读得起私塾呢?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位“刘善人”的资助。
刘善人祖籍南方,祖先积累的财富富可敌国,后来到天子脚下的北京购置房产,安居乐业。说起来有点像今日腰缠万贯冲进北京城的“温州炒房团”。相传西直门内大街有一半房产曾是他们家的。到了刘善人这一辈,已经不知是“富几代”了。据说此人长得圆脸豹眼,体形富态,声若洪钟。他喜欢玩儿,喜欢遛鸟儿、唱戏、玩儿蝈蝈儿、逗蛐蛐儿,是个老北京的闲散玩家。他说话做事总是不慌不忙,即使眼前有山崩地裂,他也只是漫不经心笑眯眯地说一句:多大事儿呀。
这位“高富帅”还有个喜好,就是施舍衣食救济穷人,因而得了个“刘善人”的绰号。今天卖件祖传的古董帮这个人上学,明天卖间铺面帮那个人治病,北京城里受过他恩惠的人不计其数,老舍就是其中之一。老舍知恩图报,在学习之余,常来刘善人家做“志愿者”,帮着他一起为穷苦的人做善事。
几十年下来,刘善人钱财散尽,就把老婆和女儿送到尼姑庵出家,自己来到广济寺出家为僧,后来做了这里的住持,人称“宗月大师”,在宗教界德高望重。
广济寺位于阜成门内大街和西四大街交会的十字路口附近,是一座年代久远规模宏大的寺院,历史上几度扩建,香火盛极一时。北京沦陷后,日本鬼子利用各种手段让他加入日伪组织的佛教会,被宗月大师严词拒绝,日本鬼子把他抓进了监狱。后来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又把他释放。宗月大师悲悯众生,爱国爱教,圆寂后出殡时半个京城的贫民自动走上街头为他送葬,场面壮观,感人肺腑。宗月大师没有遗产,没有后人,但是他的无量功德与日月齐辉,共天地长存。
我曾怀着崇敬的心情特意去广济寺参观拜访。寂静的寺院,肃穆的建筑,它们是否还记得就在并不太久远的从前,这里发生的一切呢?
老舍曾写一篇名为《宗月大师》的文章,以示纪念。在文章中,老舍满怀深情地说:“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35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老舍,宗月大师,他们一心向善,同情弱者,他们的名字是善良、悲悯、慈爱、厚德等等这一系列美好词语的代名词。同时,他们又是坚强的、勇敢的。他们热爱祖国,不畏强暴,心里怀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宁死不屈,铁骨铮铮。他们是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光辉典范,是北京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绽放出的美好人性的光芒与魅力光照千秋,万古流芳,永远值得所有的人去怀念、传承、发扬和光大。
住在朝天宫的大门口,和鲁迅做邻居,在祖家祠堂这样的地方上学,和老舍是校友,曹雪芹是母校前身的一代名师;耳朵里听的,眼睛里看的,是宗月大师这样的传奇;走过用英雄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自然而然就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老地名里蕴含着久远的传说;身边路过的,是广济寺、白塔寺和历代帝王庙这样的名刹古建……
这么短的一条从家到学校的路,就有这样多的故事,跨越这样漫长的历史。而关于整个北京的记忆,又要用多大的篇幅去描绘?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成长,我又怎能不热爱北京,思念北京,祝福北京?
三千年历史的沧海桑田波澜壮阔,一千年国都的皇家风范王气逼人,孕育出华贵从容的气质,孕育出璀璨夺目的文明,孕育出凝重深厚的文化。北京的每一条胡同,每一条街巷,每一个院落都像北京的血管、经脉和细胞,滋养着北京城,哺育着北京城,养育出一代代像老舍、宗月大师那样的北京人,给北京生机,给北京活力,给北京胸怀。而北京之所以能有日新月异的发展,皆是建立在坚实厚重的历史之上。
秋风入梦,雨打窗棂。上学路上的记忆,是北京的记忆,充满温情感动,绵延千年,深邃隽永……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