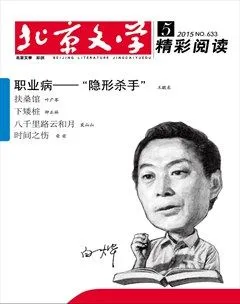今天该怎么讲“农夫与蛇”的故事
《红沙场》是一个新时代的农夫与蛇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关于生命的长度和宽度的故事,或者也可以说是关于生命的质量和价值的故事。“我”是活家老三,一个具有男子性格和气质的女子。以“我”来叙述显然可以更好地实现作者的叙事意图。小说仿佛是徐徐打开的活家的生活卷轴,从活家到红沙场落户、活家四兄妹出生开始,依次交代了活家四兄妹悲苦忍辱的童年生活,苦苦挣扎的青年时代。老实善良的父母如何因为自己的一念之仁,上演了当代农夫与蛇的故事,母亲甚至因此罹患绝症,成为被咬的农夫早早去世。活家兄妹为保护自己的权益,为了不再当愚善的农夫,和侵犯的“蛇”抗争,打起了官司,终是欲告无门,父亲死不瞑目。大姐离婚,大哥遇车祸身亡,弟弟义愤之下触犯法律成了劳改犯……作者仿佛要把所有正在上演的一幕幕人间不忿、不平集中在活家一门,以“活”作为小说人物的姓,恐怕也暗含着“活路在哪儿?如何活?怎样才能活成自己”的意思。而如何活成自己,活出自己的尊严和光彩,也正是千千万万社会底层百姓的主要诉求。因此可以说,这幅活家的生活卷轴,也正是写照当代中国老百姓生活的一幅长卷。
中篇小说《红沙场》人物众多,“我”是小说的叙述者,“我”也是生活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评论者,但“我”显然不是一个成熟老到世故的“合格“的叙述者。这篇小说里真正推动小说叙事的,是“我”的情感和情绪。“我”是一个情感充沛,然而又有点任性不负责任的叙述者。情感的充沛让这篇小说真气弥漫,从始至终情绪十分饱满,读者甚至能感受到小说里到处都是“我”那双不服气的眼睛,那张不妥协的面孔。这让小说气韵保持了相当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然而“我”又是任性的,不负责任的,“我”可以不考虑小说叙事的节奏,随意拉长或者压缩一段时空,又可以很任性地把枝枝蔓蔓和主干缠绕在一起,然后一股脑儿地塞给读者,丝毫不管你是否接受得了消化得了那么多生活的硬疙瘩。不过,这样的叙述倒也让这部中篇小说有了蛮不吝的可爱气势。尤其,这种蛮不吝里还有那么多鲜活的生活细节,那么多脆生生的新鲜独特的语言,就像红沙场的沙子,冷不丁就会硌一下你精致的牙,让你印象深刻。
可以说,《红沙场》里始终有一口气,一口不服之气,抗争之气。向不公抗争,向生活抗争,虽然抗争的空间和视野狭窄,但这口气支撑了全篇,甚至主导了小说叙事的走向。某个时刻,它甚至凌驾于小说叙事之上。当情绪可以主宰一个文本走向的时候,无论读者还是作者,都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小说结尾,作者试图让“我”放下那口气,走向更辽远开阔的未来,意识很好,也显现了作者不俗的潜质,但前面那口气的表现实在太强悍了,使得最后的这个放下有点底气不足。
《红沙场》的阅读,绝不是轻松愉快的,但却是坚实的,不容轻慢的,不会让人后悔的。这让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我们阅读小说是因为我们喜欢它。我们喜欢它是因为小说作为生活的一种图像,能刺激或满足我们在生活中的兴趣。”罗伯特·佩恩·沃伦,美国第一位“桂冠诗人”,这是他读小说的理由。如果说小说家写小说,是为了留存住生活的精髓;那么读者读小说,显然是包含着对重新结构生活的一种期待,尤其是写实性重构。农夫与蛇的故事讲了一代又一代,也许,今天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农夫被蛇咬了后到底能干些什么。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