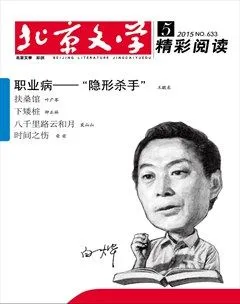相思镇(小小说二题)
茹先生
相思古镇只有一个剪头理发的铺子:茹先生修面铺。茹先生其实是个女的,从南方迁过来的,开了理发铺子,却取名茹先生,理发也被说成修面,相思镇的老少没少费琢磨。
琢磨归琢磨,不耽误镇上的老少去修理头发。茹先生又是个女的,镇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也都放弃了自己拿剪刀剪头发的习惯,跑到茹先生那里坐在可以转圈的皮椅子上,舒舒服服地剪头。茹先生剪出的发型,怎么看都像是三四十年代的明星,镇上的女人喜欢得不得了。有时候扎堆一起去打哄,铺子里叽叽喳喳唱戏一般热闹,凑不到跟前的大老爷们儿就叹气摇头。
茹先生年近四十,瘦高挑的个儿,短发齐肩,面相白净,长得中规中矩。茹先生不拘言笑,铺子里不管多热闹,仿佛与她无关,她只是专心做活。把手头的活计做停当,拿起一面镜子左照右看,客人满意,她的嘴角会浮起一缕笑意,抖着手中的围布,下一个——脸上的一缕笑意便收回酒窝里。
相思镇的爷们儿爱剃光头,省事省钱。剃光头,茹先生不用推子,就是手中那把明亮月牙般的剃刀。剃刀在茹先生手中就有了灵气,上下翻飞还富有节奏。茹先生剃头不像外面的理发店,搬着你的头摁来摆去,让人不舒服。茹先生给人剃头或高或低都是她调整自己的姿势,有时还要半蹲着做活。头剃干净了,再刮脸,全套活做下来,不多不少九九八十一下。然后一条热毛巾捂住头,待头皮焐热,再用十指按压轻拍,那舒坦都浸到骨子里了。茹先生给人修面不论价钱,你随便给,钱也行,物也中。有的一家子来理发,孩子就抱着一只鸡。
茹先生做活认真,尤其是刮脸。
镇上有个痞子黑虎,一脸络腮胡子,常常干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勾当,换了钱就去喝酒赌博。大罪没有,小错不断,气疯公安难死法院,谁拿他也没有办法。他经常到茹先生铺子理发,理完发就拍拍屁股走人,从不付账。茹先生也从不过问,照样认认真真地给他剃头刮脸。有人看不过去,就出来打抱不平。黑虎就耍横,说,怎么着,老子在镇里白吃馆子,他们也得给面子,剃个头算啥?茹先生就摆摆手,儒雅地拦住他们,乡里乡亲,和气生财。
谁也没有问茹先生为什么是一个人生活,茹先生也从不讲自己的身世。有好事的主儿就去给茹先生做媒人,茹先生只是笑笑,摆摆手,不当真,不当真。有人说茹先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上海滩十里洋场混过码头。解放后他的先生被镇压了,她就投靠远房亲戚来了相思镇。有人在理发时就搬出传闻来求证,茹先生还是笑笑,摆摆手,不当真,不当真。
一场运动袭来相思镇时,正是镇上春暖花开的季节。黑虎领着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胳膊上戴个红箍箍就成了风云人物。他们把茹先生的铺子给砸了,说,修面,就是修正主义的面子。茹先生是大军阀大恶霸的小老婆,挂着牌子游街,还给她剃了阴阳头。
白天游街,晚上,茹先生就用一块手帕裹住头,手帕在额前打了个小蝴蝶结,十分好看,照样去给各家各户剃头刮脸。
黑虎听说了,晚上也领着人找上门拉着茹先生开批斗会。筋疲力尽的茹先生在回家的路上不慎摔进沟里,双腿骨折,再也没能站起来。
黑虎的父亲卧床两年,形容枯槁,发乱须结,正值三伏酷暑天撒手人寰。老人留下的话就是要把自己收拾干净了再走。黑虎的母亲哭骂着黑虎,一家人手足无措。
门推开了,茹先生被人背着进了黑虎家。
茹先生一丝不苟地开始给安静的老人剃头刮脸。因为自己行动不便,茹先生就坐在老人的身后,把老人拦在自己的怀里。天热,放置了两天的老人体上已经有了异味。茹先生全神贯注,没有任何表情。不多不少九九八十一下,同样用热毛巾捂住头,十指在头部摁压轻拍。全套活做完,茹先生浑身汗水湿透。
黑虎扑通跪在茹先生面前,把头磕得砰砰响。
送走了父亲,黑虎就负荆请罪,到茹先生屋里跪着哭着要学修面。茹先生不放话,黑虎就跪一天。第二天,来帮着生火做饭烧茶端水,接着跪。也说不清茹先生到底收了黑虎没有,反正黑虎整天在茹先生身边伺候着,背着茹先生走街串巷。也经常看到黑虎脸上有一道一道的刮伤的刀痕。
茹先生去世时,黑虎披麻戴孝,亲自操刀为茹先生净面剪发。
黑虎的剃头铺子开张了,还是叫茹先生修面铺。
风 月
风月是相思镇剧团里的台柱子,扮相俊美,嗓音稍稍带些鼻音儿,听起来反而格外有韵味。
剧团有三四十人,旦角演员也不少,却只有风月是科班出身,省戏校毕业后分到团里,一来就挑大梁。
风月扮演过许多角色,《铡美案》中的秦香莲,《断桥》中的白娘子,《龙凤呈祥》里的孙尚香。最拿手的两出戏是《秦雪梅》和《铁弓缘》。
风月考入戏校时年龄还小,选什么行当自己作不了主。
不过这也没关系,注定吃这碗饭了,只要不演媒婆、不演大花脸都成,风月心中暗想。。
风月的授业老师姓萧,深知选一个合适的青衣演员有多难。
十几个俊丫头排成两行, 萧老师从左往右,再从右往左挨个儿相看。
风月站最后一排,萧老师在她面前驻足不前。
这个小丫头柳叶眉、丹凤眼,不用勒头眉眼都向上挑,羞羞看人一眼,就低下头笑,不声不响的,安静得像朵栀子花。
萧老师问一句,风月柔柔回一句,嗓音像画眉子叫。萧老师拉着风月的手走到一边,问:愿不愿学青衣?风月使劲点点头。
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是做演员最基本的艺术修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风月比别人学得都上心。
风月一个“卧鱼”没做到位,萧老师手中的板子就敲过来了。风月“呀”一声,抚着被打痛的胳臂,眼泪成对儿成对儿地掉,宛如梨花带雨,楚楚动人。萧老师后悔自己下手重了。
玉不琢,不成器,梨园行自古以来有陋习,老艺人们爱说“打戏”,出师后即便是红遍天下,学戏时挨打总是难免。萧老师曾是当红的大青衣,也是这么过来的。
萧老师取来一枚新鲜的生鸡蛋,细心地把蛋黄分出,仅留下蛋清,轻轻揽住风月,在她已经青紫的胳臂上涂抹,怜爱不已。
我不怪萧老师,你是为我好呢……风月抽泣着,反过来却安慰萧老师。
即便是哭,也能咬字分明,萧老师仔细端详着风月还挂着泪珠的小脸,心中一动。
萧老师说,一个好演员不能过于单一,梅兰芳梅大师工青衣,可刀马戏、闺门旦都拿得起放得下。老师没有门户之见,你学学闺门旦吧,《秦雪梅》这样的悲情戏也适合你。
风月答应了。
秦雪梅这个剧中人物的行当属于闺门旦。在《哭灵》一折中,有这么一句:秦雪梅见夫灵悲声大放,哭一声商公子我那短命的夫郎…… 秦雪梅拿着祭文,手抖得如同风中秋叶。可别小看这个抖手,那是个功夫,风月苦练多日,还是不得要领。
风月急得直跺脚。萧老师逗她说,去集市上买条活鱼,把手放松,顺着劲儿,随鱼而动。细细揣摩,反复练习,功夫到了,自然就会。
风月却当真了。那时她是个学员,没钱买鱼。伊茗湖畔经常有人垂钓,风月就趁课余时间跑到这里,静静地蹲在人背后,看见人家钓上一尾活蹦乱跳的鱼,就忙不迭地帮着把鱼钩取下,有意在手中多拿一会儿找感觉。钓鱼人都喜欢这个文文静静不爱说话的小姑娘,鱼一咬钩,就冲风月使眼色打手势招呼她过来捡鱼。后来知道风月是戏校的学生,拿活鱼是为了练习基本功,越发喜欢她了。有个老伯还送她一只红色小水桶,钓了鱼专门送到风月的住处。
手势语言在戏剧中被称为演员的第二张脸,风月一次次抓鱼,一遍遍地找感觉,终于掌握了其中的奥妙。萧老师发现,这丫头双手动作起来,表现力极强,尤其听说她真的练抓鱼,惊讶极了。
上了妆的风月一袭白衣,宛如天人。手拿祭文,跪拜在商公子灵前,一声商——郎,凄艳哀绝,荡气回肠。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尤其是唱到“商郎夫你莫怨恨莫把我想,咱生不能同衾死也结鸾凰”时,风月藏在水袖里的双手上下抖动,犹如白蝶飞舞,银花翻卷,凄美空灵,令人眼花缭乱。
一下台,萧老师就把风月抱住了,说,丫头,你抓了多少条活鱼呀?
在团里挑大梁的风月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后来和花脸海椒结合了,事业上顺风顺水,家庭美满幸福。风月依然是剧团的台柱子,青衣、闺门旦甚至刀马旦都拿得起放得下,可谓文武不挡,色艺双绝。
真正让风月名声大震的是《铁弓缘》这出戏,花旦、青衣、小生、武生四个行当全在一出戏里集于一人之身,唱念做打缺一不可。风月把青春貌美武艺高超的太原守备之女陈秀英演活了。
就在《铁弓缘》这出戏赴京演出的前夕,风月突然病倒了。
病愈后的风月基本没有变化,就是手抖动得厉害,连一小杯水也端不牢。风月郁闷地问海椒, 我还能不能上台了?海椒说能,《铁弓缘》咱不能演,还演不了《秦雪梅》?风月含着眼泪笑了。
萧老师闻讯,心疼坏了,心急火燎专程赶来探望风月。
师徒俩深情地望着对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半晌,风月好像想起了什么,就把一双手举到萧老师面前,眨了一下眼,说,萧老师,要是现在练习抖手,我就不用去抓活鱼了吧?
话说得很轻松,那神态,像个俏皮的小花旦。
责任编辑 白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