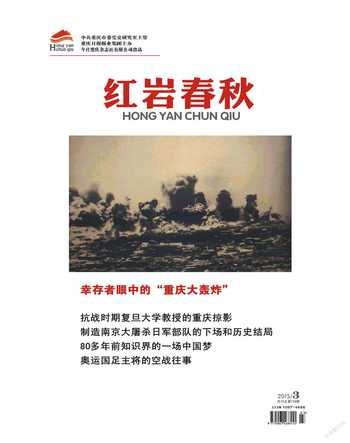粟远奎:“六·五隧道大惨案”死人堆中爬出的幸存者
陈启兵



粟远奎,尽管已是80多岁高龄,仍行动自如,思维清晰,谈吐流畅。在他的书房四壁,悬挂着当年日机轰炸重庆的各类图片。谈及震惊中外的重庆“六·五隧道大惨案”,粟老原本平静的脸上布满悲愤。他指着一张当年美联社记者所拍摄的大量死难者尸体被抛扔于石梯上的图片,对笔者缓缓说道:“记录的只是其中一个镜头!”
1941年6月5日,发生在重庆较场口的“六·五隧道大惨案”,无疑是重庆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页。当年,粟远奎正是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幸存者之一。虽时过境迁,伤痛的记忆却从未从他脑海中抹去……
他的家曾经优裕而平和
1933年12月8日,粟远奎出生在重庆较场口鼎新街(今重庆解放碑一带,包括较场口在内),旧时名曰“都邮街”。当年,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散文《都邮街》,描述了其繁华兴盛之况:“……抗战司令台下的吸烟室、东亚灯塔中的俱乐部、皮鞋的运动场、时装的展览会、窗体底端香水的流域、唇膏的吐纳地、领带的防线、衬衫的据点、绸缎呢绒之首府、参葺燕桂的不冻港、珠宝首饰的走廊地带、点心的大本营、黄金的‘十字街头’……”
粟家所建的4层楼房,正位于鼎新街口上,楼上自住,底层门面出租。粟远奎的父亲头脑灵活,又通文墨,平日代人书写家信、诉讼状,兼作其他营生。门面出租加上父亲的收入,让一家人衣食无忧。粟远奎至今记得,自己和哥哥、姐姐、弟弟平日就在这条大街上嬉戏、游玩,日子多么地优裕、平和。但这种美好的生活很快就被击得破碎,痛苦不堪。
抗日战争期间,处于中国内陆的西南重镇重庆,不仅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的指挥中心,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尽快结束中日战争”,对重庆城区及其周边区县采取“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无限制轰炸”等战术,进行灭绝人性的无差别大轰炸。所谓无差别轰炸,就是不区分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不区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狂轰滥炸。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昔日繁华锦绣、富足无比的都邮街,被炸毁、焚烧得破烂不堪,一片焦黑。凝聚粟家心血、集全家财富的那栋楼房,在1940年8月19日,也被炸成一堆破砖烂瓦。遭此重创,一家人哇哇痛哭,几近绝境。粟家在原址的街对面,用楠竹、蔑席,搭了个权且栖身的简易窝棚。但厄难并未就此打住,日机仍不时飞临重庆轰炸,粟家与所有市民一样,提心吊胆地挪时度日,谁也说不准哪天就把小命丢了。
惨案就这样发生了
1941年6月5日,天空惨淡,几乎整天都在淅淅沥沥地下雨。就在这一天,日机对重庆城实施第60次大轰炸。当时,粟远奎还不满8岁。因每天都生活在生死未卜的恐惧中,只要听到日机空袭的警报一拉响,看到汽球挂上,大家便立刻没命似地奔跑躲藏。天刚黑,粟家吃完饭,碗还没来得及清洗,警报响起了。父母简单收拾了点东西,便带领全家一路奔向防空洞。粟家离较场口隧道只有50米左右,他们很快进入隧道的深处。
外面的轰炸声没有停止,进入防空隧道的人却源源不断。粟家人开始感到闷得难受,父母带着孩子们试图向隧道口移动,但外面的人又拼命向里面挤,双方移动都很困难。起初,孩子们还听得见父母的叫喊、招呼声。挤了一会儿,一家人就挤散了。粟远奎被人流挤到隧道口的拐弯处再也无法移动。因个儿小,他在大人们的大腿间挤钻过去,挨靠隧道墙壁蹲下。
重庆防空隧道位于人口密集的市中区地下,东西南北十字形纵横走向,连接贯通朝天门到曾家岩、南纪门至临江门,设计总长4000米。“六·五隧道大惨案”发生在市中心较场口地下段,有十八梯、演武厅、石灰市3个出口,总长438余米,宽2.5米,面积1096平方米。隧道容量有限,当时人员严重超标,已是超负荷爆满。
这一天,日机对重庆城进行了3批狂轰滥炸。第一批为当日7点28分,粟家在第一批轰炸来临之际进入了防空隧道。“六·五”轰炸不同往常,日机扔了炸弹、燃烧弹,又不停地扔光明弹(照明弹),情形甚是凶险。第二批日机9点18分投弹轰炸,第三批10点17分投弹轰炸,3批飞机24架,每批8架轮番轰炸,前后历时5个多小时。这段时间里,隧道内没有人出去,眼看缺氧越来越严重。
年幼的粟远奎也感觉到人群的燥动不安,听到有人在叫喊“难受”,接着有人喊“救命”,还有的人双眼流泪,口流清水,婴儿和孩童的哭喊声也越来越多,部分油灯开始熄灭,但谁也不愿坐以待毙。于是,人们的忍耐转为紧张,斯文变成粗野,都想涌出去,但隧道里塞挤得形同桶状,如何挤走得动!人们先是自抓自扯,接着相互推掀、抓扯,昏暗、嘈乱的隧道如同人间地狱。粟远奎死死地蹲靠着墙壁,一动也不动。不知过了多久,他昏睡过去……
粟远奎哪里知道,就在他昏睡期间,由于拥挤和缺氧,他所在的较场口隧道内已酿成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
亲历者眼中的人间地狱
为还原“六·五隧道大惨案”的真相,笔者找到现居住在重庆市南岸区水泥厂的高荣彬,他当年参加过“六·五隧道大惨案”尸体疏、抬工作。提及大惨案,高荣彬不禁声音哽咽。
高荣彬是重庆长寿人,12岁时随父母从乡下移居重庆城谋生,拜鞋匠杨海清为师。日机轰炸重庆城时,重庆防空司令部招募防护团队员,条件是爱国、正直、无私、无畏、年轻体健。高荣彬和师兄游海云均被招募,当时高荣彬16岁。防护队员属义务性质,配发了一套衣裤、袖套、防毒面具,再无其他待遇。平日参加出操、训练,日机轰炸前,挨家挨户地疏导、劝说、督促、护送人们进入防空洞,逐一检查是否有盗窃、抢劫行为。待别人进洞了,自已再躲藏。日机轰炸后,防护团队员更要快速行动,救人救火,不顾自己生死。
1941年6月5日,日机第3批轰炸结束后,重庆防空司令部、空袭救护委员会和防护团即开展抢救和尸体的疏散、抬出,并在现场设置4道封锁线,不准“无关”,尤其是新闻从业人员进出。
高荣彬和游海云到达现场,已是次日天刚亮。因是夏季,尸体变质快,几十米外就感受到强烈的尸臭味。两人按指令先在嘴、鼻处喷洒上白酒,然后戴上防毒面具。十八梯洞口和演武厅洞口,均被尸体堵死,无法进入。他们便从石灰市洞口进入,任务就是将堵死的隧道疏通,把尸体抬出去。参加疏、抬尸体的除防护队员,还有警察以及雇请的民工,总计100多人。两人一组,一人抬尸体的头,一人抬尸体的脚。高荣彬和游海云分在一组。
虽然石灰市隧道没有十八梯、演武厅隧道情况严重,但尸体依然比比皆是,越往里走,尸体重叠愈多。不少地段上的尸体将隧道堵塞得几乎没有空隙,相互纠缠到一起。尽管抬尸体的人都是年轻力壮者,但拉扯挤塞的尸体,仍要用尽全身之力。最不易拉扯开的,是一些尸体的双手双脚,你抱夹着我,我抱夹着你,最后只好合抬出洞。开始抬尸体的时候,高荣彬和游海云的心情十分悲伤。抬的次数多了,伤痛变得麻木了,感觉抬的不是人尸,而是一截又一截的木头。
当到达演武厅方向时,他们见到了更加令人胆战心惊的场景。堵塞的尸体活像层层堆码的麻袋,从地上一直堆到洞顶,堵得密不透风。他们一时束手无策,只得向十八梯方向奔去。
当几名防护队员来到粟远奎昏睡处,拉开重叠的尸体,掩埋在下面的粟远奎露了出来,他本能地动了一下,防护队员高声叫道:“有个小崽儿!”粟远奎抬手揉揉双眼,防护队员又惊奇地叫道:“还是个活的!”粟远奎醒来之时,因他身边的尸体已被抬出不少,他以为周围的尸体与自己一样,是睡着了,还没醒过来。
防护队员向他叫道:“小崽儿,是哪家的?还不赶快去找你的老汉(父亲)。”此时,粟远奎四肢乏力,无法站立行走,而防护队员忙于疏、抬尸体,无暇顾及尚活着的粟远奎,他只得顺着隧道梯坎向上爬行。不知爬了多久,终于爬到隧道口。他张目四望,整个一条街,全是重重叠叠的死尸,一眼望不到头。
粟远奎跌跌撞撞地回到家,只见父亲躺在床上,哥哥和弟弟也在,母亲在哭。他们见到粟远奎,又惊又喜。母亲赶忙问:“看到你两个姐姐了吗?”粟远奎摇头:“没看到,不晓得。”父亲腿部受伤,无法行走。弟弟还幼小,母亲只带着哥哥与粟远奎,去寻找失散的两个姐姐。隧道内的尸体仍在源源不断地抬出,根本无法辩认死者本来面目。粟家母子走过去,看过来,泪流干了,嗓子喊哑了,怎么也找不到两个姐姐。
真相是什么
这是一次世间少有的集中大屠杀。从隧道内抬出的尸体,堆码在十八梯隧道口外,周围洒上了一层白石灰、酒精、药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杂气息,令人作呕。尸体的衣裤大多撕扯得稀烂,身上遍布牙咬、手抓痕迹,有的肚腹被挤踩裂开,其状甚惨。这些迹象表明,均是因窒息之际,人与人相互扭打、抓扯所致,乃至几乎没有一具完整无损的尸体。
“六·五隧道大惨案”到底死了多少人?直到今天,都没有统一、确切的数字。1941年6月11日,也就是“六·五隧道大惨案”发生后的第6天,重庆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呈文蒋介石:死亡827人,重伤165人,轻伤1000余人;7月上旬,《大公报》刊发《审委会报告》,认定死亡数992人;1994年重庆市人防办撰写的《重庆防空志》估计死亡人数2000—3000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撰的《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中描述“惨死市民近万人”。
关于“六·五隧道大惨案”的死亡人数,不管是呈报给蒋介石的数字,还是《大公报》公布的数字,以及后来官方根据领取抚恤金人数认定的900余人,都不确切。当时有外国驻华记者,将十八梯堆积如山的尸体拍摄成照片,刊发在报刊上,令世界为之震惊。而据高荣彬和游海云目睹隧道实况和参加疏、抬尸体3天3夜的经历,实际死亡数字肯定超过当时官方认定数字。
当时的实际状况是:“六·五隧道大惨案”发生前,6月2日,日机轰炸重庆城,根据防空疏散的需要,很多人被疏散到江北、南岸等地。事过几天,被疏散的人重新返回市区办理事务,走亲探友,滞留一时未归。而返回江北、南岸的轮渡,至傍晚6点多就停渡了。6月5日,大轰炸突袭而至,滞留在城内的大量人员,这时想离开也不行了。加之市中区人口密度本身就大,沦陷区和周边区县又涌进大量难民。因而日机到达时,大量人员涌进了市中区的十八梯、演武厅、石灰市3段地下防空隧道。按设计容量,这3段地下防空隧道总容量只有4300人,而实际涌入人群肯定超负荷,至使挤塞在里面的人,形同插笋。事后,重庆市区和周边区县死者家人、亲属或可领取抚恤金,而沦陷区难民和周边破产且孤身的难民,就无人前来领取。当时民间有一则故事流传甚广:一个老太婆坐在十八梯下,见抬出一具尸体,就扔一根竹签,结果扔了竹签几万根。当然,这个数字更不可信。当时严禁他人进入现场,一个老太婆如何进得去?她又如何找到几万根竹签?但据惨案亲历者田泽周称,在新民报馆当记者的表弟告诉他,报馆统计的死亡人数是17300余人。
当时有个摄影人叫程默,他既是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又兼任国民党卫戍司令部摄影顾问。这种双重身份,为他提供了其他摄影者和新闻记者所不具备的条件。程默经历了重庆大轰炸和“六·五隧道大惨案”,拍摄了一本《重庆大轰炸老相册》,这本相册至今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它忠实地记录了从1941年5月1日至6月15日重庆被日机狂轰滥炸的惨烈图像。程默有一段回忆录,里面这样描述:“1941年‘六·五’大轰炸以后几天,从防空洞到江边,密密麻麻布满了尸体。人们运尸时,都是成摞成摞的,难以计算具体数字。我看跟南京大屠杀差不多了。”
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
“六·五隧道大惨案”死亡数字虽未能定论,但这场浩劫是确凿无误的。当时,从隧道抬出的尸体,无人认领的,开始还有城内各善堂提供薄板棺材。棺材不够了,就用篾席包捆。天热尸体发臭,边捆篾席边流尸水,动手包捆者无法忍受,就将尸体简单裹拢,中间用根竹篾片围缠一下。再后来,竹篾席也没有了。政府出动20余辆军用卡车,拉运那些没有任何包扎捆裹的尸体。装载着腐臭尸体的车辆,车走一路,恶臭一路。尸体拉到朝天门码头,再用几十条木船走水路运到江北寸滩、黑石子等地埋葬,前后达几天几夜。粟远奎与家人赶到朝天门码头,希望能从翻动、搬运的尸体中,找到两个姐姐,但最终没有找到,估计是运到“万人坑”集中草草掩埋了。
大惨案发生后,重庆城经济更加萧条,粟家在城内的生活也就更加艰难。当时政府要求疏散城内人员,粟远奎的父母也担心日机再来轰炸,于是决定:父亲一人留在城内,母亲带着孩子搬到乡下避难、谋生。他们搬到南岸龙头庙(今重庆市南岸五公里)。没想到的是,这个地方有一家兵工企业,是日机重点轰炸对象。粟家又搬到江北五里店一带,紧挨着21兵工厂,也是日机重点轰炸对象。为保住家人性命,粟家只好再另寻他处。几经辗转,最后搬到寸滩甘蔗坝,靠租种几亩地维生。父亲仍在城里想法挣点小钱,维持家庭日常开支。1945年,抗战胜利,粟家喜极而泣,他们又搬回城内较场口原址居住。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为了强国保家,粟远奎光荣参军。先是到湘西剿匪(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剧本,就出自粟远奎战友之手),抗美援朝时期,粟远奎又扛枪奔赴朝鲜战场。从部队转业后,他先后在重庆市政府、重庆市民政局工作,于1993年退休。
粟远奎的一生可谓历经险难,但令他终生不忘并告之后代铭记的,当属他亲身经历的“六·五隧道大惨案”。
(作者系重庆市写作学会、散文学会理事。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