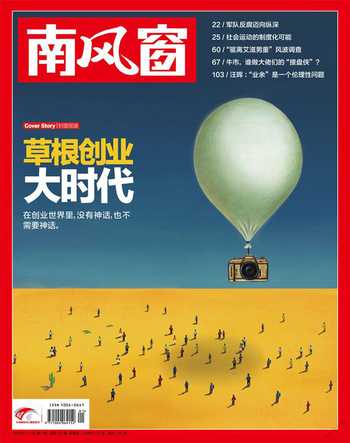“邹碧华现象”的启示
叶竹盛
新一轮司法改革启动以来,常有法官“倒在”司改路上,既有辞职下海当律师的,也有身兼领导职务的法官自杀或是意外死亡的,还有因为贪腐而落马的。他们的“倒下”或有微澜,却大多迅速湮没在这个时代司空见惯的常规叙事之间。
然而,另一位倒在司改路上的法官却改变了此类叙事的节奏和基调,引起的反响甚至蔚然而成“现象”。2014年12月10日,上海高院主管司改事务的副院长邹碧华在前往参加一个司改调研会的路上,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死亡。上海高院这两年来并不平静,先是发生了“五法官嫖娼事件”,从贵州公安厅长任上调来的新院长崔亚东尔后又受到贵州老下属的集体举报,并且他还因为轰动一时的贵阳“小河案”,遭到“死磕派律师”的龃龉。
此类“不平静”或许更符合这个剧烈转型时代中国法院和法官的公共形象。邹碧华之死无疑是一种颠覆。邹碧华猝死的当天,他的死讯便在朋友圈里“刷屏”了。我的朋友圈中几乎每一个法律界的朋友,不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学者,都在发自内心地哀悼邹碧华。很快,邹碧华刚刚随风飘散的灵魂又在他诸多朋友、同学和家人的笔下重新汇聚而成一个温润、丰富、完满的存在。连崔亚东也说,“他以一个法官的身份赢得整个法律界的尊敬!如此哀荣,实属罕见。”
尽管邹碧华备受哀荣,但是接触过法治发达地区法官的人们或许会发现,参照他们的标准,邹碧华只不过是一个尽职的“正常”法官,具备的是法官职业本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德行。一个尽职的“正常”法官却制造了一个“罕见”现象。崔亚东的话在无意间道出了中国法治一个令人隐痛的“集体潜意识”。确实,我们过去几年看到了不少另外的法官故事:在冤案中没能守住正义的底线,在法庭内外与律师发生冲突,在公共舆论上“丑闻”不断,在判决书中讲理粗糙……在这些负能量的故事中,法官没能成为社会的粘合剂,反而一次次损害人们对于正义的憧憬。
从一定意义上讲,修复法官形象正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甚至可以说,检验新一轮司法改革成败的标准就是能否产生足夠多的“邹碧华”。
作为上海司改前哨的操盘手,邹碧华“出师未捷身先死”,但“邹碧华现象”却为后来者带来至少两个启示。其一,树立司法权威的根本不在于要求人们对司法应有什么态度,而在于一个司法体制能否产生足够多的“邹碧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值得敬仰和尊重的人,人们总是乐意赋予尊荣。同理,信仰和尊重法治的公众心理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取决于法治状况本身是否值得信仰和尊重。因此,司法改革的重点在于创造更好的司法制度,使更多法官更容易成为“邹碧华”。
其二,一些法官或许会为自己未能达到“正常法官”的标准而责备客观条件,以此为自己开脱。但无可否认的是,邹碧华与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外部环境中履行法官职责的。也许邹碧华付出了比大部分法官更艰辛的努力,但邹碧华能达到的,其他法官似乎没有更好的借口停滞不前;邹碧华能坚守的,其他法官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借口轻易放弃。相比法治发达地区的法官,如果说中国法官与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中国法官比他们多了一项职责:在更难坚守法治精神的环境下,更加努力地坚守法治精神。这正是“正常”法官邹碧华的“不寻常”之处。
邹碧华倒在了司改路上,但他身后哀荣备至,照亮了司改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