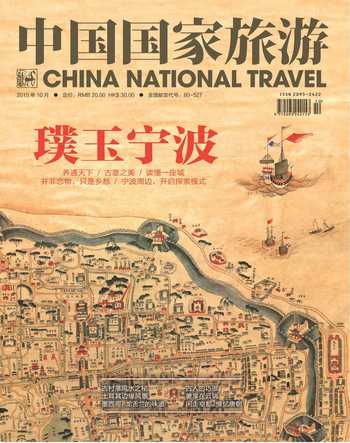只在沉默时旅行
威廉·哈兹里特(1778-1830),英国散文家、评论家、画家。他的随笔风趣、亲切,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散文风格;代表作是散文集《席间闲谈》和《时代精神》
我看不出一面走路一面又谈话有什么明智之处。当我在乡村的时候,我希望过简单朴素的宁静生活,就像这乡村一样。我不赞成评论那些灌木树篱与菜牛。我走出闹市是为了忘却那座城市与其中的一切。有些人,为了这一目的而去海滨胜地,同时把大城市的那一套也带去了。我喜欢有更多自由活动的空间而较少累赘。我喜欢离群索居,当我沉溺于其中之时,完全是为了独居的缘故,也不愿找一位朋友分享。

旅行的灵魂是自由,完全的自由,是思考,感觉与行动,怎么高兴就怎么做。我们旅行主要是为了摆脱所有的累赘与一切的麻烦,把自己远远地抛在身后以摆脱其他人的纠缠。这是因为我想有一块小小的活动空间,思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在那里沉思会整理她的羽毛又让她的翅膀生长变强。
因此我常离开城市一段时间,在由我自己决定离开的那一刻,我一点也不会感到迷惑。我不是与一位朋友同坐在一辆轻便双轮马车里或一辆邮递马车里彼此交换着什么有趣的消息,或将同样陈旧的话题重翻花样,这一次就让我与无礼傲慢达成一次停战的协议吧。给我头上那明亮的蓝天,让我享有脚下那绿绿的草地,还有呈现在我眼前的那条弯弯曲曲的路,再让我跑上三个小时的路程,享受一顿美餐——然后是思索!在这寂寞的石楠丛生的荒野上如果我不能搞一些消遣娱乐,旅程将是非常艰难的。我大笑、奔跑、蹦跳,我由于高兴而歌唱。然后是久被遗忘的事物,像“沉没的失事船只的残骸与无数的珍宝”一样突然出现在我急切的目光前,于是我开始有了感觉,有了思维,重又变成了现在的我。
这不是一种试图用妙语或陈词滥调打破的尴尬的沉默,我的沉默是一种未受干扰的心灵的沉默,只有这种沉默才是完美的雄辩。没有人比我更喜欢双关语、头韵、对偶、辩论与分析了;但有时我宁可不要这些东西。“去吧,让我休息!”我此刻正忙着其他的事呢,这事对你来说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但对我来说它可是“事关良心的大事”。不加评论,这朵野蔷薇难道就不可爱了吗?那有着祖母绿般表皮的雏菊就不会突然出现在我的心中了吗?然而,如果我向你解释它如此受我喜爱的原委,你也许只会一笑了之。难道我最好不是保守秘密、让它满足我默默思索的愿望,从此地到那远处陡峭的峰顶,再从那儿移向远处的地平线?我要是一路都这样做的话,我只能是一个不能相处得极好的伙伴,因此我宁可独自一人出游。我曾听说,当一阵闷闷不乐的情绪袭来之时,你最好是独自步行或骑马,让自己陷于沉思之中。然而这看起来好像是违背了惯例,是对别人的轻视,而你又一直在想你应该重新回到你的伙伴中去。“还是从这种半心半意的友谊中脱身出来吧。”我说。我喜欢要么自己完完全全地独处,要么彻底地听别人摆布,要么讲个痛快,要么彻底保持沉默,要么走路,要么静静地坐着,要么爱交际,要么独自一人。
有人说:“边喝酒边吃饭是一个很坏的法国习惯,一个英国人同时应该只做一件事。”我看这话很有道理。我不能一会儿说得上劲儿,一会儿又想得入神,一会儿又沉浸在忧郁的沉思中,一会儿又加入到愉快的谈话中。不断讨论与留在心中的对事物的无意识的印象是相抵触的,而且还破坏了情绪。如果你仅仅只是用类似哑剧表演的方法暗示你所感觉到的,那么这是乏味的。如果你不得不说明它的含义,那么它就把一件乐事弄成了一件苦差事。
比起分析法来,我宁愿在旅途中用综合的方法。因此我满足于将各种想法贮藏起来,然后再检验分析它们。我愿意看到我的那些模糊的想法与见解飘飞,如微风吹送的种子的冠毛,而不愿让它们被争论的荆棘缠绕。
我不反对与任何人争论一个观点以消磨二十英里的有限路程,但决不是为了快乐。如果你闯到了豆田飘过道路的芬芳,你的旅伴也许毫无嗅觉。假如你指向远处的某一物体,他也许是近视眼,不得不掏出眼镜来才能看到它。天空中存在着某种感情,云朵的色彩中有着某种心境,这一切激发着你的想象力,其中的效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就不会有同情,而只有一种焦躁地想得到它的渴望,一种旅途中纠缠着你的不满,最终也许会招致心情不佳。这样一来我决不会和自己争吵,并认为我自己的结论理所当然是正确的,直到我觉得有必要为遭受异议的这些结论做辩护。这不完全是由于你与将自身呈现于你眼前的事物与环境不相协调——这些也许会使你想起许多事物,引起联想,这些联想太微妙,以至于你不能将它们传达给别人。然而这些我却极为珍视,而且有时我仍充满深情地紧抓住它们,当我能离群独处而可以这样做的时候。
假如我能自如支配言词与形象,我就会试图唤醒休眠于晚霞中的金色山脊上的思绪;但一见到自然,我那本来就贫乏的想象,垂下了头,合上了叶子,像落日时的花一样。在现场我竟然什么也描绘不出来,我必须得有时间使自己镇定下来。一般来说,一件有趣的事会使户外的风景变得兴味索然,它应该留作席间的谈资。
美的事物一旦消失,便不再回返。我愿意在将来某个时候重游这令人陶醉的地方;但我要独自一人重游。我找不到其他任何人能与我分享这如涌的思潮,无限的惆怅,无比的喜悦,这些连我自己都几乎想不起来的片断,已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
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旅行更能显示出想象的缺乏预见性与多变性。随着地点的变化,我们的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不仅如此,我们的看法与感情也发生变化。通过努力,我们确实能把自己带到久远的、长期被人遗忘的景致中去,心灵的图画也随之再次复活;但我们忘记了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似乎我们一次只能想象一个地方。而想象的画布只有一定的面积,如果我们在上面画了一组物体,它们立刻就会把其他的一切擦掉。我们不能扩大我们的构想,我们只能变换我们的角度。风景向迷醉的眼睛敞开胸膛,我们在饱览之余,似乎不能再塑造出其他美丽与壮观的形象。我们继续前进,不再去想它,将它排斥于我们目光之外的地平线,也将它像梦一样从我们的记忆中抹掉。
在穿越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时,我真想象不出一片树林繁茂的耕作中的土地会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整个世界都是荒芜的不毛之地,就像我所看到的这一片那样。在乡村我们忘记了城镇,在城镇我们又看不起乡村。“除了海德公园,”托普灵·弗勒特爵士说,“所有的地方都无非荒漠。”在我们面前,我们在地图上看不见的所有部分都是一片空白。我们所构想的世界比一个坚果的外壳大不了多少。它并非是一个景观延伸到另一个景观中去,并非是郡连着郡,王国连着王国,陆地连着大海,形成一个庞大广阔的形象——大脑所能构想出的空间与眼睛一次所能收入的空间差不多一样大小。其余的只是写在地图上的一个名称, 一种数学计算而已。例如,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叫中国的国家,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只不过是地球仪上的一英寸纸板,并不比一个中国的铺子有更多的意义!靠近我们身边的事物看上去与真实生活中的尺寸一样大小,远处的事物则缩小到理解的尺寸。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测量宇宙,甚至在理解我们自己存在的结构时也是非常零碎的。然而,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记住了无数的事物与地方。大脑就像一架演奏各种不同曲调的机械乐器,但它必须将这些曲调连续地演奏出来。一个想法会回忆起另一个想法,但同时它又把其他的想法排斥在外。

在试图复活回忆起来的事物或景象时,我们好像不能打开我们的存在之网;我们必须抽出一根一根的线丝。因此如果我们来到以前住过并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地方时,每个人一定会发现,由于预感到了将会得到的实际印象,我们越接近这个地方,这种感情就越强烈:我们记起了多年来我们未曾想起的环境、感情、人物、脸庞与名字;而此时世上其余的一切都被暂时遗忘了!
回到上面我放下的那个问题:我并不反对与一位朋友或一群人去参观遗迹、沟渠与绘画,恰恰相反,这是因为与先前相反的理由。它们是可以理解的事物,而且是可供人谈论的话资。这里的情感不是心照不宣的,而是可以交流与公开的。索尔兹伯里平原没有什么好评论的,而其附近的巨石阵却是一个富于画趣的、研究文物的、富于哲理的讨论题目。
在观光的一群人出发时,首先要考虑的总是我们要去哪里;在独自一人漫游时,问题是我们在路上会经历什么。“心灵是它自己的地方。”我们也不想急于到达旅途的终点。我自己就能不带偏见地评论艺术品和奇物珍品。我曾经颇为炫耀地带着一群人去牛津——指给他们看缪斯女神的住地,大谈从长满青草的四方院与各教学大楼与学院的石墙之间吹来的学术之风——在博德利图书馆我真是轻车熟路;在布伦海姆我完全取代了接待我们的向导,他徒然地举起手中的棍子指点着绝妙绘画中那些平庸的美女。前面提到的理由当然还有另一个例外,那就是我冒险在异国旅行而无人相伴时,会感到信心不足。我不时地希望听到自己国家语言的声音。在一个英国人的心中,对于需要社会同情的帮助才能被接受的异国风俗与观念,存在着某种并非出自本意的反感。随着与家乡之间距离的增大,这种慰藉,起初是一种给人享乐的事物,却变成了一种酷爱, 一种欲望。发现在阿拉伯的沙漠中没有朋友与同胞相伴, 一定会让人感到窒息;在看到雅典与古罗马的时候,必须允许有一些需要表达的感想存在; 而我则承认金字塔太伟大非凡了,仅靠一次的思索冥想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种处境下,与一个人所有平常一系列的想法相反,他似乎是单独的一个种类,是从社会扯下来的一支,除非他能即时遇到伙伴并得到支持。然而当我的双脚刚踏上充满笑声的法国海岸时,我一度并未感觉到这种需要或渴望的迫切性。加来港充满了新奇与欢乐。该地忙乱连续的模糊之声像灌进我耳朵里的油与酒;太阳西沉时,从港中一艘又旧又破的船的顶部由水手们唱出来的圣歌,在我的心灵听来并不像异国之音。我呼吸的只是普通人类的空气。我走过“藤蔓覆盖的小山与法兰西快乐的区域”,身子笔挺,满意非常;因为人的形象未现愁苦之相,也未束缚于恣意专横的御座的基部,语言并未让我不知所措,因为我能懂得所有伟大的绘画学派的语言。整体像幽灵一般地消失了。绘画、英雄、光荣、自由,一切都遁逃了,除了波旁皇族的成员与法国人民,什么也没有留下!
毫无疑问,进入到异国他乡旅行,必定会有一种在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激动;但它给人的愉悦是暂时的而非长远的。它离我们习惯的联想太遥远了,以至于它不能成为我们普通谈话或言及的题目,而且,它像一个梦,或像另外一种存在状态,不会进入我们日常的生活状态。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然而却是短暂的幻觉。它需要某种努力才能用我们当前的实际身份换取理想中的身份。为了非常敏锐地感觉到我们旧时狂喜复活的激情,我们必须“跃过”一切现有的舒适和现存的关系。我们的浪漫与变化流动的性格不应受到驯服。大学者约翰逊博士曾评论过,对那些去过异国的人来说,异国旅行很少能提高他们谈话的能力与技巧。事实上,我们在国外度过的时光是既愉快,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有教益的;但它似乎是从我们实实在在、完完全全的存在中被剪取的一段,永远不会自然地与我们整体的存在相结合。在我们离开自己国家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另外一个人,也许是更令人羡慕的那个人。对朋友,对我们自己,我们已不是原先的我们。因此诗人有些古怪地唱道:“我走出国门,离开自己。”那些希望忘记令人痛苦的忧虑的人,最好能在一段时间内摆脱那些能使他们想起忧虑的联系与事物;但只有在给予了我们生命的地方,我们才可以说达到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