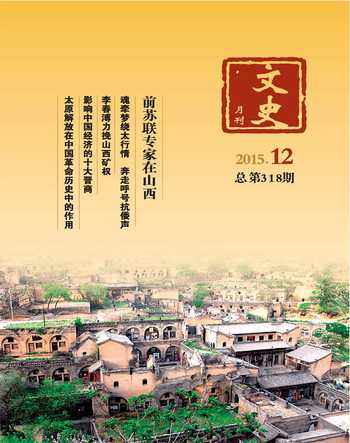前苏联专家在山西
杨建峰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千上万的前苏联专家来到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他们胸怀高尚理想,承载着两党两国友谊,与中国人民一道挥洒汗水,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贡献了力量。然而,1960年7月,前苏联政府一纸命令,所有专家突然撤退回国,给两党两国留下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苏联专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作为中苏两党两国友好的桥梁和见证,如今回忆起那段岁月正是“真情如歌、难以忘怀”。
一
我国资深外交家、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一氓,在一次见面时和我谈及前苏联专家工作时十分肯定地说:“前苏联专家的历史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前苏联专家工作总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回忆与总结。”的确,当时成千上万前苏联专家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军人和学生的友好交往,正是两党两国友好的一个具体缩影。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党和国家培养的第一批俄语翻译人才,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今外国语大学),走出校门后由外交部到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苏联专家工作处(后合署为外事办公室)工作,为前苏联专家服务多年。那时,我才不过二十几岁,跟随一批久经战争洗礼的老前辈,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由于翻译工作的特殊性,我有机会接触双方高层人员,经历重大商谈,阅读内部文电,使我了解到两党两国的不少机密,并被委派参加了诸如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送别工作……
二
前苏联专家工作的历史源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直至1960年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全部撤走专家为止,历时十年。1949年12月,应斯大林邀请毛泽东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前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从随团访问的首席翻译、原北京俄语学院院长师哲先生回忆中得知:毛主席向斯大林亲口提出“希望苏联派出专家援助中国”,并要求“派驻中国政府总经济顾问。”于是,斯大林特意选派了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师哲评语)的阿尔希波夫。
实践证明,斯大林是说话算数的,阿尔希波夫也是合格的。他在中国工作的8年期间,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姚依林等国务院领导人联系密切,精诚合作,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他为了保证前苏联援华项目的顺利实施,同中苏两国专家一起跑遍了我国的大江南北,视察过很多工矿企业和重大工程。我回忆,阿老先后到过太原三次:一次由一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沈鸿,陪同他前来重点考察研究太原重型机器厂上马重型水压机的项目;一次是由五机部领导陪同前来考察、指导二四七厂、七六三厂、七八五厂等国防工厂工作;三是飞兰州途中因气候原因迫降太原,进城休息一晚。第三次我跟随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郑林到机场迎接。因为是意外停机,当我们去机场时,阿尔希波夫已经等候2个多小时。郑林同志很着急,一再让我道歉,但阿老却一点也不生气,还加以解释,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祥和、慈善的印象。晚上,郑林同志宴请阿尔希波夫一行,特邀驻山西专家组长和各援建企业负责人、前苏联专家负责人作陪。阿老当面教诲和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国同志,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要认真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尽快传授好技术,确保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学会独立工作的能力。”
记得,阿尔希波夫于1958年奉召回国,薄一波主持欢送会,他高度评价了阿尔希波夫同志。他讲到过:“阿尔希波夫同志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无私奉献精神,博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阿尔希波夫同志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个时候,前苏联专家深受中国人民信任,每位专家手中的小红本(即工作证),实际上成为了其去任何单位(甚至最保密的单位)的通行证。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类似笑话的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前苏联专家,从鞍钢到了北京,游逛至中南海后,竟突发奇想说想同毛主席聊一聊,并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出人意料地是主席接见了他们。事后阿尔希波夫从中国领导人那里知道此事,找到这些专家询问,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未料到毛亲自接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毛生活得如何!”阿尔希波夫并没有责备他们,但却告诫援华专家:“没事不要轻易打扰中国领导人!”
三
前苏联在山西援建的工业项目先后有20多项,厂址相对集中在太原、大同、长治、阳泉、侯马、永济这些交通较为方便的中心城市,个别的也选择了资源产地,如垣曲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等。当时,中央在山西安排的前苏联援建项目在全国各省当中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军工生产体系,门类有机械、化工、仪表等,生产各种火炮、枪弹、火药、柴油机、仪表、鱼雷以及飞机、坦克、舰艇配件等。民品项目有蒸汽机车、重型机械、火力发电、水泥制造、矿山设备、地质勘探、矿山冶炼等。随着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大批前苏联工程技术人员(统称前苏联专家)抵达现场。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直至1960年全部撤走,累计有上千人次(根据工作需要有来有往),如果加上前苏联专家的家属,人数就更多了。
开始,我们的接待条件很差,大批前苏联专家加上我国的陪同技术人员前来山西踏勘现场、进行设计,首先要妥善安排食宿。当时太原旅馆、正大饭店等几处最好的饭店都住满了,后来实在住不下,就到处找房子,一直到1955年专家招待所(今太原迎泽宾馆东楼)落成(大同、长治也建了小招待所),住宿紧张的问题才慢慢得到缓解。建起招待所又不会做西餐,于是求助外国专家局派来了一批厨师、理发员、司机、翻译,接待条件才有了改善。
当时各项技术业务工作统归国务院各有关部委院所和国防科委抓总,地方政府则负责政治接待和生活接待。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成立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具体接待工作委托交际处承担。后来涉外工作范围扩大,中央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撤销,新成立了以周恩来任组长的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同时成立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统筹全国的外国专家工作。山西也作了相应调整,省委成立了外事小组,政府组建了外国专家处,接受国务院外专局的业务指导。山西的外国专家工作一直是由郑林领导。那时,省委、省人委很重视专家工作,经常听取工作汇报,分析情况,研究问题。郑林每周主持召开一次碰头会,深入了解情况,开展现场办公。遇有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保证了专家工作的顺利进行。
每逢重大节假日,省领导出面接见、招待专家,相机做些工作。那个时代,对外谈话的主旋律是“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原则是“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能强加于人。”我们翻译人员都很熟练地掌握了每面“红旗”的内容、形式、结构、目标、意义。有时还组织专家参观人民公社,在社员家里做客,他们对中国农村的民居、民俗、民风很感兴趣。为了使专家及其家属安心工作,我们专家处想了各种办法活跃、充实专家们的生活。每周举办一次电影晚会、一次舞会,有时还邀请文艺界名流,包括晋剧、杂技、皮影、歌舞、书画家到驻地联欢、表演。也举办过知识讲座,如马烽、西戎谈《新儿女英雄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冠洋谈《孙中山与国民党》,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郝树侯谈《山西地理与历史》……每遇两国国庆节,双方共同举办文体活动,还深入学校、农村、工厂,与工人、农民、学生举行篮球比赛、小型演唱会。其中,专家篮球代表队很有实力,他们几乎打遍了太原厂矿学校代表队。省体工队专业球手们还来“以球会友”,学习他们的新技艺。这些联谊活动受到过省里和北京外专局的好评,也确实起到联络友谊、增强体质、活跃生活的作用。
实践证明,关心、做好家属的工作,对于稳定专家们的情绪,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很有益处。专家处挑选招待所优秀女员工、对口学习的优秀女技术人员与家属们交友,常常往来,互助互爱,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使后来许多疑难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给我的印象是,前苏联派出的专家政治素质高,马列主义修养好,特别是专业技术过得硬。凡选派来的专家,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多数专家都是党团员,有的还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的是生产一线的技术能手。专家组组长是总工程师,也是党支部书记。团支部、工会组织都很健全。平常接待工作多与他们的工会组织联系。我看见他们内部有一个行为准则,共二十条,违反了纪律要受处分,其中有两条涉及到“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他们说,出发前集中在莫斯科学习一周后才动身的。党、工、团都分别有活动,时间安排的很紧。而且他们每周召开一次例会,总结工作,学习文件。他们有时主动与我们联系,问中方有什么安排,好协调一致。他们内部也有思想斗争,有时还很激烈,看得出有的人受了批评,情绪低落。有的负责人不团结,被调整到其他城市。
专家们与中国人相处共事很顾全大局,处处以中苏友谊为重,以两党利益为重,工作上却不含糊,要求跟班技术人员很严格。看得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都想尽快传授技术,培养出人才,完成好任务。
四
当时,我国为前苏联专家安排的待遇很优厚。比如他们的工资,据有些专家告诉我们,他们的工资差不多是本国工资的5倍。
其实很多情况下,前苏联专家是用不着花钱的,各单位拨给专家的招待费、纪念品费、文娱费、书报购置费、住宿费、交通费、医疗费等的标准比工资还要高。上级规定专家完成任务回国,所在单位要以领导名义给专家和家属赠送礼物。每遇两国重大节日,如十月革命节、斯大林宪法节、苏联红军节和我国的国庆节、春节,都有宴请。对一些苏联人爱吃的特殊粮食,如黑面粉、三角米、麦精、巴力米、豌豆瓣、通心粉、黄油、奶酪等,由当地粮食部门负责加工和调拨。有时我们也派出购买人员通过专家工作渠道到产地订货,如黄油基本上由内蒙古友谊宾馆包揽。双方还共同选出代表成立“伙食委员会”,对伙食实行民主管理。通过伙食委员会交流、协商、沟通,伙食保持了平稳运营,而且时有改善。由于太原专家招待所的伙食工作成绩突出,曾在《专家工作通讯》进行过介绍。太原专门开设了“友谊商店”,那时商品不充足,食品、衣服、鞋帽等,各种用具、纪念品、礼品奇缺,市场上基本买不到的,但友谊商店都有。每批回国的专家,利用自己的积蓄,都能到那里选购到满意的商品,大包小包好几件。我们翻译下班以后经常应邀去帮助购物,看得出来他们尤其是夫人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专家们的要求,中方总是想尽办法满足,办不到的及时沟通取得谅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两国两党友好是主流,专家工作舒适、和谐,后期随着两党两国关系渐趋恶化,为专家工作带来极大的波动。特别是在1959年、1960年,专家工作逆转直下,直至撕毁协议,专家撤回,大大损害了援华工作。然而,蕴藏在专家心灵深处的深厚情谊是永远抹不去的。
我们对专家的优厚待遇,固然是两国协商确定下来的,但我们竭尽全力的服务换来的却是深厚的友谊。直至1966年“文革”之前,我陪同由山西代表组成的中国友好访问团赴苏、波、德(原民主德国)访问,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偶遇山西专家组长阿廖耶夫的夫人阿廖耶娃。她是事先获知有山西团来访,但并不知道我也在其中。见面后故作镇静,不敢多言,悄悄约我到电梯里含着眼泪,掩面低语,偷偷塞给我一个眼镜盒,没说两句话就离开了。我回房间打开一看,眼镜盒里压着一张纸条,原来是讲他们返国后的遭遇,以及对中国朋友的怀念,最后,祝我们访问成功。
五
为了真实反映和回忆当年前苏联撤回专家的真实情况,我专门到在山西省档案馆查阅了当年送别工作的一大摞卷宗,重温了中央文电、工作总结、简报……一位当年参与送别工作的老同志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好,人家也不是石头人。”在依依惜别之时,专家们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于是,他们讲课加快了速度,努力把重要的、核心的东西讲完;有的在握手拥抱告别时,把一些技术数据写成小纸条偷塞在中方人员手里;有的在告别舞会上暗示,所有资料你需要什么留什么,于是我方人员连夜复制资料。这些情景在当时十分普遍,以至于1960年国务院专门为此发出过通知,对于主动提供技术资料,甚至亲自协助抄录的专家,“必须尽一切可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保护,以免给他们返国后造成不利影响。”文电还要求:各单位不要向专家索取原来属于其所有的技术资料、工作笔记和教材等,除非专家主动借给或送给。对于向专家借来的资料进行抄录或拍照时,应严格保密,务使资料保持原状,必须选择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员去做,并禁止在专家招待所内进行。还强调指出,所借资料一定要将原件按时归还,不可拖延时日,以便保护专家。切忌对个别专家表示过分的热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强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前苏联专家得到回国的通知要比我们接到的通知晚一周。他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这一周和往常一个样,按时上下班,兢兢业业工作着。突然通知“停止工作,一周时间内全部撤回”,这对他们来说太突然了。每个人都陷入迷惘,百思不解,感情难断。有的难以自恃,情感失态。之后,中央连续发出通知,规定了对外谈话口径,抢先向专家说明:“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是单方面的,责任不在中国,完全是苏联政府造成的。”对苏联专家的贡献要充分肯定,表示感谢。还要求各地、各单位认真做好送别工作,做好技术接受,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对专家的态度要“不亢不卑,友好热情”,加强“沟通、接触、交流、联谊……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于是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组织舞会、茶话会、电影晚会,陪同购物,派人打包行李。临别前这一片友好的气氛,同样给专家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车站送行时,有组织的人员去了,没组织的人员也自发去了,工人、市民、服务员也去了。激动的场面难以形容,美丽的鲜花,美好的祝福,惜别的泪水,重逢的期盼,谱成了一曲友谊的乐曲,在站台上空久久的回荡着……
我陪同专家处长薛珊、交际处长潘汝泗专程送专家到北京,入住北京友谊宾馆。第二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我国政府隆重召开的欢送会,大约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千多专家。周恩来向前苏联专家表示深切的感谢,并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向每位专家颁发了一枚“中苏友谊万岁”纪念章和证书。证书上印着周总理手写体的签名。纪念章、证书是我代表山西统一领回来,按原先造册的花名,发给专家。纪念章做得很精美,金色的底,有两面红旗重叠飘动,一面有五颗星,一面是镰刀斧头,边缘是金色麦穗,还有两片橄榄叶,下面一条红彩带上镶刻着“中苏友谊万岁”六个繁体金字。
如今,前苏联专家奉召回国已经50多年,但他们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